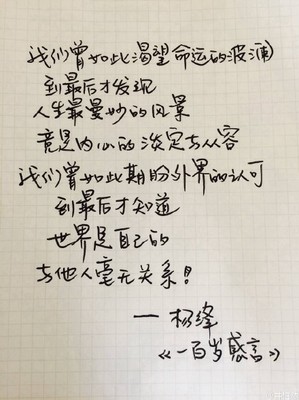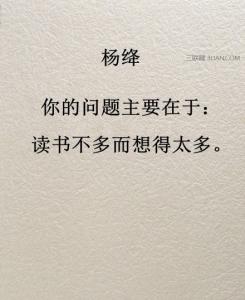【题外话】杨绛原名杨季康,“绛”者,“季康”反切也。
(参见:)
一、名
以下内容参见吴学昭《先生回家纪事》:
2014年4月,钱、杨二位先生曾就读的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Exeter College)院长佛朗西斯·卡恩克劳斯(Frances Cairncross)女士来函称,在Exeter学院建立七百周年之际,该院以推选杰出校友为荣誉院士的方式纪念院庆,恭喜杨绛先生当选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荣誉院士,特此祝贺。
信件如下:
吴学昭女士执笔,杨绛先生口述的回复如下(引文出处同上):吴学昭女士执笔,杨绛先生口述的回复如下(引文出处同上):
············我很荣幸也很感谢艾克赛特学院授予我荣誉院士,但我只是曾在贵院上课的一名旁听生,对此殊荣,实不敢当,故我不能接受。
很明显,这是婉拒。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当选的荣誉院士只有两位,都是杰出女性。除了杨绛先生,还有一位是西班牙王后。Frances Cairncross院长再次回信,澄清并非是因杨绛为钱锺书先生遗孀而授予她荣誉院士头衔,她认为杨绛的情况“很特殊”,但“目前我院还没有女性学者获此殊荣”,“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女院长之一”,Frances Cairncross非常希望杨绛先生能接受这一荣誉。
然而杨绛先生的回信再次拒绝了她。
Frances Cairncross院长最终的回复是(引文出处同上):
以我对您超众脱俗品格的了解,您具有尊严和思虑缜密的回信应在我的预料之中。未能将您延揽入我院授予的极少数的杰出的女性荣誉院士中,我个人非常难过,但我尊重和接受您的理由。感谢您为回应我们的请求,做如此认真的思考。
以下两个链接可以作为某种参考:
不妨再加一条材料(参见):
二、利
钱锺书去世以前,钱杨两人名下并无属于自己的房产。钱锺书去世两年后,杨绛买房了。
(以下参见):
在钱钟书去世两年后,杨绛在北京买了一处新房子。在杨先生自己撰写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她清楚地写道:2000年12月14日,“买房交款”。
······
以杨先生的现状和品行,她买这处新房肯定不是为她自己。在女儿钱瑗与钱钟书相继离开后,房子、钱财对她来说,意义已经不大。在《我们仨》结尾,杨先生写到:“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9月7日,杨绛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正式签协议书。这项奖学金是用他们夫妇2001年上半年所获七十二万元稿酬现金以及以后出版的所有作品报酬设立的。”当年的数字是72万。
十五年之后的2016年,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白永毅在《“好读书”精神永存》里透露:
十五年来,“好读书奖学金”基金已累计达到2434万元,获奖学生614人次。
2014年之后,杨绛还将家中收藏的文物、书籍等物件全部捐赠给国家博物馆,这些珍贵的文物、书籍包括(以下全部翻拍自《杨绛——永远的女先生》):
1、张之洞手迹
2、宋代拓本(宋版书有一页一金之说)
3、汉砖拓本
4、钱锺书在牛津读书时的校服
5、传说中写满钱锺书批注而其出版社重金求购不得的《韦氏大词典》
等等等等。
不好意思,这里要拿大杨绛11岁,前作协主席冰心作一个案例,因为众所周知的事件,也是家庭狗血剧。(;;)
其中,看这里:
再看这里:再看这里:
‘【必须声明,这些都是一家之言,真实性待考。】‘【必须声明,这些都是一家之言,真实性待考。】
------------------------------------------------------------------------------------------------------------------------------------------
三、打架
本来想写“权”的,但被审查了,写不了,以下改写“打架”。
在几年前钱杨书信拍卖事件结束后,时任清华法学院院长的王振民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参见《为了读书人的面子》):
她(按:杨绛)还坚持把这句话写下来,“我不同意拍卖钱锺书的书信”,并郑重签上名。她说她每天打八段锦,“我很牛的,可以打架的。”说着,她伸出自己的胳膊,攥起拳头,证明自己还很强壮。
杨绛所说的“打架”是有先例的,那件事被记录在了《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中,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那件事也可能是钱、杨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事情(参见):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锺书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在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这事有答主提到过,其实事件双方即钱锺书、杨绛夫妇与林非()、肖凤()夫妇。
杨绛说:
我下干校后,钱瑗一人在家里,她(按:XF)在厨房里当面质问:“你爱人‘下干校’啦?怎不回来探亲呀?”钱瑗说:“他已经去世了。”随后,钱瑗听到他们屋里哈哈大笑。这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原来男沙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
以及:
12月2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革命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我出于母亲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冲上去还手。钱瑗是看惯红卫兵行径的,不愿妈妈效尤,拉着我说:“妈妈,别——”可是她拽不动我,就急忙由大门出去了。(她是去找居委会主任的,当时我没有理会。)锺书这时在套屋的窗下看书,我记不清外间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反正他不知道过道里发生的事。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声。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么没叫喊一声。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锺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林非一方的版本如下(),以下是肖凤说:
1973年12月7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那一天,我的丈夫林非被一根大棒毒打,我自己的手指也被咬得鲜血淋漓。那男人殴打时用力极很,手中的大棒当即断成两截。那时正值隆冬季节,林非身穿棉袄,挡住大棒的右臂还被打肿和打破,鲜血淤积,漆黑一片,让我深感恐惧而又心疼不止。 以及:
1973年12月7日,适逢我刚从郊区农村返京,就请余嫂替我洗洗从农村带回来的衣服,因为几天之后还得带着儿子下乡,时间很紧张,让余嫂赶快洗起来。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了,为什么要如此着急,于是就争论起来了。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双臂要抓住我的脸庞,我长得比她高,赶紧向后仰起头,并且伸出双手挡住她,没想到她竟用自己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当时抽出来就鲜血迸流。她这个当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中国有句老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连大字不识半个更画不成圆圈的阿Q都懂得这个道理,想不到她竟会如此行事。俗话说食指连心,我疼痛得大叫起来,林非从房间里奔了出来,想要解救我。咬人者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咬人者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林非赶紧伸手挡住木棒,打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咬人者诬称我们将她提起又摔下了不知有多少次,请问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造谣造得实在太荒唐了。而且既然已经跌得晕头晕脑,怎么又能够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还要可恶地造谣,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在此次冲突中,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只动口没动手,咬人者和打人者则是又叫骂又动手。他们的表演和所作所为,让我看清了他们本来的面目。面对着她的造谣生事,我深深地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了。 (按:杨绛的反应是“我不会生气,我不理她,叫她难过去。”)
关于此事,双方陈述的时间、在场人物、起因都不一样,有比较细致的分析()称(立场偏向钱、杨):
首先是时间,杨绛先生说的是12月2日,星期日(笔者注:杨绛先生文中此段以1972年3月开头,一路写下来,没有在此处注明年份,但在文末杨绛先生明确说明在下一个星期天,1973年12月9日,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流亡生活,可知杨绛先生说的是1973年12月2日)。我想杨绛先生或者是记日记,或者对此事记忆犹新,所以连星期几都可以写出来,将当年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查万年历表,1973年12月2日果然是星期日。而且,1973年全中国都在“抓革命,促生产”,不但没有双休日,非节假日必须上班,职工不可以随便留在家中。从双方的描述看,钱家一家三口,濮家参加工作的两口子整天均在家,也间接说明了这一天是假日。赵凤翔(按:即肖凤)却说是1973年12月7日,相差5天。据《文学报》第119期转载赵凤翔文章后的编者注:林非先生称,肖凤记载日期据林非被打伤后医治的病历卡为证。按照濮良沛本人的说法,治伤的女医生对他很是心疼,中文“心疼”一词,并不是对什么人都可以用,如赵凤翔对濮良沛可以用而且已经用了(在赵文中,赵说她对濮被打“心疼不止”)。濮良沛搞中国文学研究多年,对中文词汇的微妙用法不会不知,特意用上“心疼”一词,可知这女大夫与他关系很不一般,而赵文中再写到此处时,除绝口不提女大夫三字外,更将“心疼”二字拉回到自己身上,按照濮氏夫妇的一贯行径,当他们极力要掩盖某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就一定有使其露出马脚之处。因此,这病历卡的来历本身就很值得怀疑。而且1973年12月7日是星期五,也不是什么节日,如果病历卡的日期居然是12月7日,除了更证明了其可疑外,只能说明他们连这个问题都要撒谎。(按:可能是病历卡上的2写得像7)
其次是人物,杨绛先生说的是有四个人,杨绛本人、钱瑗、钱家请来洗衣服的钟点工小陈,再加上赵凤翔。在赵凤翔的文中,没有提到钱瑗。当年钱瑗与二老相依为命,时值星期日,又是洗衣服之类的身为女儿须要做的事情,不可能不在场。赵凤翔否认钱瑗在场,就是想要抵赖她先打了钱瑗一个耳光这一事实。还有一点,洗衣服的大嫂姓陈,并非姓余,当时正当中年,杨绛先生当年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故称她为小陈。钱家确实有过一位做保姆的余姓大娘,人称余奶奶,但当时已不在钱家。赵凤翔张冠李戴,将“小陈”错当作余奶奶,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已经记不清当年的事情了,无论是哪种情况,赵凤翔描述的可信度,都是很低的。
再就是打架的起因,双方的描述除了钱瑗一事外,事实上并无太大的出入。这是赵凤翔文中很少的几处符合事实的地方之一,因为直到现在她都认为当年她在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是理直气壮的。首先,赵凤翔的“我也请余嫂帮助洗衣服”实际上就是在钱家请来“小陈”洗衣服的时侯,不由分说地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让她“赶快洗起来”,在赵凤翔看来,“小陈”不但应该为她洗衣服,而且她和濮良沛“革命工作”繁忙,“时间很紧张”,钱锺书和杨绛不过是在躲着炮制大毒草,“时间比我充裕的多”,不让她先洗衣服,就是“故意抬杠”,到底谁是“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的人不是很清楚了吗?赵凤翔在这种思想意识之下,同时,配合着濮良沛对“五一六分子”及其家属的“攻心”行动,对钱瑗说出“你不是好人!”这句话,干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这种事,完全符合其性格,即便没有“小陈”作证,任何人都可想而知。
其实这个打架事件已经不可能说清了,双方或多或少都有错,但必须指出,当时杨绛六十多岁,肖凤三十多岁。当事人之一的林非最后总结的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参见《若干必要的澄清》):发生在“文革”后期的此种纠纷,是这场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悲剧。钱家原来独自居住,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心里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而我们的迁徙也因为是护理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同住一室,而不请保姆又无法上班,所以虽然犹豫再三,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思潮与有关决策,热衷于掀起紧张的阶级斗争,却很少为了日益增长与膨胀的人口,考虑怎样去建造更多的房屋,让多少人们混杂在一起居住,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这大概就是大时代的小悲剧。
按:林非的《若干必要的澄清》中也出现了因为记忆偏差、以讹传讹等造成的若干“造谣”,已有学者进行了澄清,具体见以下两篇文章:
林非的:
胡文辉的:
四、病
戏剧家夏衍的女儿沈宁说(参见《杨先生,想念你!》):
1994年我父亲生病住北京医院,一天,我在三楼走廊里遇到了杨先生。她手上提着暖壶,扶着墙艰难地一步步走着,原来她要去打开水,我才知道钱先生也在住院。回来把这消息告诉了父亲,他马上说,那不行,得照顾他们。父亲通过官方渠道,通知了有关部门,使钱先生的就医条件得到了改善,并找到了一个好的护工。
······
后来钱先生因牙床萎缩,不能装假牙,进食只能通过鼻饲。医院里鼻饲的食材都是冷冻的,不太新鲜,杨先生于是决定自己做。······这就忙坏了杨先生,每天把有营养的菜换着花样做好、打碎,送到医院。这一年杨绛83岁。《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记录该年事件为:
······
7月30日,锺书肺炎高烧住院,我陪住。
8月19日,锺书动手术,割除膀胱瘤三个,手术成功,但肾功能急性衰竭,抢救。8月,《杨绛作品集》由社科出版社第一次印刷出版,前后共出六版。
9月30日,我病不支,请得生活护理住医院照顾锺书。我在家做后勤工作,做菜及炖各种汤。
······两年后的1996年,钱瑗也生病住院。《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记录该年事件为:
1996年 1月,钱瑗住温泉胸科医院。
······
11月3日,胸科医院报钱瑗病危。我方知女儿患肺癌转脊椎癌,病发已是末期。 钱瑗所住的医院和钱锺书的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然而在《我们仨》里,杨绛却以当时只道是寻常的语气说:
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那么,杨绛是如何传递消息的呢?
显然不能让钱锺书先生知道真相,学者钱碧湘回忆称(参见《杨柳本是君家树,折却长条送远行》):
(1996年11月)29日再通电话,杨先生说:“······原来,三个人里不知道是谁先走。现在看来,我不是第一个了。不过也难讲,我是随时可以倒下来的。”我说:“你千万定下心来。事情到了这地步,只好拿命来解释。你要保住自己,不然,他们父女俩就可怜了。”杨先生说:“是呀,我现在心里蛮静。我没希望了,心倒静了,别的不想了,就想想安排她后来的事。我也没经验,有什么想不到的,你提醒提醒我。
······
钱瑗第一个“回家”了。······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瞒过钱先生。杨先生说:“我得编一点讲,不然他要问。也不能告诉他,告诉了就要坏事了。”阿圆去世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日,我去电话问候。杨先生说,她每天去北京医院陪侍钱先生:“只有礼拜天不去,讲的是那天去看阿圆。明天我又要编点话说。现在是越编越难了。日子一长,越编越难了。”钱家亲属潘兆平在《是永别,也是团聚》中同样提供了一些信息:
钱瑗去世后,怕钱先生因丧女之痛,雪上添霜,影响治疗及健康,杨先生还佯装没事,照常传递信息:上星期×我去看圆圆了······昨天又和圆圆通电话了······时间长了,怕谎言穿帮,杨先生就拿出当年写小说剧本的本领,写了一个圆圆病情提纲,以便长期笑脸相骗(良苦用心,令人落泪)。钱先生虽已是不能言语,但聪明的脑子仍在正常运转,杨先生的善意谎言编得再天衣无缝,渐渐地终被察觉。后来每当向他再说圆圆时,钱先生表情愈益不耐烦,最后终于动怒表示不愿再听,杨先生试探着嗫嚅问道:“······侬晓得啦?”钱先生闭眼做了个肯定的表示,一场凄凉的骗局才告终止。钱锺书的弟弟钱锺鲁说(参见):
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瑗都罩在里面,外在的风雨都由她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庭,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如此,再读那段极著名的书尾之言: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1999年的除夕夜,陪杨绛吃年夜饭的是司机小王夫妇、阿姨小吴。
按传统,瞻仰先生的遗容以示尊敬:
【待续】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