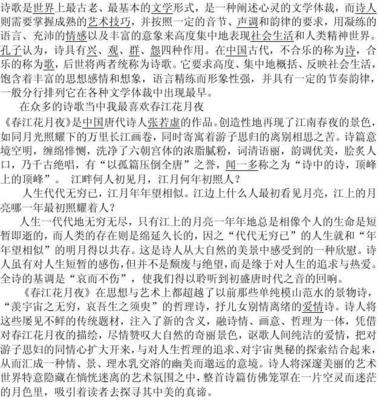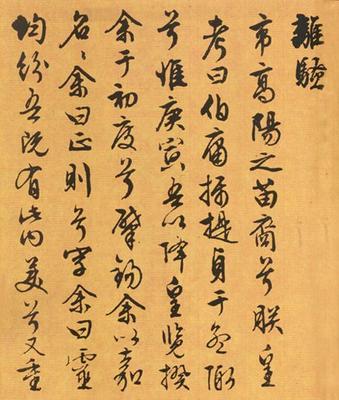虽然答这个题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但是还烦请想要找我麻烦的童鞋有点耐心,看懂我说的是什么再反驳,谢谢了,这是对答主最基本的尊重。你略翻一遍连我说的是啥都不知道,就自说自话一堆,我是很无奈的。
================================================
看这个题目下的一些答案看的火大。我也来答一下。
曾经因为这个问题在别的坛子里和人家吵过两次大规模的架。但是时间这么久了,我还是秉持着我一贯的观点:毛的诗词,自有其可观之处。但毕竟手段不足,驾势有余,空余霸悍二字,远不在一流之列。加之其身份的特殊性,对于他的诗词之评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过分拔高和过分贬低都存在,远远不曾有一个真正客观的评价。
题主既然问的是:仅从文学艺术上说。那么他诗词的得分可能会更低一些。
以上是我总的观点,下面分而述之。
一,诗是什么?格律这玩意儿真的是可有可无的么?
关于诗是什么,是最需要辨别清楚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讨论诗词类的问题,偏偏不在诗词的范畴内说话。这就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出现,譬如说:毛在填词格律上出差错,是因为故意要打破束缚,是因为要创新。再如,他写了一些主旋律题材的诗词,反映了爱国的情感,就在层次上高于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诗。
我可以说,这些都是主观的。我们讨论诗词,必须要在诗的内部讨论。什么是诗,我在个人的专栏里一直在写一个文言诗词的简易教程,正本清源的一个问题就是诗的概念,以下引文:
字典中对于诗的解释是:
【诗】:1.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歌。~话。(❶评论诗人、诗歌、诗派以及记录诗人议论、行事的著作;❷古代说唱艺术的一种)。~集。~剧。~篇。~人。~章。~史。吟~。2. 中国古书名,《诗经》的简称。
由此我总结出诗的概念,组成一首诗有两个必要条件:
A.语言层面【通过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
B.感情层面【反映生活,抒发情感】
由此我引申出:
A,是作为一首诗的骨架,即诗是要用语言来表达的,是要读出来的(有些时候还要唱出来)。在语言层面上,它区别于散文区别于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就是A,抛弃了A,则诗与其他文体的界限消失。
B,是一首诗的灵魂,我们写诗,最首先,是要表达自己的感情,《毛诗序》说:“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开宗明义就说出来我们要写什么。这些感情可以是最普遍的求不得爱憎会,也可以是很私密的个人情感,可以美好,也可以消沉。总之表达内心表达自我是一个写诗的人所要做的最艰难的事情,我们感受生活感受人生,然后通过A来达到B。
A和B的关系是:
1. B是A的最终目的。我们磨练技巧,我们学习庞杂的诗词知识,无非是为了获得理论上更大的表达能力,从而表达的更好。
2. A是实现B的途径。表达不是一句空话,没有扎实的功底,缺乏词汇量,不懂语法,不知韵律,就算感触再大,也只能手写不出你的心。说到底,空中楼阁是盖不起来的。
3. A和B一起构成诗。只有A没有B,是徒具样式的【匠人诗】,从概念上讲这不能算是真诗。只有B没有A,因为文体特征消失,自然不能算是一首诗。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四不像。
引文有些长,但我还是坚持引在前面,因为连讨论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讨论就没有意义了。
下面我继续做衍生:首先,格律这个东西的意义,你可以说是为了节奏感,为了音乐美,但是大家往往视而不见的是:格律是构成诗的骨架,是诗与其他文体放在一起辨识度的来源。很多人反感格律,其实是因为觉得是个门槛和阻碍,但是他们凑起来,却是五言的七言的,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打脸的行为,把五七言的样子当成辨识度的来源而忽略押韵这些,自欺欺人。
而太祖的一些东西明显是出韵出律的,这时候,就有很多人来给他辩护说:格律是小技,是束缚,他是为了创新和打破束缚才故意这样的,你以为他不能写格律正确的么?
所以他就写出来《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样的词了: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大家注意,这是一首无韵的词,胡适先生苛责过这个词不押韵,于是人辩护说这个是用湘潭方言押韵的,但是据胡适先生考证,还真不是。于是我们在网上随手一搜,辩护的人又来了:
胡适苛责《蝶恋花》的押韵,固然有理,却分明是看小了MZD(的审核啊)。此点押韵知识,他应是懂得的,只是他不愿损伤情感之发抒以迁就词法。
看看,我怎么说来着。其实根本不用给他辩护,此等程度的文辞和情感,毛完全有本事能够腾挪到押韵且表达的更好,但是他没有,这就说明了一点:他本身不在乎,而且他对于诗词不自觉。而其他的如《七律.长征》,写律而邻韵通押的,我认为完全是战争年代不方便查韵书罢了。大可不必为他找什么不愿损伤情感,刻意创新之类的理由。
为了做一个佐证,我们可以考察下毛自己对于格律的看法:
MZD对所作诗词的修改,有不少地方是着意调整用字用韵,使之更加符合格律的要求。毛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表明了他对写作格律诗词的见解。诚然,MZD的诗词对传统的格律,有很多突破和创新,但从总体上来看,MZD绝大部分诗词都是符合传统诗词格律要求的。譬如律诗一般在同一首诗中不用同字。特别是对颔联和颈联要求更加严格。《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其中的“水拍”原作“浪拍”,这就同“五岭逶迤腾细浪”中“浪”字相重了。所以后来作了修改。《MZD诗词选》中作者自注说明了这一情况:“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认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中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这位不相识的朋友,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这样虽与第二句的“水”字重复,但总比与第三句的“浪”字重复为好,且两个“水”字含义不同。同时,根据我们所见到的最早刊载在《外国记者印象记》上的这首诗,其中“云崖”原作“悬崖”,后来在《诗刊》正式发表时改为“云崖”。这样修改以后,这一句和下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作为律诗的颈联,对仗就更加工整了。“云崖”和“铁索”,不仅整个词相对,而且词的内部结构中语素与语素之间也相对。再如《七律·登庐山》中“跃上葱茏四百旋”中的“旋”原作“盘”。按照韵书“盘”属上平声十四寒,“旋”属下平声一先,修改以后,“旋”就与本诗中其他的韵脚“边”、“天”、“烟”、“田”一致起来,同属一个韵,读起来就更加音韵和谐,铿锵有力了。
大家可以通过这段话总结一下他自己对于格律的认知:他自己是此道中人, 他自己是知道格律是有多重要的,而且通过引文的几个例子,他自己很多时候也是爱抠这些东西的,譬如登庐山一首和七律长征一样犯邻韵通押的问题,他自己发现后便修改了。
所以他的态度还是很明显的,但是他不是个足够自觉的诗人。他有苦心经营的诗作,但是随手的更多,有抠邻韵通押这种问题的时候,却也有答李淑一那样连韵都不押的时候,所以我说他不自觉,而自觉与否,往往是分别一流和二流的关键,老杜渐于诗律细,大家可以体味一下。
我比较反感的,不是他本人和他的诗词,而是他的脑残粉们。俗话说:一粉顶十黑。江湖有分教:清新兰公子,俊逸措活佛。( 这句的作者大人)这两位深为脑残粉所苦,估计泉下都在别个诗人面前抬不起头。他的情况也类似,看看这些书上所谓专家的嘴脸,登庐山不能通押,改了就值得大书特书,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长征犯这个错误就略过不说,反正一般大家也看不出。犯了错误,就是对传统的格律有很多突破和创新。(至于创新与否,留到后面单独说)
二,传统诗词的审美自有其体系,好坏自有其评定标准。
我见到过很多人,他们质疑我往往会说,我看着挺好啊,朗朗上口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多好啊,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多好啊,就你嫉妒人家说不好。于是我往往就背上了一个嫉妒的大帽子,而后更有甚者,会抬出所谓的万金油:你行你上啊。
呵呵。
其实,传统诗词作为一个发展了几千年,脉络分明的艺术门类,其评价体系是很健全完善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往往浸淫其中的人一眼便能看出来。而在这个门槛之外的人,往往只能看到表层的美丑好坏,深入不进入,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于诗词的语境不熟悉,对于各个诗体的特征不熟悉,对于常用技法不熟悉,对于文言文不熟悉。
最明显的就是“名篇”《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我反驳这首七律是好诗,其实所谓的押韵错误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七律这个诗体,写得好和坏是最容易分辨的,所谓起承转合,并不是说死板的教条,而是满足这个诗体特征的运气法则,这么写出来浓淡合宜,最好看最舒服,而毛呢?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个首联说实话,从文字上其实是很一般的。以下,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五句各自单独叙述了一件事,我基本没见过这种写律的,因为没有疏密开阖,没有章法,这个律一下子变成了流水账,毫无蕴藉,一气泄了。尾句实则很无谓,三军过后尽开颜,刻意收住了。
后来我看碰壁斋主的《旧体诗杂想》,看到对这首诗的评论,感到不愧是当代最牛的诗人之一啊,说的比我明白多了,请看引文:
这首诗题材重大。不过,题材的重大,不能保证艺术的伟大,虽说它有可能辅佐出伟大的艺术。重大题材只是伟大艺术的“助产士”,而非“生产者”——那位做产妇的母亲。伟大的艺术需要母亲艰辛的孕育、痛苦的分娩,这是助产士不曾付出的;作为母亲的光荣、欣慰,助产士也就无权分享。在这地方,我们更不能势利眼,因为产科医生的权位,便奉承婴儿漂亮;不用讲,同样不必因为母亲的名位而谄谀婴儿。
这诗有个打眼的毛病,中间两联把四个地名齐头并列,军训时集合整队似的;耳朵灵光的人当听得见那四个地名报数时喊的“一、二、三、四”——这种摆法便太呆木了。骆宾王爱用数目字作对,给讥讽为“算博士”;毛也可当“地理教师”,因为他写得来像“方舆图”。古人对诗里用地名有许多讨论,譬如地名可不可以虚用,因为好些诗用起地名来跟实际的地理完全违背,不能拿方舆图来查对的;似乎明清人学唐诗的时候,有一派专爱把易于入诗的漂亮地名嵌得满版,作为诗诀,不过我没有详细考察,不知道他们是否用“我注六经”的态度在诗里注山经水经。前人讲究地名中的一条,便是要求把地名用得使人不觉堆垛。毛四句四地,加上“岷山”,一首诗里逛了五处山川。李白《峨眉山月歌》四句便用了五个地名,可是参差错落,叫人注意不到他在念旅游册子,所以古来很受赞赏。这首诗小孩子都会背,我们仍然引出来,跟毛做个对照:“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聪明地把几个地名嵌镶在某些关系中;“峨眉山”上的月,影子会落入江中,所以“平羌”勾连上了;他乘舟从“清溪”出发,去的地点是“三峡”,两者又亲近得不勉强;“三峡”峰高天窄,月亮看不见,他不免思念,便在这思念里顺流跑向“渝州。”他顺路而下,有事理、情理的关系网络其中,每个地名露面都有必然性,不像“半路杀出的”的程咬金那样显得突兀。地名并非路遇的、陌生不相熟的路人,而你呼我应、左牵右引,好像一伙儿朋友出门小游似的。这便破除了刻板。画家画多个人时,也让他们互相交谈、互相协作,处在某个情景中;这画才灵动自然,不像阅兵式的机械排列;这个道理跟诗歌写作是相通的。把毛跟李白相照,我们便不免觉得毛的写法堆垛得太齐整了。
毛写《长征》时,完全没有留意古人这方面的经验,他只向仓库里堆码箱子,而不曾试图向客厅里布置家具。他那四个地名像是按行军顺序讲下来的,可是文字里没有指明这个关系,也没有像李白那样,把这个关系来处理、影响地名。李白诗里地名间的关系有好几种,较为复杂。我们找得到与毛几乎如出一辙的地名关系,出在杜甫那里。杜甫名作《闻官军官收得河南河北》结句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同样的四个地名,同样的顺路程次序,而且更密集,只挤在两句中。看来,杜甫给自己提的要求特别苛刻,他不但要松动本来会有的僵硬,而且偏要用最僵硬的排列来创造流动、迅捷的效果,好恰合他胜利的畅快、回乡的迫切心情。他的办法简单之极,便是拿“从、穿、下、向”几个字眼指出顺承关系。他故意选用同带“峡、阳”字的地名,把刻板的那一面愈发加强些;只要有能力使刻板的东西流动起来,那么,愈刻板便愈把流动衬托得突出,刻板的能量掉个头全加到流动上面来了。好比打仗,只要能赢,对手愈强大,你的斩获便愈丰厚,对手所有的粮草、枪械,全给你虏掠过来。
毛诗四个地名完全平行,句与句、地与地之间不相闻问,也造成一个后果:诗意不曾推进、转换,只在原地兜圈子;他实际行军时顺地名往前走,在诗里呢,好像夜行军碰见了鬼打墙。类似的印象,读毛的其它作品时,都不同程度地遇得到,它使人觉得毛的写作过于平面化,缺少纵深感。单讲《长征》,那样地兜圈子,愈会加重刻板的能量。而且,他把四个地名偏挤在中间两联里,尤其要算失察。律诗那两联非得对仗,这种格律形式本来便僵硬,毛没有想办法避免格律的弱点,反而雪上加霜。毛那两联的句意都密得碰鼻子挤眼睛,不用虚字调剂,不但雪上加霜,霜雪更凝固为冰,越影响变化生动之感。黄庭坚写律诗的时候,常常一联疏一联密、一联虚一联实、或者一联写景一联抒怀发议论,使诗更为流利不死滞。他认识到律诗那两联对仗会带来先天胎里病,因而力图后天补救。毛看不起宋人,也许便看不到宋人的苦心、好处。
毛把中间两联写得那样浓得化不开、密得拆不散、板得挖不动,相衬之下,首尾两联便越觉疏薄。首联两句词意密度很小,因为下句只重复了上句。末联也稀疏,阅读时,我们先受了中间两联那样密重的压力,到末联时压力猛的卸掉,我们心里上会闪个趔趄,越觉末联轻飘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这样讲,咱们在末联忽的飘起来,正中毛的下怀,他所求的恰是这个效果,好拍合他行军完成的轻松之感。人各有见,我不争辩,只指出一点,这个看法见木不见林,无以开脱中间两联笨拙的板滞。统起来看,中间两联使得通篇不很均衡。古来传统里做七律的常法,总是倾力于中间两联,因此易于把首尾两联写得弱些。
……
所以,在这个写作、阅读的传统下,如果毛不排头用地名,中间不显得那样地压迫首尾,均衡问题也便无妨忽略;只可惜那两联太过度了,你想闭眼不见,它都还要来打眼、打开你的眼的。讲文章的常语有所谓“凤头、猪腹、豹尾,” 毛诗的中间确像吃饱撑鼓的猪腹;至于头,也许不必借书病所谓“蚓头鼠尾”来指为“蚓头”,可是,我们终觉它的尾有点儿像“虎头蛇尾”里那条蛇尾。
类似的,关于《沁园春.长沙》,碰公也做了一个评价:
对下片的另一个评价角度,是纯粹词学的。虽说它更贴合鉴赏的本职,倒不消化费多少口舌;这条正路短得很,几步便跨得完。
无论毛在下片的回答正确与否,合于他的思想与否,这个回答是借助词这体裁讲出来的,它会运用词的技巧,最终也构成词的艺术效果。我们读了“怅寥廓”那个气宏笔重的句子之后,再读下片,便觉没劲。好像碰见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不免大为耸动,凝神聚气地一拳打去,结果打中的并非麻老虎,而是只纸老虎;我们的心理扑了个空。下片笔力风格都显得轻飘飘,完全压不住、承不下那个好句。尽管他用的许多似乎昂扬、慷慨的陈词滥调,譬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万户侯、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些景象本来是豪放派爱请进作品里的常客,可是比较那立于“寥廓”、向着“大地”发的“苍茫”大问,尽成为泥人纸马,不经一搠。我们知道,常客必定不是贵客,再尊贵、珍贵的客人一旦来的次数多了,数见不鲜,也会降格得稀松平常,我们对他,不再重视。读词时,这些习滑用语也构不成审美的重大刺激。在连年累月、连篇累牍的滥用里,这些词汇已经磨损了,感觉也给它磨钝了,它像经千年流水打磨的卵石,没有圭角来刺人,感觉也生出老茧,不再会给它刺痛。这也是毛词吃亏的一个原因。可是,即便这些词汇还是头次上市,也卖不起“苍茫大地”那样的辣价钱。词的下片显得狗尾续貂,不相匹配,整首词也便头重脚轻,好像胖子跟瘦子玩翘翘板,下片给翘到半天云里,落不下地。我们对身体部位的偏向一向是重头轻脚的,艺术品却有点儿重脚轻头。假使一首词不是头重脚轻,而是头轻脚重,那便无人敢有微词了。跟着词读下去,感觉它的声音愈响愈大、情感愈转愈深、笔力愈下愈重、词意愈出愈奇,那是词家所梦想的大好事。反之便大非妙事。倘没有那么重的问句,这首词固然因此减掉它的点睛之笔,可也落个通体匀称;有它,词就像害甲亢,只一双大眼睛突兀地鼓出了。一个好句会成为通篇匠弊病,这是文艺里顶叫人头痛的问题,对于作者和读者,都像俗语所谓“猴子捡了生姜,吃又辣不得,丢又舍不得。”
下片比上片虚弱,似乎是他的慢性病,不时发作。譬如接下来一首《菩萨蛮·黄鹤楼》。上片说“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写得非常之好,小词这样大声镗鞳,叫人想来辛幼安、陈其年、顾贞观。可是下片说:“黄鹤知何处,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一落千丈,比了上片,不是“逐浪高”,简直是风止浪息了。他末句想挽回颓势,便拼命地使劲,就像低嗓门偏要唱高调门,憋着喉咙喊,愈见力气不足,古人讥刺学苏辛不成的所谓
“叫嚣”,便正是描摹这种窘态。《菩萨蛮·大柏地》与此类似。上片“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很好。下片“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江山,今朝更好看”,又比不上前片。
我们在《沁园春》里也看得到他词的句意密度很小,比方下片“恰同学少年”以下六句,竟只是一个层面的一个意思,太浪费不赀了。而且六句中几乎没有提供实象,全是浮夸、虚飘之词。整个下片只末句摄进来一个切实的画面。当然,即便通篇不写实而只发议论,也不足以构成缺点——想来毛不同意这个讲法,他会嗤之以鼻:“不懂形象思维”——可是,议论里有着着实实的意思,还是只有空空疏疏的套话,这依然可算作充实与虚浮的区别。
举这几个例子,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毛其实对于传统诗词的一些技巧的掌握,是很有限的,他是完全依照自己的语感来写诗的,换句话也就是不假控制,随手。而讨论诗在文学艺术层面的成就,古人积累数千年的审美体系是不可能绕过去的。这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从主观的角度,容易让人家叫好,但是在真正懂行的人面前,往往又逃不了被批评。这或许就是毛诗词水平评价两极分化的原因吧。
如何遣词谋篇,如何调和浓淡开阖,如何控制气息,这都是很大的学问。忽视这些而评论其诗词水平,我可以不客气的说,和不会负数的小学生,说初中生1-2减不过一样的。
三,他的好处在哪里,以及他是创新还是被笼罩?
毛在我眼里,虽然有诸多不满,但是不能不说,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绕不过去的诗人。他有很好的诗词,譬如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一句一直是我心里最好的之一。毛的气魄雄大,想象力丰富,这些都是很少的人才具备的天才。他作为一个诗人,又是直爽的可爱的一个人,他说自己学三李,其实只是学了李白罢了,他的好恶很明显,喜欢直来直去的,不喜欢宋后那些绕弯弯的路数,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是个足够有趣可爱的诗人。
另一方面,他的身份是雄主,是开国者,所以附加在诗词上的价值便更高,他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诗词作品也可以算作是史料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窥视他的思想,作为研究他的思想的材料之一。这是他的身份带给他的诗词独特的价值。所以无论怎么贬低,他的诗词都不会如很多人所说的一样不堪,所谓的抄袭论,枪手论,我从来都表示嗤之以鼻。毛的诗词,虽然诸多不完善,但是他的诗词不可磨灭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说他的诗词是对传统诗词的创新和开拓,我每次讨论这个话题,都会看到无数人用这个做为论点的。总之,一切不合适的东西都是突破,破体出律是创新,技巧粗疏是创新,宣泄而不控制是创新,霸悍也成了创新。
其实创新开拓哪里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不自觉和自己不加控制,完全不等同于创新。
毛的诗词,说到底,大家觉得他反叛,觉得他气魄雄大,突破了古典以来的审美,所以他是一个开拓的人。在我看来,他其实不过是古典审美的简单复刻罢了,哪怕是他的小令,也有辛稼轩陈其年在前,他所有的东西,其实都能向上追溯到可以笼罩住他的存在。说豪气,想象力,霸悍,这些都是复刻而不是开拓。之所以毛能带给我们他是传统的反叛者的感受,其实是他本身的气质和所处的时代而已,你看他所发出的感慨:谁主沉浮的话题古今说之不尽,萧瑟秋风今又是的感慨自黍离来也是说烂了,环球同此凉热也绝不是他的创见,至于他赖以震慑人的想象力,也脱不出李贺李白的笼罩。
而真正的创新,我直到当代的嘘堂等诗人,才看出了端倪。真正突破传统审美的,是现代性的进入,诗的疆土正在扩展,这些都与毛无关。
四,其他的东西。
1,我觉得首先是要排除意识形态进入诗的审美体系。国朝盛行所谓豪放婉约二分法,所谓豪放的、反映主旋律价值体系的,就是好诗词,相反的,纠结于小女儿态,写婉约的就等而下。周邦彦古来评价极高,到了国朝便不如刘克庄这样的二流了。
而传统诗词的审美体系从来就是多元化的。违背这种多元化的,其实都是开倒车。
2,从后遗症上来论述。毛的诗词在很多人心里减分的很大理由,其实是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诗的衰退,这几十年孕育出了一批老干体诗人们,毛是厥功甚伟的。譬如以下这种的,在几千年诗的历史上,都是奇葩一朵:
《庆祝十大在京召开》
十大春雷响碧宵,震惊中外看春潮。发言热烈如泉涌,策马腾飞逐浪高。
建树五年累硕果,浓香万里绽新苗。小康社会期全面,再创辉煌赶比超!
3,自觉与不自觉。
上面说了很多关于自觉不自觉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诗人对于诗的主动领悟和用力经营。譬如写诗到了一定程度,会不会去想什么是诗,我是为了什么写诗,我要表达些什么,我为什么这样表达,我怎么样能做的更好,我有什么地方可以下功夫,可以精益求精。
以前一个前辈跟我们谈诗,说过一段:
诗其实说来很简单,就是用语言表达情感。语言层面靠努力就可以过关,情感属于先天禀赋气质,也属于后天感悟修养。各有各的缘法,强求不来。语言层面过关了,就是文人。语言过硬,情感遥深,就是诗人。写得出人人皆有而未道之情,就是大诗人咯。所谓诗歌没有客观标准,那是就情感偏好而言的。在语言上绝对可以分出高低。如果一个人认为黄庭坚或者李商隐在七律上超过了老杜,这个人可以被认定是外行。因为那两位的错综变化远远少于老杜。同理,认为黄景仁像李太白的,那是在歌行问题上污蔑太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类似的情况,辛稼轩和吴梦窗,晏小山和纳兰性德,语言高下立判。稼轩和梦窗一点儿不难判断。
分别总结变化技巧,稼轩起码是吴梦窗的二十倍多。意象的重复性典故的多少,都可以比。所以大诗人都是无争议的,李杜光焰,二三流诗人反倒是容易激发论战。
大诗人,绝非偶然。诗人好当,大诗人要透过时代的复杂表面提供一种生活哲学。且是极具代表性的生活哲学。如果历史是一根棍子,能按上图钉的很多。 能钉上徽章的极少。个头要大,力气要狠,手法要准。才能钉上。写诗一样的。 格局大,笔力强,技巧高明,缺一不可。
毛是伟大的诗人,但不是一流的诗人。他的毛病太多。但愿大家有所体会。
以上。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