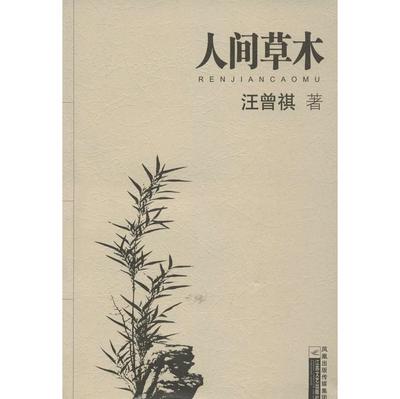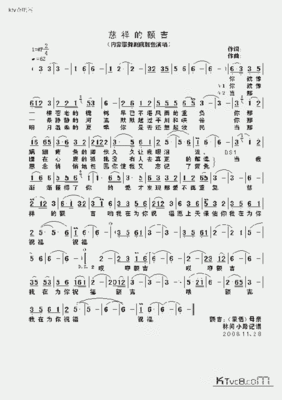很多人评价汪曾祺时,会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汪曾祺祖籍徽州,大约清朝时其家族迁至高邮。曾祖父在外地教过书,后来做生意几乎赔光了家产,他的祖父几乎白手起家重新创出了一份家业。他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了两百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是殷实人家。祖父中过拔贡,是前清末科,还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但是祖父生活俭朴,自奉甚薄。……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说起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我没怎么听明白,又不敢问个究竟。后来我问父亲:“是有那么一回事吗?”父亲说:“有!是一个什么大官的姨太太。”他的祖父亲自教过他古文,家里逢寒暑假也会请老先生为他讲解古文。他读各种小说,
(后院)山顶有两棵龙爪槐,一在东,一在西。西边的一棵是我的读书树。我常常爬上去,在分杈的树干上靠好,带一块带筋的干牛肉或一块榨菜,一边慢慢嚼着,一边看小说。
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巨大。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这些就是汪曾祺的童年与少年的家庭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汪曾祺是可以称得上一名“士大夫”的。
———————————————————————————————————————————
该如何评价汪曾祺其人呢?
才子。
书画,少时即佳;
唱戏,“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父亲)拉胡琴,我唱。”在西南联大时就演出昆曲、京剧,演话剧;
文才,带着恶性疟疾考上了西南联大中文系,王力、杨振声、闻一多、罗常培对他都十分看重,汪曾祺曾经替一名同学写了一篇关于李贺诗作的读书报告,闻一多赞赏有加:“比汪曾祺写得还好!”沈从文甚至给过他的习作120分(满分一百)的高分;日后因才气被江青钦点写样板戏,创造出“人走茶凉”等词句;
博学。
在大学时是夜猫子,夜里在图书馆读各种书,甚至看过元朝的菜谱,看西方文学、哲学,喜欢纪德、阿索林、弗洛伊德、萨特、伍尔夫。日后更是研究历史、民歌、京剧,涉猎颇广,还曾拟写长篇小说《汉武帝》;
有情趣。
举二三事即知。1935年夏,他考入江阴南菁中学。江阴河豚出名,肉鲜美,但吃来有危险。他的同学曾表示要带他去吃一次河豚,但未能如愿。半个世纪过后他仍念念不忘,75岁时他写了一首“河豚”:
鮰鱼脆鳝味无伦,酒重百花清且纯。
六十年来余一恨,
不曾拼死吃河豚。他还曾在下放到张家口期间给上百种马铃薯画图谱,画花和薯块,薯块画完就在牛粪火里烤熟吃掉,自诩没人比自己吃过更多种马铃薯;
日后回忆起赏识他的江青,他写道:
江青一辈子只说过一句正确的话:‘小萝卜去皮,真是煞风景!’我们陪她看电影,开座谈会,听她东一句西一句地漫谈。开会都是半夜(她白天睡觉,晚上办公),会后有一点夜宵。有时有凉拌小萝卜。人民大会堂的厨师特别巴结,小萝卜都是削皮的。萝卜去皮,吃起来不香。
是的,他是个「美食家」。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你能读到各种高邮美食、淮扬菜、昆明美食,晚饭花、葵、薤,昆明的糖炒栗子、汽锅鸡、火腿、菌、乳扇、乳饼、黑芥、韭菜花,北京的咸菜,故乡的炒米、鸭蛋、茨菰、虎头鲨、螺蛳、野鸭、鹌鹑、斑鸩、荠菜、马齿苋……他研究过宋朝人的吃喝,自创过一道“塞馅回锅油条”。各处吃,自己做,笔下写,他与美食是连在一起的。
———————————————————————————————————————————
汪曾祺曾开玩笑,自称自己是文体家。
他在小时候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功底;
高二时抗战爆发,汪家多处逃难。他曾在一个寺庙中住过一阵,带了两本文学书,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集。日后回忆初读沈从文小说时他说:“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
后来他考入西南联大,成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沈从文对他的影响十分巨大。沈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都选了;
大学里他又读了各种西方现代小说。他的小说早期是有意识地运用意识流等手法;
后来他进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下乡改造、当编剧,开始更多地学习、借鉴民间文学。
这些都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痕迹。
他推崇桐城派的散文,认为桐城派重文气、节奏,这些都是非常可取的。他喜欢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篇,有很多地方都有学他的痕迹。如悼念沈从文先生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的结尾
……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又如《我的祖父祖母》结尾: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回了一趟家乡,我的妹妹、弟弟说我长得像祖母。他们拿出一张祖母的六寸相片,我一看,是像,尤其是鼻子以下,两腮,嘴,都像。我年轻时没有人说过我像祖母。大概年轻时不像,现在,我老了,像了。这些平淡的语句,连着整篇文章,都令人落泪。
又比如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沈曾教导过他两点,
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汪曾祺有一篇《大淖记事》,小锡匠十三子因和巧云相爱被保安队长打成重伤,只有灌陈年尿碱才能保命:
十一子的牙关咬得很紧,灌不进去。
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在十一子的耳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
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
在这之后,汪曾祺忽然写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我的老师教我们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人不懂他这句话。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
———————————————————————————————————————————
汪曾祺的文学地位,我曾在 中写过:
在对“民族历史”的“寻根”趋势中,最重要的作家,非汪曾祺莫属。甚至可以说,汪曾祺一人之力,续接了自鲁迅至沈从文的“乡土”的文脉。(汪曾祺自称自己“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
贴几张汪曾祺和他的书画的照片吧: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