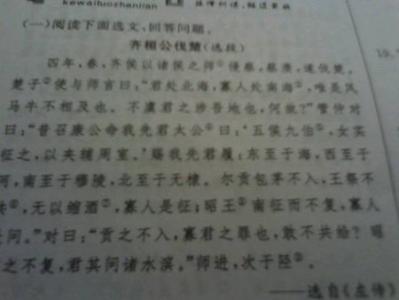说一部杨德昌导演的电影:《恐怖分子》。
一
2007年,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的大导演杨德昌去世,享年六十岁。
一年后,他的前妻蔡琴出了一张名叫《不悔》的专辑,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由香港导演罗启锐作词,李宗盛作曲。这首歌里有几句歌词:
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
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
人间不过是你无形的梦
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
以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
以身外身做梦中梦
我一直觉得蔡琴的这首歌是在唱给杨德昌听,斯人已逝,那些过往婚姻中的纠葛也早在时间里被风吹散了。很难说在蔡琴的心里究竟还有多少对杨德昌的怨恨,但可以明确的是,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杨德昌的人之一,蔡琴深知杨德昌的离世对台湾电影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电影意味着什么,对电影这门艺术意味着什么。
杨德昌去世时,蔡琴在公开信里写道:“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记录者;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
不知道杨德昌泉下有知,心里会生出怎样的波澜。
在说这部《恐怖分子》前,突然想到了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就算是对大师的一种缅怀吧。
二
华语影坛好导演不少,但称得上大师的,寥寥无几。
有人说中国最好的导演在台湾,我深以为然。就算“大师”的标准再高,侯孝贤和杨德昌都足以占据两个席位。
侯孝贤讲的是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而杨德昌拍的是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这两人之间很难比出高下,但于我而言,会更喜欢杨德昌一点。
很多时候,杨德昌像是个孩子,天真烂漫地注视着身边的一切,贪婪地用眼睛记录着他所看到的这个社会。他又像是一个历经无数沧桑的老者,敏锐地捕捉着生活中所出现的那些不易察觉的危险因子,用冷漠的口吻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

而在《恐怖分子》这部他早期的影片里,四十一岁的杨德昌用自己精准而又极具想象力的镜头语言审视着这个看似平静而又异常躁动的社会,在他的镜头里,台北不只是台北,更像是末日前的庞贝,处处弥散着危险的气息。没有人能做到心境平和,每个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却又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三
李立中和周郁芬的婚姻,像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周郁芬写作,李立中并不关心她写些什么。在周郁芬因写作没有头绪而苦恼时,李立中只会说:“放轻松嘛,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那么要命的事呢?”他不知道,对于周郁芬来说,写小说并不是要命的事,和丈夫无话可说,过着没有变化的生活,才是要命的事。
周郁芬在影片里写过这样一段话:“那天是春天到来的第一天,如果你了解季节,变化只是一种轮回的重复。这一年春天和往常没有两样,对他们这样一对夫妻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
影片没有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但所有的观众都会明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两样。
而李立中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两样”的人。在医院工作的他似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前一天的生活。他的生活早已模式化,连每天在卫生间的洗脸的时间,都像是固定好的一样。杨德昌多次给出李立中在卫生间洗脸的特写镜头,在暗红色的灯光下,水流的声音似乎放空了他内心所有关于人类的情感,他像是一台机器,似乎感觉不到压抑,荧幕外的观众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李立中在工作中也不算是个成功的人。没有背景,又不善言辞,小心翼翼,却难得到升迁。在组长因病离世后,他耍了滑头,本想借机爬到组长的位置,却功亏一篑。这样的小人物在我们身边不知道有多少,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实在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淡的不能再平淡。
周郁芬和李立中刚好相反。
以写作为生的周郁芬,大抵是个理想主义者。她不愿生活在无穷无尽的轮回反复里。就像她在后面一长段的独白里所说,她结婚是为了新的开始,写小说是为了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是为了新的开始......她做什么都是为了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看上去并不是一个难以完成的目标,但对于李立中这样一个丈夫来说,恰恰是难以实现的。
四
小沈出现了。
小沈这一角色的出现的一点也不突兀。在李立中和周郁芬的夫妻生活里,他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必然事件。
年轻时小沈就和周郁芬有过一段感情,也正是因为小沈娶了别的女人,周郁芬才嫁给李立中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如今小沈离婚创业,和周郁芬重遇,也就为旧情重燃制造了机会。
而比旧情更加重要的,是小沈对周郁芬的理解。
说起周郁芬的小说,李立中一无所知,他会费解“写小说怎么会变成这样要命的事”。而小沈会告诉周郁芬他看了她的小说,而且觉得其中一篇的主人公就是自己,并且为过去的事表示遗憾。
李立中尊敬周郁芬,待周郁芬很好,但显得是那样客套而疏远。而小沈对周郁芬则是一种骨子里的欣赏,他夸赞周郁芬的能干,并邀请她加盟他的公司。哪种相处模式对周郁芬更加受用,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在两人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对话越来越暧昧,笑容也越来越多,镜头转接,从面对面的谈话变成了两个人赤裸地躺在床上,也自然地无话可说。
在这里,杨德昌对于叙事手段的掌控娴熟到无以复加,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能这样凌厉却自然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在《恐怖分子》里,镜头的切换让人眼花缭乱,有的时候让人不得不感慨,两个镜头连在一起,在杨德昌这里不是加法,更不只是乘法,简直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作为一个真正的电影大师,他对蒙太奇手法的使用,神乎其神。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影片中那段以《Smoke get in your eyes》为背景音乐的蒙太奇,在黑暗的房间里,音乐声想起,被母亲带回家的不良少女淑安在静谧中躁动,她的母亲也不知在思索着什么。突然镜头一转,淑安的照片一张张出现在我们面前,摄影男孩小强和他的女朋友出现在画面里,音乐在一片狼藉中戛然而止,留给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
五
作为一部多线叙事的教科书式电影,不良少女淑安的线和摄影男孩小强的线虽然没有李立中那条主线那样强烈的戏剧冲突,却是推动整个故事进行下去的重要线索。
在偶然拍到从犯罪现场逃走的淑安后,小强疯狂地迷恋上了这个女孩。实际上,小强迷恋的可能只是他相机所捕捉到的那个淑安,那个看上去纯净清澈,又带着一丝叛逆的淑安。
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小强最向往,或者说最难拥有的,就是叛逆的自由。即将服兵役的他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了那种无法挣脱的拘束感。而看到在警察眼皮子底下逃跑的淑安,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看到了自己永远不能去过的生活。
可是幻想终究是幻想,淑安和小强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小强心中的悸动也只是单方面的意淫,淑安偷走了他的相机,也带走了他对于理想世界的最后一丝惦念。
于是小强找回了自己的女友,他明白现实中的幸福才是有迹可循的。
可淑安早就打乱了别人的现实。在家百无聊赖的她用一通骚扰电话彻底毁灭了李立中和周郁芬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生活,这样的安排看上去荒诞,却又十分巧妙。
六
淑安电话响起的时候,杨德昌给了一个空镜,在沉闷的电话铃声下,我们看着空荡荡的家具,仿佛看着周郁芬那张木然的面孔。
接到电话后周郁芬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让她看不到新意的生活。
李立中什么也不知道。他不懂周郁芬为什么会离家出走,也不懂周郁芬离家几天后回家为什么要收拾行李和他分居;他不懂周郁芬为什么会因为小说写不出而苦恼,也不懂周郁芬为什么想要一个新的开始。
在李立中的生活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陈旧的,哪里有新的开始呢?
在周郁芬离开李立中之后,她的小说获得了成功,像是一种讽刺,直到这个时候,李立中还从来没看过妻子的小说。
小强却发现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直偷窥着淑安的他知道那通电话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告诉了李立中事实的真相。
知道真相的李立中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周郁芬不愿意相信他,为什么周郁芬要离开他。
他在影片中说周郁芬“喜欢好东西,喜欢舒服的生活,可他给不了”,事实上他完全不知道妻子想要的是什么。
人与人一间最怕有座巴别塔。
七
失去了妻子的李立中也失去了升职的机会,本该成为组长的他并没有得偿所愿。
他不懂这个世界的规则,于是他活得拧巴,过得纠结,总是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带着一张扑克脸度日,最终连怎样去笑都忘记了。
所幸他还有个做警察的朋友,而这个朋友有一把枪。
在影片的最后十分钟里,他拿着枪杀死了不让他升职的主任,杀死了小沈,也把枪对准了戏弄他的淑安,可一声枪响,我们才知道,这一切只出现在周郁芬的梦里,李立中杀的,只有他自己。
当蔡琴的《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的歌声响起,李立中倒在警察朋友家的浴室边,头上流着鲜血,却像是早都已经死了。
杀死他的,是沉重的让他喘不过气的生活。
只有生活,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在恐怖的日常生活里,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当恐怖分子在空气中扩散,伴着影片中出现的那些嘈杂的车声、犬吠,我们才会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脆弱,生活中那些看似微小的琐事是多么地致命。
八
《恐怖分子》1986年上映,那年缪骞人二十八岁,李立群三十四岁,金士杰三十五岁,杨德昌三十九岁。
那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现在眼中的老戏骨李立群、金士杰在那时就已是戏骨,杨德昌那时也还风华正茂。
缪骞人那时已结束了和周润发的恋情,拍了《投奔怒海》、《最爱》这样的电影,拿到过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而如今她早已嫁为人妇,成为那位拍过《喜福会》的王颖的妻子。相信很多人年轻人并不知道缪骞人的名字,也没见过她的倾城之姿。
那时的台北在杨德昌眼里像是李立中的生活般压抑。人们为了生计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似乎得不到快乐,不安和躁动掩藏在平淡下面,透着格外的恐怖。
时间过去了三十年,我们的生活似乎也是这样。
三十年过去,好像并没有出现周郁芬口中新的开始,所有的一切还是一如往常。
可生活总在继续,即使没有新的开始,也不能止足不前。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这部电影,影片结束的时候全场起立,掌声足足持续了半分钟之久。
真正好的电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以上。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