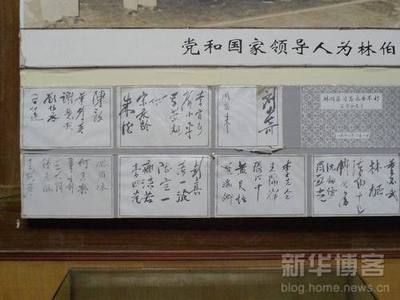王津进故宫修复钟表39年了,在纪录片播出后,他一举收获了“故宫男神”的美称。故宫文物修复实行学徒制,他就算是钟表修复的第三代传人。在39年里,他陆陆续续修复了两三百件宫廷钟,故宫钟表陈列馆里,很多都是他年轻时候修过的钟表。在第一集靠近片尾的地方,王津站在钟表馆里,对展览的每一件钟表都如数家珍。它们都被修得好好的,上满了弦,稳妥地静静地安置进陈列玻璃罩里,他说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就感觉它们都是活生生的,但现在这样就摆着,我就有点心疼”。
屈峰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在是木器修复组的科长,在第二集的片子里带着自己 的小徒弟修复了一件辽金时期的木质佛像。佛像送来的时候,断了两个手指头,下嘴唇缺了一块,腰上的飘带也断了。修复过后,他得意洋洋地问别人,你找找看补哪儿了。当佛像要被移去展示厅时,屈峰依依不舍到了小心眼百般挑刺的程度,先是嫌弃搬运工捆绑的不好,
临走了又拿了纸把佛像的脸盖住,临走了又拿了纸把佛像的脸盖住,佛像走远了,他还在门前的藤下站着望了很久。佛像走远了,他还在门前的藤下站着望了很久。在第三集中则讲了一个关于书画临摹组的故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已经年近花甲的冯忠莲大师花了十年的时间临摹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冯老师在01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如今她的徒弟郭文林也已经退休返聘了,他回忆起冯老师当时临摹《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没说太多,只说冯老师当时要每天从库房里领出原画,到晚上了再还回去;又说临摹师一辈子,也没有几个十年临不了几张。《清明上河图》原本是故宫的一大珍宝,而冯老师的摹本也成了另一大珍宝。
在对修复大师们的采访中,许多人都提到过,故宫里的这些文物是活的。钟表组的王津提到过,木器组屈峰提到过,镶嵌组的孔艳菊提到过,陶瓷组的王五胜也提到过。这其中,屈峰讲的最明白,“有些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有些就是愁眉苦脸……那种神秘的纯净的笑是最难刻的……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把椅子……所以故宫里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因为这些人在制物的时候,总是要想办法把自己融到里头去。”
如果说先祖们在制物的时候融入了自己,那么在千年后重新对文物进行修复与文物进行对话的修复师肯定也在修复中融入了自己。所以他们愿意把这些文物看做一个个有生命有灵魂的个体,维系住它们的生命,把它们细心地打理妥当,还以尊严,把它们最好的样子重新展示给大家。所以王津看到钟表馆里已经修复好的钟表,却终日喑哑,指针停滞不前,会心疼地叹一口气;所以屈峰看到木佛像被躺平了捆住,会生气,会想盖一张纸聊胜于无地遮住它的脸;所以冯忠莲会在自己盛年时期就退出了国画创作,在故宫里默默无闻地临摹古画一干就是三十余年。
这些老师傅常说,修复文物干了几十年一辈子,能碰到一件稀世珍宝就算是幸运事。但反过来想想,这些蒙尘了千年的文物,能在漫长的光阴里碰到一位手艺高超尊重文物也尊重文物修复这个职业的修复师,是更为难得的幸福。

故宫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工作场所,这里极美极神秘,也极静。纪录片中有这样一幕,周一故宫闭馆,陶瓷组的纪东歌骑着自行车经过空无一人的太和门广场,话筒里能听到有风呜呜地吹过,周围高大的建筑群显得有些陌生。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地方,很多人工作的地方在西三所,这里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冷宫。也许大家每天早上走着去提开水的路,当年被打入冷宫的嫔妃们也曾经走过。
在这样名副其实的“冷宫”里工作,没有几分爱和坚持是没办法支撑下去的。镶嵌组的孔艳菊是从中央美院毕业的,当初来故宫工作纯粹是因为父母想要子女留在北京找份安稳活儿。她以为故宫只是个旅游景点,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是个博物院。她说的很明白,文物修复的工作是和社会完全脱节的,——“一进那大宫墙,之后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静得我都不敢说话。“——大约当年一夕之间走入冷宫的嫔妃也不过这般感受了。
在这幽静又封闭的环境里做着关于修复文物这么繁琐的活儿,时间久了,大家的脸上都有了一种特殊的气定神闲的感觉。有的老师傅在院子里养了十分漂亮的八哥,有的种了西红柿和茄子。王有亮老师在修青铜器的时候一边利索地下手一边嘴上罗里吧嗦地解说几句,带着徒弟修完太后的海南黄花梨大柜子之后,还十分镇定地表示自己要去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他骑上小电驴,出宫门吸烟去了,故宫不准师傅们吸烟。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萧寒曾经说过,自己很惊讶这部片子居然打动了那么多人,这让他不禁想起《从前慢》里的句子,从前慢,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一生也只能干一件事。
故宫修复的各个专业可能会或多或少借用了现代高科技装置,但传统技艺的传承依旧严格遵循着拜师学艺的学徒制。老师傅们修文物的时候,也时常会开玩笑,这要是修不好,搁以前可要被皇上拖出去砍头了。在西三所的冷宫里,时光好像真的可以静止。漆器组的科长闵俊嵘进故宫工作在修复漆器的时候,用的依旧是自己调配炼制的天然漆,连生漆,都是他夜半里和采漆人一起翻山越岭采集来的。他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漆树,时不时地要浇水,——“过两年就可以割漆了。”
就是那么一刻,我深深意识到,这些在故宫里寂寞修复文物的人们,是真的爱这份职业,爱到要认认真真死心塌地干上这么一辈子的。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