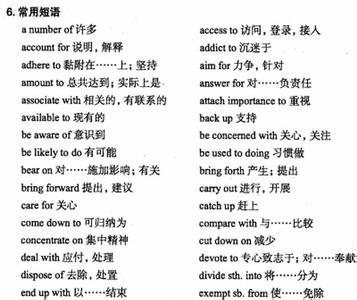一
轮到我比剑的时候,夕阳下沉,青灰色调的道馆泛起红色。佐藤先生坐于榻榻米上,声如洪钟:
“赤星因彻。”
我站起身,走到场地中央,对面,加藤也正手执竹刀,站姿戒备。我右手握紧刀柄,掌心汗水冰凉,望向四周,北辰一刀流的弟子们正襟危坐,没有表情。
我和加藤相互屈身,直至半蹲之姿。刀缓慢前伸,是拔刀动作,仿佛将刀自一无形的刀鞘中拔出,最终刀尖相对。
“开始!”
缓缓站起,各自后退一步,接着,我和加藤都静止不动。此刻,道馆鸦雀无声,呈现着浑然静止的状态,从加藤收缩的瞳仁中,我看见时间正在局促地流淌。"谁都不动的时候,就看眼睛。"佐藤先生说,"敌人的眼睛里有动作的预兆。"
我没能看出佐藤先生说的预兆,我看到的只有自己,在加藤漆黑的眼眸里,是目光近乎呆滞的自己的脸庞。这会是一个武士?当我第一次执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突兀地冲入脑海,现在,它孤零零地悬在加藤的眼眸中,剑尖和我的头颅,构成武士之道的符号。
我的父亲是一个为藩主饭菜试毒的下级武士,每年拿三十石的稀薄俸禄,他的工作,是和他的同事一道在藩主吃饭之前吃上几口。八岁的时候,我被送入佐藤先生的剑道馆学习剑术,我的父亲说,剑是武士之魂。因彻啊,你是武士的儿子啊。我的父亲目送我踏入剑道馆的门槛,他在门外对着天空喃喃自语,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在和我说话。
我很小就发现自己握不紧拳,而这或许是我剑术糟糕的原因。当我握拳的刹那,我的胸口会泛起撕裂般的疼痛,疼痛使我的拳心总是留下一枚黄豆大小的空隙,而当我手持竹刀,我掌心的绵软使得我对一切劈刺动作都力不从心,虽然我努力去学习每一个招式,但三年里十二次比剑,我从未胜过一场。我不多言的父亲在得知我的剑术成绩后变得愈发沉默寡言,他用干枯的声音频繁地重复着昔日送我入馆时说的话:因彻啊,你是武士的儿子啊。声音拖得漫长,在我学剑的三年里串联成一曲低沉的吟唱。
学满三年,我们迎来了道馆的第一次考核,两两比剑,由佐藤先生进行评判。我第一次对阵加藤也正,他此前的成绩是九负一胜,师父做出了尽可能让我们体面的安排。预兆悄无声息地来临,加藤眼睁一线,剑霍然刺出,我抡起刀,下一瞬间,掌中竹刀坠地,加藤的剑击中我的咽喉。
“你真是连刀都捏不住的孬种啊。”
我被佐藤先生驱逐出馆,在他的四十二名弟子中,我是唯一一个。佐藤先生说,我是一个不能拿剑的人。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步出道馆,喉间依旧泛着甜腻的气息,在我抡刀的瞬间,我感觉血气自我胸口上涌,当刀脱手的瞬间戛然而止,停留并弥漫在我的咽喉。
我的父亲在得知这一切的时候有着平静的口吻,他的目光流露出一反常态的犀利。“我来给你看几样东西。”他把我带进他的和室,我的面前摆放着长短两把刀、一块棋盘和一黑一白两颗棋子。“它们只是装饰。”我的父亲露出痛苦的神色:“这是武士的遗产……我没有珍惜。”
我知道它们的渊源,它们传自我的祖辈,两把刀长为太刀,短为肋差,它们是武士象征;而黑白两色棋子原有各一百八十颗盛放于楠木罐中,后来被我祖父典于当铺,只剩下两枚棋子徒留纪念。“我都不会。”父亲的声音变得含糊不清:“我为主公试毒……我退休以后,就轮到你啦。”
我默然无语,抽出长刀,刀出鞘三分之一,刀光可鉴人影。此刻,喉间黏腻的气息再次涌现。掌心一松,刀与刀鞘一并落在地上,刀自刀鞘滑落,我看见完整的刀锋,金属光泽下,隐约有着赭色的暗纹。
“你真的握不住刀啊……”
父亲喃喃自语的时候,我拈起白子,食中指夹棋,无名指小指上扬,手形状如飞鸟,这是正确的落子姿态。我时常看见街巷间的三教九流摆开棋局,我耳濡目染,第一次落子便无师自通。我抬起手臂,前臂举高,将棋子重重拍下,棋子与手臂一道划出弧线,我愣住,这分明是刀砍杀的姿态。
我几乎是一下子就迷恋上了打子的动作,反复用棋子敲击棋盘,打子酷似抡刀,棋子落于盘上,仿佛长刀入肉,每落一子,如同杀一人。我疯狂的打子动作被父亲打断,后来他告诉我,当时我的表情有着疯子般的错乱,他抡起刀鞘在我的脑袋上重重砸了一下,紧接着是一声大喝:
“去学棋!”
二
三个月后,我拜入围棋四大世家之一的井上门下。
父亲对于我的学棋之路有着清醒的认识,我现在学棋已经为时已晚,在无棋力的情况下拜入四大世家几无可能。因此父亲带我求教了本地寺子屋的水岩先生,他有一张十四级的免状①,可以教我入门。
我在水岩先生门下学习了三个月,从让九子一直下到分先可以战而胜之,水岩先生夸我有学棋的天赋,但距离拜师四大家还为时尚早。父亲说现在去试一下亦无妨,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大世家,被一家拒绝,还有三家,为什么不试试运气?
我到井上家的时候樱花凋零,一地残红仿佛碎玉。我在家丁的引领下穿过绿肥红瘦的花园小径,走进一间六坪的和室,房间空旷,只有一双蒲团,一副棋具。他们派出一个年纪和我相仿的男孩以试我棋力,由我执黑先行,我高举手臂,如抡刀般打下一子,棋子裂开,片刻,碎成三片,形如破碎的樱花。
然后我听见一声刺耳的尖叫,这个眉清目秀的少年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我目送着他清瘦的背影冲出屋门,他留下令我费解的字眼:
疯子!
我在当天下午拜访了井上家家督井上幻庵因硕,这是井上先生的亲自召见,这个正襟危坐的男人有着狞恶的长相,黑紫脸膛上黑斑密布。“井……井上先生……”我垂首而立。“坐。”井上先生说,手指向棋盘对面的蒲团。
“下一手吧。”
我愣住,迟迟不动,不让子?这怎么可能?我紧张地凝视着井上先生,井上先生咧开了嘴:
“下一手,像上午一样。让我看看。”
拈起黑子,举高手臂,有了执剑砍杀的心念。手臂下沉,视线撞上井上先生目光,手臂竟无法下坠,仿佛被匕首钉死在半空,前后洞穿。深吸一口气,向下挣扎,刹那间感觉皮开肉绽,棋子落下,声音微弱,如同呻吟。
“你几岁?”
“十二岁。”
“十二岁?”井上先生飞快落下一颗白子:“你学棋多久了?”
“三个月。”
“咦?”井上先生手臂稍抬,落下一子,我凝视着它,以它为中心,棋盘上的木纹好像泛起涟漪。“在门下三年的弟子,和我对局,竟下不了一手,他像上午和你下棋的山田一样落荒而逃,”井上先生忽而抽出怀中折扇,戟指向我:
“究竟几年!”
“三个月。”
我被井上先生收入门下,成为他的一名内弟子。内弟子住在师父家中,师父包揽吃住,而弟子在学棋之外要为师父干起居活。我得知上午和我下棋的山田弘一已经是第三名内弟子的候选,在十二岁的少年当中,他的棋力最为出挑,但最终却被我这个新来者取而代之。
临行之前,父亲在我的包裹里放入短刀。“这是肋差,用以近战或切腹,”父亲拿起肋差,在腹部比划了一下:“切莫拔此刀,除非杀人,或者自杀。”
我在训练中的第一个对手是井之原太郎,这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落座后在棋盘上放上八颗黑子,微鞠一躬:“赤星君,请多指教。”接着打下一子。我愣住:“井之原君,这是?”井之原说:“师父的意思。赤星君,请开始吧。”
这盘八子局以我的大败亏输而告终,当下到一百二十多手的时候,黑棋已经支离破碎。井上家的门人围拢上来,观棋不语的规范使得他们在注视着这盘可笑的对局时都保持着缄默,而他们脸上窃喜的表情使得这肃静的场面变得荒诞绝伦。井之原坐姿端正,他神情肃穆,像是在苦思冥想,他正以当局者的身份一并参与了这场闹剧。
我看到了山田弘一,刚刚结束对局的他从对面走来,他的余光瞥过我们的对局,脚步依旧匆匆,仿佛视而不见。我投下一颗黑子示意认输,井之原冲着山田弘一的背影喊:
“山田君,我替你报仇了!”
围观者爆发出按捺已久的笑声。山田弘一停下脚步,背影如刀削:
“井之原,我跟你下。”
“什么?”
山田弘一回过头:“我们把这盘棋下完,我执黑。”
我和井之原不约而同地站起,围观者仍旧愣在原地。山田弘一坐上我先前坐的蒲团,拈起我认输的那枚黑子,接着,一子落于天元。
三小时后,黑棋三目胜。山田弘一坐在蒲团上,目露凶光:
“赤星君,我替你报仇了。”
我在井上家的第一盘棋是之后很多盘棋的翻版,那些比我年龄大很多的棋手对我毫不容情。师父对我的胜负抱着熟视无睹的态度,只是有一次,他问了我一个和胜负若即若离的问题:
“你知道你的对手为什么都比你大出这么多么?”
“师父,我不明白……”
“和你同龄的孩子,没人可以和你坐在一张盘前。”师父说:“你盛气凌人,少年无可抵御。棋道和剑术一样,最优秀的剑士,能让对手不敢拔刀。”
“可我还是输……”
师父的脸色忽而变得和蔼,他一贯沙哑冰冷的声音这时候有着慈父般的亲切:
“没关系啊。你去拿棋盘,我们下一盘吧。”
三
我在师父家中度过了五年,黑白在棋盘上堆砌瓦解循环往复,仿佛昼夜交替。时过境迁,我让井之原之流五子绰绰有余,他们与我对局时,会不时带着羞赧的微笑。
我和山田弘一的对局并非师父安排。自我入门之日的第二日,师父把我们唤至跟前,明令禁止我们之间的对局。山田在一次训练后叫住了我,时隔五年,他成了一个胡茬坚硬的少年:“赤星君,五年里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不置可否:“为什么师父选我?”“不,”山田弘一的脸颊悲哀地抽搐:“五年之前,为什么我会逃跑。”
我仿佛看到一把刀,它悬于山田弘一的头顶,如流水倾泻般劈落下来,最终在山田的头颅上一闪而没。我的喉咙泛起甜腥的味道:“找到答案的方法,是再试一次。”山田点点头,他的表情变得诚恳:“我看过你的棋谱。我觉得我可以让你先。”
“确实可以啊。”我说。
我和山田的对局是在那次对话的三天以后,那天是我每个月回家探亲的日子,我可以搁下每天的的洒扫尘除,去看我父亲,或者拿着十几文钱去逛街市。我们约在第一次对局时的那间和室,和室外,四月的樱花烂漫成灾。“感觉像是又活了一次呢,”山田弘一坐下来:“谢谢你,赤星君。”
“我欠你一条命啊。”我拈起一颗黑子,又放回棋罐:“如果我输了,我会切腹。”
“啊……”山田嘴巴微张,眼睛睁大。
“如果我赢了,”我重又拈起棋子:“那么五年之前,你就死得其所。”黑子打下,我看见棋盘的纹路泛起涟漪。山田仍旧张着嘴巴,他的唇角聚集着一圈口沫,白子落下,居然杳无声息。
白棋诡谲近妖,这并非山田棋风,山田素来尊崇师门,他的棋风从来大开大合。但我预想中的砍杀在盘上并未出现,白子凝聚在黑色的锋芒周围,仿佛一匹卷起刀刃的白雾,刀锋过处,竟是触不可及的幽灵。
我赢不了,武士的刀杀不死幽灵。我看向山田,一丝晶莹的唾液从他的唇角流下来,他的嘴巴合上,但是嘴角却歪向了一边。“山田君!”我喊道。山田目光空洞:“下棋呢!你吵什么!”
我输了三目,意料之中。我对山田鞠一躬:“山田君,我会切腹。”山田对我的话似乎浑然未觉:“复盘啊。”我点头:“好。”我们按部就班把棋摆了一遍,我几次想说话,都被山田打断,他用浑浊不堪的声音重复着:
“为什么啊。这……很难啊。”
我需要一名介错人②,在我切腹时砍下我的人头,我听说藤堂川的剑术不错,在拜入井上家时已获得镜心明智流的免许③。藤堂川听闻我要切腹时大惊失色:“赤星君,原谅我不能帮你的忙。”言罢匆忙出屋。
藤堂向师父报告,我切腹的消息不胫而走。师父赶到,我们身边围了一圈门人。“为什么?”师父微微睁大眼睛。“我输给了山田。对局之前,我有输棋就切腹的承诺。”“你有刀么?”“有。”“哦。”师父转向藤堂:“那你就满足他的要求吧。”
“我办不到……”
师父没有理会藤堂,他转向我:“去洗个澡。然后换身干净的衣服吧。”
切腹的地点是在井上家的庭院。我换上白色的和服,跪在一张雪白的垫子上,垫子前是我的肋差,它被白色的丝绸裹住。藤堂川站在我身后,他的腰间挂着长刀,井上先生对他说:
“你们都商量好了吧。”
“是,”藤堂说:“十字切腹。肠子流出来的时候,我会抱首④。”
我揭开和服,上身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庭院里暗香浮动,樱花的香有着淡淡的甜味。我拔出肋差,出鞘的竟是把寻常铁片,铁片上,锈迹斑驳。
深吸一口气,樱花香有了腥味,我看向师父,师父对我摇头:
“开始吧。”
“为什么?”
“入门之日,你的父亲把他的刀充作学费。”
世界开始变暗,人脸上像是蒙了一层灰。淡粉色的樱花逐渐变黑,花分五瓣,轮廓是五年前那颗黑子破碎的模样。我看见五片樱花瓣向我飞速逼近,它们重击在我的面门,脸面一凉,接着,我听见玉石坠地的声音。
地上是黑子的碎片,五颗,形似樱花。眼前,山田弘一龇牙咧嘴,面目狰狞。“你还留着啊。”我说。山田忽然跌倒:“你真要死啊。”话音未落,抬起和服袖子,掩面而泣。
山田被门人拉走,须臾,刀切入腹。感觉身体下沉,沉到肚腹,顺着刀锋,从身体里缓缓淌出来,它们跌落在白垫上,哗哗有声。
“斩吧。”师父说。
藤堂长刀劈落。我的双手脱离刀把,身体加速下坠。“结束了?”我含糊地说:“原来……这么快啊。”
醒来的时候,暮色昏沉,肚子上缠着白布,藤堂坐在我身边。“你的刀明明下来了。”我对藤堂说。
“师父让我用刀背打你的手。”藤堂说:“但是……挥刀的瞬间,真的很想杀人啊。”
“我能理解。”
“这念头使我觉得可耻。为此我要照顾你。”
我卧床期间由藤堂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半个月后,师父来看我。身体有了坠落的感觉,我咬紧牙关:“师父,您为什么不成全我,或者阻止我。”
“我不想你寻死,”师父说,“但是棋士如果死过一次,就什么也不会怕了。”
“郎中说,假如刀再往里半寸,就没得治了。”我说:“现在想起来,还是活着好啊。”
“刀锈得厉害,否则你就死了,”师父转过身,肩膀微微耸动,他往前踱了几步,说:
“五年之前,山田死过一次。五年以后,他终究没有活过来。你有时间,就去看看他吧。”
几天后可以下地,我在院子里见到山田,当时他在采摘樱花。他摘下一朵,把它们剥成五瓣,接着专注地撕扯着剥下的五片花瓣,目光时不时瞟向自己的脚下,他的脚下隆起了一堆土。我走到山田身边,山田看了看我,嘴角忽然流出了口水,口水滴在地上,啪嗒,声音清脆。
土上摆着黑子碎片,一共五颗,棋子周围,散乱着一圈花瓣,花瓣轮廓,酷肖当年的碎子。
“还能下棋么?”
“你把棋子给他,他会往嘴里送的。”藤堂干涩地笑了:“把土堆起来,撕花,摆好,这么些天,每天都这样。”
“土里有埋着什么吗?”
“我们翻土找过。没有。”藤堂说:“走吧,别打扰他了。”
“他终究是没活过来啊。”
“什么?”
“你们应该找的到的。”我剧烈咳嗽,感觉血腥气涌出了喉咙:“他埋的,就是他自己啊。”话音未落,眼睛瞥向土堆。
土堆上,有了斑斑红点。颜色深过樱花,浅过棋子。
四
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升到六段,被师父特别推荐参加一年一度的御城棋。每年霜月中旬,四大家的高手齐聚江户,在中奥黑书院弈棋,由于时间紧张,棋士在此之前就将棋在别处下完,届时再在江户城将军御前复盘。我的对手是林元美,五十七岁,是林家掌门。
对局的地方是一间六坪房间,我和林元美坐正中,两侧分别坐着井上家和林家棋士各两位,还有一名记谱的小姓⑤。我执黑先行,落子声音响亮。林元美皱起眉头,半个时辰后打下白子,他的动作很慢,棋子落下,无声无息。
这一幕似曾相识。我抬头,与林元美目光相接,这个老人的眼睛炯炯有神。我重重拍下一子,棋子震动,略微偏离原位,林元美伸手,扶正我的黑子,闭上眼睛。
一个时辰过后,林元美睁眼,打下一子,仍无声息。
自巳时三刻,一直到夕阳下沉,我们的棋局进行了不到二十手。林元美着着长考,一手棋至少要花半个时辰。“晚上继续吧,”林元美转向身边的井上棋士:“要不,你们先去休息吧。”
晚上,灯光亮起,井上家和林家的观战者离开,只剩下呵欠连天的当值小姓。林元美下得快了一些,曙光将现,盘面上一百手不到。“有点累啊,”林元美说。接着,改正坐为盘坐,闭上眼睛。
一个时辰后,我被师父拍醒。睁眼的时候,发现自己上身仆倒,头靠棋盘,像是切腹死去的武士。我坐起,师父凝视着林元美,目光收缩。林元美说:“你的徒弟,精力很旺盛啊。”说话的同时,将被我脑袋弄乱的棋形复原。
我伸手想去协助摆棋,手背忽然一痛。师父折扇敲下,边缘棱角击中我的掌骨,我下意识缩手,师父的扇子往前扫去,盘上的棋子纷纷坠落在竹席上,沉闷的响声此起彼伏。
“你干什么!”
“这盘棋,到此为止!”
林元美低头,沉默注视盘上零落的棋子。东南方走来一胖大之人,僧人打扮,却腰间插刀。此人是本因坊家督丈和,身居名人棋所,名人是棋坛最高领袖。丈和笑容满面,轻拍师父肩膀:“你徒弟只有六段,本没有参加御城棋的资格,因你一意推荐,幕府才破格同意。你现在出尔反尔,是要将幕府置于何地?你要三思后行啊。”
“这不是下棋,这是决斗,”师父没有理会丈和,仍注视林元美:“杀人诛心,为何要做到这种地步?”
林元美抬头,眼纹颤抖。丈和转向我,他的胖大之躯居高临下:“因彻,你说这棋是下还是不下?”
“下啊。”我说。
丈和笑容满面,两只眼睛仿佛出鞘双刀。师父转向丈和:“三年之前,我已经逆来顺受。但我的徒弟,我会拿命去保。”
“徒弟还会再有,”丈和手握刀把;“名人却只有一个。”说完,转身出屋。
棋局续弈,战斗趋于白热。白子一子落于黑棋腹地之中,是凌空一击,仿佛忍者的手里剑。杀心大炽,我迅速落下一子,棋子落盘的声音仿佛刀剑相击,棋盘上,黑白两颗棋子空悬当央,相互紧贴。
午饭时候棋局暂停,饭后是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我在书房小睡,师父把我拍醒。“为了毁掉你,林元美通宵达旦,”师父说:“你称病即可,我会上书幕府,为你开脱。”
“这是双刃剑,他也会深受其害。”我说:“我的身体比他年轻啊。”
“林元美身经百战,在他身体垮掉之前,你的心灵会先扛不住!”师父说:“你会步山田后尘,这就是林元美的目的,他是在以命相搏……而你也是啊。”
“可是……林家与井上家并无宿怨,他豁出性命,是图什么?”
“我不知道,但一定与丈和有关。”师父说:“你进步神速,将来会是威胁丈和名人地位的最强人选。丈和借刀杀人,林元只是杀人工具。”
“如果林元美做到的话,丈和会给他什么吧。”我说。
“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师父说:“可是林元美……这老头不是被骗过一次么?”
师父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本因坊与林家曾一度蝇营狗苟。三年之前,丈和欺骗师父签下允诺他当名人“备忘录”,经由林元美携“备忘录”与幕府元老暗通款曲,幕府才下达旨意,授予丈和名人之位。事前丈和允诺林元美,若当上名人,将以名人身份颁发林元美八段免状,不料事后丈和出尔反尔,八段承诺只字不提,林元美自觉被骗,却只能无可奈何,事发一个月后,大病半年。
“我已经死过一次,”我站起身:“神会眷顾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吧。”
师父转身,肩膀颤抖,脊背如同断崖:“你不该去斩他的剑。而是应该斩他掷出剑的手。”
巳时三刻,棋局重开。黑棋腹地内,林元美的白子撒豆成兵。鬼魂仍有征兆,但林元美的棋根本无法捉摸,忍者的剑,从来绝处逢生。
去斩他的手……我的视线避开应接不暇的飞来之刃,盘上陡然开阔;棋盘左侧,白棋一串孤子悬而未决。我不理睬突袭的白棋,黑子落下,悬于那串孤子当央,仿佛长刀刀锋高悬在上。
盘上,双方各自行棋,三回合后,原本固若金汤的黑势千疮百孔。像是持刀疾速趋近,转瞬身中数剑,终于,长刀劈落。
棋局进行到晚上,林元美仍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越来越有趣了啊。”林元美嘀咕着。棋盘上,原先的黑势被反噬,成为白棋的死子;另一侧,白棋的孤子已经绵延成一条无眼巨龙,在黑棋的包围下寻求生路。
成屠龙之局,龙死黑胜。黑白交替,巨龙生长蜿蜒向下,直面下方黑棋,呈临渊之势。小姓不知何时睡着,此刻发出轻微的鼾声,灯油无人去添,此时一灯如豆。
“要活下去。”林元美拈起一颗白子在手,他的唇角流下一行口水:“林家命运,在此一搏啊。”
我愣住:“林家,与我相干?”
“丈和许诺,如果摧毁你,一年之内林家门人有段位者皆能上升两个段位。”林元美眼神涣散,仿佛撕扯樱花的山田弘一,手臂下沉,棋子行将打下:“林家,会复兴。”
“丈和既借林家之刀,”我说:“林家,又如何复兴?”
林元美手臂巨颤,迅速缩回,目光恢复常态:“你说什么?”
“我说,你错了。”我摇了摇头:“林家不会因此复兴。”
“像是做了一场梦啊,”林元美面色铁青:“告诉我,过了多久?”
“弹指之间。”
“失神的时候,是休息啊,”林元美的双目炯炯有神:“接着,就是你了。”
话音未落,身体开始下沉。五脏六腑向腹间靠拢,它们冲撞挤压,寻找出口。林元美打下一子,接着,肚子像是有刀插入,裂缝撕开。
灯油燃尽,屋内一片漆黑,低头,看见肚子上有点点银光。手不自觉相互交叠,一齐向左移动,银光也向左移动,再向右,折回,上下移动,肚腹间出现银色的十字,在昏冥的夜晚光芒万丈。
感觉痛彻骨髓,想立刻被斩。拈起一颗棋子,如抡刀般打下,棋子落在棋盘上,我没有听见金玉之声,却是“刷”一声轻响,响过以后,人头似已落地。
门外涌入亮光,木屐的声音杂沓而入,接着,是刀出鞘时与刀鞘相撞的琅琅一响。一道白光循着刀斩落的弧度掠过眼底,头顶被击中,感觉头颅重新回到自己的脖颈。头顶流出温暖的液体,沿着脸庞滑落到嘴唇,甜腥的气息陡然扩散,一瞬间,充盈胸膛。
“我来掌灯。”
师父站在门口,脚下是灯笼,双手握刀,刀背朝下。棋盘重又映入眼帘,先前落下的黑子与另一颗黑子相接,没有锋芒,钝如刀背。师父将灯笼放在棋盘边,盘腿坐下,一炷香的时间,林元美额头淌下一滴汗水,须臾,大汗淋漓。
“林元美,你输了。”师父说。他又拍了拍睡着的小姓:“轮到你了。”话音未落,林元美扔下一颗白子,接着身体摇晃,逐渐后仰,最终纹丝不动,眼睑上,留着浑浊的泪光。
“刀背,也可以杀人啊。”师父折扇抽出,戟指棋盘:“倘若直取龙眼,白龙会从右侧冲出。原谅我用刀背斩你,禅宗的当头棒喝,可以驱魔。”
想回答师父,但忽然困意上涌,闭眼前的最后所见,是小姓睡眼惺忪的脸。
五
翌年,我升到七段,成为最年轻的高段棋士。师父颁发免状那天,手持我父亲的刀。“是时候了,”师父说:“我把它们还给你,现在你有资格佩戴它。”
我接过免状和长刀,它们的分量变得非常不真实。我感觉七段免状有着千钧之重,而刀却轻如蝉翼,仿佛一松手就能飞上天空。“在过去,成为武士之前,须杀死罪之人,”师父说:“可是现在和平年代,武士学习剑道,却不懂杀人。”
“师父,请您赐一局。”
“好主意啊!”师父拊掌而笑:“胜负,仿佛斩人或者被斩……和平时代,能杀人的,只有棋士啊。”
我和师父弈了四局,四战四胜。师父俯视终局的棋盘,点头又摇头。“你才二十七岁,”师父说:“井上家要复兴啊。”
我心生惶恐,这句话有着不详的征兆。师父抬起头,显出亢奋的神采:“因彻,你将迎战丈和。”
我心一沉:“丈和自当名人之后一直拒不出战,怎么会同意和我对局?”
“两个月后,幕府元老松平周防守将在他的宅邸举办名手大会,会后有棋,幕府将勒令丈和对局。”师父说:“丈和输棋,可证明他的名人徒有虚名,我是唯一可与丈和抗衡的八段,兼有松平支持,可以取而代之。自丈和当上名人的四年里,我一直在筹划此事,只是这四年里一意钻营,使我的变得棋风猥琐。”
“弟子不辱使命,”我向师父叩首:“我会击败他!”
“围棋多么残忍,”师父抽出折扇,做出劈砍的动作:“不要总想着击败他,而是要想着杀掉他。”
秋分日,名手大会召开。四家弟子齐集松平家,在书院摆开五副棋局,四家弟子以我们为中心围坐观摩。丈和姗姗来迟,落座后目光斜视:“一年之前,你说我借刀杀人,而你是案下鱼肉;一年之后,你倒成为他人之刀……可喜可贺。”我顺着丈和目光瞥向刀架,两具刀架上分别摆着我和丈和的刀,刀鞘颜色均是如墨黑色,远观难以区分。
布局伊始,丈和下出“大斜千变”,两颗白子斜罩而下,仿佛穹顶。我不假思索落下一子,分断白棋,势如破空。数手之后,黑棋也被断开,四块棋如同崩裂的大地,棋子衔接处,火星动荡。
少顷,一颗黑子贴边路坠于白棋空内,如刀入肉。丈和微微仰起头,露出短而粗的脖子,粗重地喘息。“这是村正……”丈和喃喃:“要小心啊,它会伤了你自己。”
我听说过村正,它是刀名,人称“妖刀”。用村正砍杀过后,剑尖的血难以洗濯,据说这是妖刀的嗜血之癖,持此刀者,唯有杀人或自戕。局面自此一手打开,黑棋牺牲一子,而中间一整串白棋沦为废铁。我落下第五十九手后丈和打挂⑥,在走廊我遇见林元美,林元美笑容苦涩:“赤星因彻,恭喜啊。”
“棋局还很漫长啊。”我说。
“你要小心,”林元美的目光变得恐惧:“村正妖刀,会伤了持刀的人……围棋,比剑要残忍啊。”
“我不会像你一样,”我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老人的智慧吧!”
“一年之前,我轻视过你,”林元美笑起来:“你们不要以为可以轻易扳倒丈和。本因坊家督和名人棋所,两者都不会徒有其名。”
我拂袖而去,林元美笑声不绝。我在玄关与师父相会,师父雇船,晚上我们在江心食宿。船舶江心,远眺松平宅邸,房屋庭院错落,是一段又一段的剪影。我和师父将白天的棋子摆在棋盘上,当我摆出妖刀的一手,师父笑道:
“这一手,绝妙啊。”
“他们说,这手棋如同村正。”
“你的刀已成为你的棋,”师父声音渐低:“你会拔刀……雪藏于鞘,非它宿命。”起身,自刀架取下长刀。
传来船桨划破水面的声音,闻声走出船舱,迎面一艘黑船驶来,船上一人身躯肥大,竟是丈和。船头轻触,两艘船微微晃动,少顷,终至不动,两船之间,一线相隔。
“赤星君,我想见识你的刀,”丈和大踏步至船头,目光瞥向我师父手中长刀:“作为摆设,它太凶险。”
“这把刀很久没斩过人了。”我说:“凶险,言过其实啊。”
丈和手按刀柄,双目显出怯弱:“可是这刀……是村正啊。”
喉咙口泛起血腥,虎口发麻。师父递过长刀,接过,下意识拔刀,刀出鞘一半。“刀铭隐于鞘内,”丈和握刀之手颤抖:“你的棋,让我感受到它。”
咬紧牙关,拔出整把刀,细看,在距离刀柄位置,刻有“妙法莲华经”字样,颜色泛红。“村正刀铭,在月光下才能看清,”丈和长刀霍然出鞘:“你的刀有嗜血迹象。”
“嗜血?尚未。”师父面向我,目光澄澈:“因彻,杀了他。”
长刀指向丈和,咽喉的血气流向四肢百骸,第一次握紧刀,从未如此幸福:“北辰一刀流,请多指教。”
丈和拔刀,刀背反射月光。月西沉,江心倒映一弯明月。五片水花溅起,月亮跃出江中,刹那间手中刀变轻,似要脱手,连忙握住;眼前跳脱之月被斩为两截,切面,褚色暗沉。
丈和的刀只剩半截,一半落入水中。江心泛起涟漪,江面上,一弯月轮将碎未碎。万物静止,唯有月轮悄然复原,须臾,拉长一倍,呈刀形,与刀重合。
月梢微颤,挑向丈和咽喉。丈和脖颈前伸,银光没入,下一瞬,月轮倏忽间变窄,仅成一线,双手突然变得空虚。“柳生新阴流,”丈和将村正掷出,刀一半插入地板:“多谢指教。”
“无刀取⑦,名不虚传。”师父说;“新阴流以不被杀为胜,是慈悲之刀。”
“村正既出鞘,断无双活之理,”丈和跳回自己的船,拾起船桨:“我和他,总会死去一个。”
“是啊,”我将食中指交叠,如虚拈一子:“明天还要下棋。”
丈和用力划桨,两船渐行渐远,江面起雾,逐渐隐去丈和身形:“村正出鞘,要么斩杀,要么被斩,”丈和的声音飘渺:“你,不配握它。”
师父拔出插入地板的刀,携刀走进船舱。我尾随而入,黑色的棋子交替闪烁着赭色和淡粉色的光芒。拈起一颗棋子,未举高,棋子坠落,落下的地方,棋形支离破碎。
“丈和引出了妖刀,”师父说:“现在我后悔杀了他。”
“没有您的命令,我也会拔刀,”流向四肢的血气重回咽喉,使我剧烈咳嗽:“我是武士,不是不能握刀的人。”
师父起身,手掌颤抖,取过刀鞘。一炷香时间,师父前额通红,刀入鞘三分之一。天空泛白,耳边忽而传来“刷”一声响,若有似无。
刀终入鞘。
六
翌日,棋局重开。丈和第一手提去二子,与我计划相悖。我伸手入棋盒,尚未拿出棋子,脸面忽然一凉,好像是有金属贴向脸庞。抬头,眼前掠过白影,循着轨迹,看见白影嵌入断刀与刀鞘的缝隙,影子狭长,有着长刀的弧度。
觉得浑身发冷,总觉得刀架上的断刀随时会出鞘。临时改变落子方位,本来决定开疆拓土的一手最终下在了狭窄之地,为补强自己。棋子方才落下,地板骤一声响,循声望去,师父的折扇正在敲击地板,眉头深深皱起。
丈和落子如飞,盘上白棋快速抢占地盘。几个回合后,我不由自主跟随丈和节奏,以极快速度打下一子,手未撤回,丈和的手迅速伸入棋罐,拈子在手,眼看要打下,却忽然定格,彼时,手中棋子距离棋盘仅一寸;再过片刻,手缩入袖中,端坐不动。
两个时辰后,丈和将棋子举高,整条手臂忽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把自肩膀突兀冒出的长刀。长刀下沉,划出月牙般弧线,刀鞘后退,“啪”一声响,刀刃刺入咽喉。下意识仰起头,余光瞥见刀末端字样,是“妙法莲华经”,村正刀铭。
白子坠入黑棋空内,如刀入肉。“这是村正……”我打下棋子的时候,止不住喘息。
丈和紧随我落子,村正复现。刀刃挣扎,然后猛地自咽喉拔出。看见鲜血涌出,覆向村正刀面,沿着刀上的暗纹渗入,刀面逐渐变红。棋盘上,白子落于黑势外,如拔出之刀。
几个回合里,感觉村正刀尖始终抵向咽喉。怒气大炽,黑棋一子镇压白子头顶,如当头一棒。丈和思忖半晌后落子,落子刹那,看见村正刀鞘回拢,喉前的刀反转方向,缓缓入鞘。
吃过中饭,盘上不过百来手,黑与白都呈现着崩溃的面貌。轮到丈和落子,他嘀咕:“真复杂啊”,接着宣布打挂。
我和师父仍在船上食宿,晚上乌云密布,没有月光。我执黑打下当天的最后一手,师父站起,自刀架取过长刀。
拔刀,刀面上的赭色暗纹变深,色泽如血浆般粘稠,少顷,村正刀尖如雨点砸下,盘上三颗棋子转瞬间碎成齑粉。
“这三手棋,是妖刀啊。”我说:“莫非丈和的刀,也是村正?”
“不是。村正妖刀,是刀选择人。无刀取后,你的刀已追随丈和。”师父扬手,将村正掷入江中:“丈和与你决斗,是为了夺刀,我们都落入了圈套。”
隔着水面,村正刀面光泽消失。“这是我的刀,”我说,“现在像废铁。”
“已是废铁。”
“武士不能丢了刀啊。”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身影,他的嘴唇沉默地开阖,却有声音在胸口振荡,我用低若蚊吟的声音说:“因彻,你是武士的儿子啊。”深吸一口气,跳入江中。
水中的村正,看上去像一个溺毙的人。刀近在咫尺,连忙去握,手掌一阵炽热,江水泛红,像是握住了一枚太阳。用尽全力将掌中的太阳扔向空中,村正划过与抡劈相反的弧度,一跃出江面,刀光前所未有的明亮,形如日出。
光芒转瞬即逝,接着,听到刀坠于甲板的声音。苍穹被江水拖拽着下沉,没有光芒的夜空温柔地卷起我的身体,此刻仿佛历经永恒。忽然,夜空破碎着飞出江面,睁眼,我被推上了船。师父站在船头,浑身湿透,将村正丢入船舱:“村正不能落水,落水即成废刀。”
“刚才它那么明亮……”
师父脱下湿透了的和服:“生命到最后一刻,都会被点亮的。“
“这不重要。”我说:“它仍是我的佩刀。”
“不重要?”师父将村正夹入和服中,刀背贴衣滑动,弄干刀上的水迹:“山田弘一并非死于围棋,而是死于妖刀。你的妖刀差点将你斩杀,也将他逼成废人。”
“我不明白……”
“你入门那天,我向你父亲索要村正作为你入门的条件,”师父说:“围棋里藏万物,而妖刀与万物相通。当你手执棋子,等于手握妖刀。“
“山田和林元美,都是刀下之鬼,”我说:“丈和会是下一个。”
“你的刀是村正,我的刀是你,”师父将刀插入鞘中,又豁然拔出:“我这把刀,造了十五年。可惜现在,已成废刀。”
我看向村正,刀面不见了赭红色的暗纹,通体澄澈,仿佛皎洁的月亮。
七
三天后第三次续弈,当天丈和意外地在自己落子后宣告打挂,把用盘外时间思考的机会留给了我。我和师父在盘前研究了两个日夜,最终等来的是他疲惫的声音,像一纸裁决:
“不早了,换浴衣睡吧。”
翌日,松平周防守命令五盘棋在当天必须下完。坐下的瞬间,自胸至咽逐渐泛起撕裂般的疼痛,像是喉咙里逐渐涌出一截刀刃,一点点划开我的肺腑直至咽喉。我开始咳嗽,好像这样就可以把喉咙里的刀咳出来,再后来,咳嗽变得无法抑制。我抬手掩面,飞沫溅在我苍白的掌心,是一颗颗不规则的淡粉圆点,让我想起山田掌中破碎的樱花。
黄昏时分,丈和粘劫。他的视线掠过刀架,又看向我:“多好的刀,可惜了。”
我看向师父,师父眼睛充血,血丝汇聚在眼角,眼角红得像两颗玛瑙。我们目光交汇,师父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面带笑容的师父看上去是那么陌生。
我将一颗黑子举高,感觉举起了刀,放眼棋盘,恍惚间看见空点已全被白棋占据,棋盘变得无处可下。手腕酸痛得像是要折断,最终松开了手指,黑子坠落下去。
我的记忆回溯到十五年前的黄昏,眼前的坠落有着似曾相识的模样,竹刀与棋子划过相同的直线,它们在记忆中有着惊人的重合。坠落的黑子打碎了盘上的棋形,它们用异于木头相击的金石之音驱逐了我的回忆,但这两种声音都是同一类宣言,一是空手待斩,一是投子认输。
人声开始喧哗,而丈和岿然不动,他紧闭眼睛,眉头深深皱起,显出极其痛苦的模样。喉口一热,感觉刀刃呼啸着冲出我的喉管,我的唇边泛起如薄雾般的血光。我的半边头颅枕向棋盘,颠倒地注视着惶乱的人们,眼前的白子红白相间,黑子浸泡在血里,像是出滩的礁石。
八
我躺在床上,床头坐着师父和一个宽脸的男人,男人身边放着药箱,看样子是个郎中。我从松平的宅邸回到我居住的和室,印象中,前后不过眨了下眼睛。隐约嗅到了焦臭的味道,感觉身体在焚烧。
火焰来自胸膛,它们洞穿我的身体,筑起一道虚实不定的墙。我被困在光与火之间无法动弹,师父和郎中的脸近在咫尺,而声音却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
“已经两天了。”师父说。
“肺痨发作得太急迫,”郎中说:“井上先生,对不起。”
“可是他的眼睛……”
郎中叹了口气:“睁是睁着,可是完全不动啊。”
师父!
我向师父喊叫,但他浑然未觉。郎中走远,传来踢踏的脚步声。“赤星因彻,你不该拿刀。”师父的手抚向我的额头:“我也不应该啊。”话没说完,师父的头低下去,肩膀颤抖如筛糠。
我的眼角不知何时渗出了一滴泪,它附着在烈焰之上,在火光中熠熠生辉。觉得自己的生命都在这一滴泪中,连忙闭上眼睛,泪滴被眼睑覆盖,像一颗珍珠,好像永远不会干涸。
附记:
天保六年,幕府老中松平周防守于府上举办“名手大会”,弈者共十人,唯十二世名人丈和与幻庵因硕之徒赤星因彻之局引人注目。此局丈和的六十八、七十、七十八三手绝妙,史称“丈和三妙手”,棋行至二百四十六手,执黑的因彻取胜无望,万念俱灰之际,因彻于盘前吐血,染红棋子,举座皆惊;翌日,因彻身亡,时年二十六岁。
备注
①免状:围棋的段位证书。
②介错人:介错是指在中为切腹者,以让切腹者更快,免除痛苦折磨。此斩首之人,即为介错人。
③免许:日本武术界在评定各弟子水平时,没有特定的模式,各个流派采用的方法各不同。自古以来,没有一定的规定。进入江户时代,很多流派开始授予 “切纸”、“目录”、“免许”三个阶段的证书或卷轴。获得“免许”称号,即获得可以告诉别人自己流派名字的资格。
④抱首:②挥刀向剖腹者的脖子斩下,但不完全斩断,让头和脖子仍有一丝牵连。
⑤小姓:小姓一词意为"侍童",除了在大名会见访客时持剑护卫,更多的职责是料理大名的日常起居,包括倒茶喂饭、陪读待客等。
⑥打挂:日本旧时代,上手拥有随时可以暂停棋局的权利。暂停棋局,即为打挂。
⑦无刀取,是的招数,在绝妙的时机冲入对手的怀中,控制住刀子,之后将整个夺走,是接近敌人的可怕的招式。
原文发表于《文艺风赏·美第奇》封面故事
感谢评论,把“莅临井上家的时候”改成了“到井上家的时候”
9/10 首页 上一页 7 8 9 10 下一页 尾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