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文学创作的女作家 怎么看沈从文 49 后不再从事文学创作?
一九八〇十一月二十四日,沈从文先生在美国圣若望大学作报告《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朋友: 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今天到贵校来谈谈,不是什么讲演,只是报告个人在近五十年来,尤其是从二十到三十年代,由于工作、学习的关系,多少一点认识。……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
……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
(引自《。)1981年4月11日沈从文先生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
外面传说更多一点,说我是受压迫什么。特别是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头一次讲演,有个台湾记者,把我添盐加醋地写了一个访问记,记者,记录,好像我就是凄凄惨惨地出来,出来是不让我出来,怕我跑。他就不晓得我能跑到哪去,我还能离开中国吗?我绝对不会,我历来是讨庆外国人的,在我作品中从来没对洋人有好感。(《沈从文晚年口述》第93-9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981年4月8日,沈从文在湖南博物馆的演讲:
我是一九二八年就混到人学教学这一行,教散文——那也是骗人了——教散文习作,一直到解放我才离开学校。离开学校以后,我就直接到历史博物馆,名分上是做研究员,实际上我是甘心情愿做说明员。我深深觉得这几十年生命没有白过,就是做说明员。因为说明员,就具体要知识了。(《沈从文晚年口述》11页)
当然,即便是沈先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但依然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沈先生是长期饱受压迫、心有余悸之下的口是心非。
对此,我想问问,既然是心有余悸,应当是闭门谢客,谨小慎微,为什么还要跑到国外长篇大论?而且竟然还公然与党媒唱反调呢?!
高票答主知友 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窃以为,知友 的解读不乏真知灼见。然而,鄙人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愿商榷一二,还望多多指教。
知友 认为,沈从文先生1949年之后不再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无非两点:第一在于沈从文先生所擅长的创作内容与国内文化环境的冲突。第二则是沈从文先生曾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与中共有过不愉快的回忆。
对于第一个原因,在下是认同的。毕竟沈先生本人也坦率提出:“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
对此,在1949年4月6日日记中,沈从文是这样记述的:
昨杨刚来带了儿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尤动人。李秀真也极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从这几篇文章中,让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国家的长成,作家应当用一个什么态度来服务。这一点证明延安文艺座谈记录实在是一个历史文件,因为它不仅确定了作家的位置和责任,还决定了作家在这个位置上必然完成的任务。这一个历史文件,将决定近五十年作家与国家新的关系的。上期有萧参著《坚决执行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一文,可惜没有见到。从推想说,一定是对当前和未来能完全配合得极密切的。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沈从文全集》第19卷25-26页)
有网友贴出了汪曾祺的文字,认为沈从文建国后不写小说是因为担心被骂修正主义,并引用沈从文的信作为证明。窃以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鄙意以为需要看全文,来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评判还是较为公允一些。我这里把这封信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节选自《沈从文全集》第21卷19-22页):
血压总是上升,头重重的,有时还简直沉重得可怕。本来馆中已决定是要“全休”厂。先是休假一年,打算写本故事,是三姐家堂兄闹革命,由五四后天津被捉,到黄埔清党逃出,到日本又被捉,到北京被捉,回到安徽又被捉,……终于还是在“蒋光头”西安被困二个月以前,在安徽牺牲了。死去后第二代经过种种事故,到昆明我们又碰了头,第二代又活动,复员后,回到上海,又被捉,幸亏手脚快,逃往冀东解放区,现在则是宣化龙烟公司宣传部长,先生是书记,我因此还到过宣化两次;已得到十万字材料,极有意思,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可兼有《红旗谱》、《我的一家》两方面长处。可是血压一高,什么都说不上了。最难过时只想死去赶及烧掉完事。这一月来血压一下降,却又想起还有〔20页〕一大堆事待做了。人倒并不胖过98磅,只是心脏已不大好,将来还是致命伤。目下还无妨。
……我大致年底出院,以后将是照常工作,不过是坐办公室揽杂事,还是写那个未完成的东西,可没一定。总之,人既〔21页〕然还得好好活着,趁能做事时,有事可做时,就拼命的去做,才是道理!。……近来看了些文学书,血压也下降了些,不免静极思动,心想还可能写个十来本本什么玩意儿的。真近于古人所说:“跋者不忘履”,还简直不忘飞奔!并不是想和什么年青人争纪录,那是不必要的。也无意和“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争地位(那是无可望的天才工作),只幻想如果还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假定说,此后还可活过几年,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来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竟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若居然到时又可印出来,不受人为限制,在一个比较自然情形下,一定总还会值得有人去看看,且不会让读者中毒的!因为真正有毒的什么神仙公主古怪离奇故事,还大量在旧戏中得到不同发展,不同鼓励,而许多新的模仿也还大有市场。我写的东西应当不会比那个更坏的!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可是我却依旧还是想劝你在此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本,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我年纪已到六十岁,即或再憨气十足的来在写作上用力,实在成就也有限。而且再也受不住什么歼灭性打击批判。所以十分怕事,见人都可拱手,特别是怕批评家(这可不能怪我对工作不认真。就工作说来,已够认真了,这些年来什么不写也是把写作看得过于认真的结果。不是懒惰!但是事实上倒是像有些人不那么认真还好些!)尽管诸事常在变,我怕来不及还看到对我工作或工作态度的正当估价机会了。可是你还年青,能在这世界上多活廿年,我总多少有点迷信,以为国家十分大,过些日子或许还是要有更多的人用各种不同方法、不同艺术风格来写新的人事,来写“短篇”或“特写”,即“通讯”到另一时也会要变一变,写得十分活泼有生气!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从信中可以看出,经历了1957年大规模“反右”运动之后,沈从文似乎并未有什么太大的心理阴影,依然对文学创作跃跃欲试,甚至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再作冯妇之心跃然纸上。“可是血压一高,什么都说不上了”,加之“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正是在这种主客观因素作用之下,沈先生又回到了文物研究事业中去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建国前从文先生因为其“粉红色”的背景而被左翼文人批评过,因而建国后受到TG的打击与排斥,导致沈从文先生放弃了文学创作。其中,比较典型的是 @ 的回答: 。
@ 先引用了沈从文先生的一句话“但如果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会走得更好呢?”,并感慨道:“沈从文始终相信,文学要保留对政治批评和修正的权利,而不是单方面的听话和守规矩。这种坚守,让他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对此,这位网友解释到:
“建国后各种政治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昔日的朋友们纷纷识时务为俊杰听从“红绿灯”指挥的时候,沈从文还在坚守着自己。直到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沈从文被踢出北大,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教授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
在下真的对这位网友无畏的言论无语了!一个堂堂的历史博物馆文物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能说“被踢出北大”?全国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全国第六、七届政协常委,能说“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
这位网友恐怕不知道这个基本的常识——《斥反动文艺》是郭沫若在1948年2月(也就是TG建国前近两年前)在香港发表的一篇文章。2个月后,郭沫若被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为第一届人文组院士。
明明是候选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发表于1948年的文章,怎么成为“建国后各种政治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
这位网友难道不知道,就在所谓《斥反动文艺》“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的9个月之后,1948年11月7日晚八时,沈从文才在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纪念堂提出了“红绿灯”疑问吗?
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如何令郭沫若、沈从文在建国前后实现时空穿越的?如此荒诞不经的时空穿越竟然博来一阵阵喝彩,在下的感觉只是一阵阵悲哀!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并没有直接指出沈从文受害与郭文,但是,依然认为沈从文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高票答主 网友就持这样的看法:
政治上的乌云给了沈从文以巨大的压力,几乎摧毁了他敏感而脆弱的内心,以至于他甚至有几次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已经不知道在那段岁月下的沈从文究竟经历了什么,但是其直接后果就是沈从文选择放弃从事文学创作而专注学术研究。
这里插句话, 网友 称“我们已经不知道在那段岁月下的沈从文究竟经历了什么”,却又得出了“政治上的乌云给了沈从文以巨大的压力”的结论。是不是搞文学研究的都是习惯于凭直觉、感性得出结论呢?
不错,在建国前夕,沈从文精神上曾经受到打击。1949年4月2日,沈从文妻子张兆和给沈从文大姐夫妇写信:
上次我信中曾提到二哥这几个月来精神不安的现象,但是这种不安宁,并不是连续的,有时候忽然心地开朗,下决心改造自己,追求新生,很是高兴;但更多的时候是忧郁,悲观,失望,怀疑,感到人家对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因为说的太多,我反倒不以为意。他那种不近人情的多疑,不单是我,连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他失之常态,不可救药。不想他竟在五天以前,三月二十八的上午,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现在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他一切都很正常,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己;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便执着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计划的要打击他谋害他。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写文章联想又太丰富,前两年写东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误解,社会一变动,虽然外面的压力并不如想象的大心里不痛快。(其实并没有压力),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当然,一个人从小自己奋斗出来,写下一堆书,忽然社会变了,一切得重新估价,他对自己的成绩是珍视的,想象自己作品在重新估价中将会完全被否定,这也是他致命的打击。总而言之,一句话,想不开,闹成现在这样局面,否则好好上课,慢慢来修正自己,适应新环境,不至到这个地步的。眼前书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后必须易地疗养,一定要把他观念上的错误纠正过来才能保安全。我现在想问问大姐,在我们父系或母系,或者同父系或母系有关的祖辈中,是否曾经有过神经病患者,医生需要参考材料,望告我。并望转告大哥三哥。他身体很好,伤口不要紧,勿念。祝安好。(《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2-23页)
众所周知,郭沫若1948年发表的《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先生进行了批判。可能这就是“沈从文先生曾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与中共有过不愉快的回忆”吧。
但是,据在下所知,TG建国后,不仅并未对沈从文先生进行过批判,还得到了TG高层的力挺和优待啊!
在下不才,摘录一些沈先生“那段岁月”的自述,看看是不是“政治上的乌云给了沈从文以巨大的压力”。
先看下面文字,这是郭沫若于1964年6月为沈从文作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写的部分序言内容。
这里插句闲话,有网友认为郭沫若的文字《斥反动文艺》自有千钧之力,彻底打垮了沈从文。那么,郭沫若为沈从文先生专著所写的序言,算不是为沈从文撑腰呢?
而这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又是怎么回事呢?从文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最先企图是为总理外出送礼而用,因此康老看后为题一签。他把那么一种重要工作交给我来主持,总经过些考虑,我敢答应下来,也不是不事先考虑。郭老并主动为写一长序。”(《沈从文全集》)
一部学术著作,由中央书记处书记题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作序,即便是现在也是何等荣耀,这“政治上的乌云”也该散了吧?
文革期间,沈从文于1972年5月致信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
五四年文代会,主席和总理接见我,劝我再写几年小说时,我没有动。我把这种天大难得的鼓励,转而更坚定的学习“为人民服务”,提高了热忱,也提高了责任感。在反右后,又要我去接老舍在北京市作协①那个位置,可是还是不动。随后承你厚意,要我来故宫学学绸缎,倒毫不迟疑,就来和大家一道,在你领导下进行学习了,实在应当向你表示深深谢意。(《沈从文全集》第23卷104页)①作协疑为文联之误。老舍曾任北京市文联主席。
TG党魁亲自劝说“再写几年小说”,安排到文联任主席,这等待遇叫做“政治上的乌云”?
1973年,正值文革时期,沈从文在写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个人实在太不足道,虽写了二十年不三不四的小说,徒有虚名,在新社会已近于“空头作家”。因此即或还有机会,和茅盾、老舍、巴金、冰心一群老同道,用作家名分,长年向各国飞来飞去,享受友好国家的隆重款待,享尽了人间快乐热闹,还是不去。(主席和总理在二次文代会上接见我时,就亲自劝我再写几年小说。)……你明白这个十年,我是用一种什么心情来爱党和国家,你就理解一个七十二的人,和你第一次谈话中流泪的原因了!目前尽管已七十过了,不离开这个战场以前,我还有不少责任待尽,……而对外教学,和生产服务,前后在全国政协又提过提案二十件,多和这两事有关,一律得到通过,有的指明二三个部执行,有的且到五、六个部执行(包括外贸、纺织、轻工业、文化、教育等等部门在内),最多的一个,据一个审查提案委员说,还是总理亲自批示,附加了个“这是内行说的话”。不问传说是否可信,总之,提案交六个部执行,却是事实。因此,我就还有不少责任待尽。例如提案中有改编全国大专院校工艺美术教材事,总的工艺美术史教材,及丝绸印染系、漆工艺专系教材,当时就是调全国院长、主任教师、青年讲师来京,由我为提供材料,由专任教师编写,后来又还由我来修改审定的。有些在“文化革命”前全国己试教一二年,明年又将开学,近十年新出土文物万万千,大致还是得由我为提供材料作补充修改。(《沈从文全集》第23卷第477-478页)
文革期间向全国政协提案二十件,总理亲自批示,几个部执行。提出改编全国大专院校工艺美术教材,结果就是“调全国院长、主任教师、青年讲师来京”,并“由我来修改审定的”,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政治上的乌云……几乎摧毁了他敏感而脆弱的内心”的文人啊?!
有很多文人把文革期间的沈从文写的悲凉彷徨、哀怨委屈,乃至于意味深长的写下所谓“抱着记者胳膊哭”文字。对此,我们可以看看沈从文先生文革期间的信件,看看是不是所谓的“害怕”、“不敢说话”、“饱受委屈”。
1967年2月2日,沈从文在写给其次子夫妇的信中大谈时局如何动荡,而自己又如何“十分好”:
全国各处都在搞夺权,北京自不例外。……近来终日大小会连续开,权是夺了,如何行使,还是问题。文化部萧望东统战部李维汉等等许许多头头均坐卡车挂牌子游了街,近军委已下令正式禁止,许多人或可免去此种冲击。形势变化快,前不多久参加检阅的陶铸、刘志坚均已下马。穆欣、唐平铸、胡痴也被号以“小三角”而下马。贺老总止式点了名,朱总也有大标语(光明报、人民报、解放军报),薄一波、罗瑞卿已死去,又传邓、陶也死去。陈云也有大标语,吕正操因铁路员工罢工而下马;王任重、刘澜涛似均已上过街。……今年过年不放假,凡事照常,十分好。我们每天学毛选和政策文件,劳动照常,天气过冷,室外打扫园子已不常进行,只收拾毛房。(22卷27-28页)1967年5月11日,写给其次子本人的信中,则更是大谈时局:
大街头大字报对陈老总、叶剑英的似不少,虽有总理一再说(或戚本禹说)过外交部不能妨碍外事,还是老揪住不放:谭震林也是大标语最常见的姓名。此外部或副部长级、院校长或党委书记级,万人大会事似还在不断举行。一隔行,便不明白情形内容了:机关夺权一般情况是分成两派,有的又各引外援,外援一多,即不易好好开会,争辩若不能解决,最后便易由挨、挤、推、攘,进而为武斗。斗有大小,闻儿童医院和市政机关即各死五六人。有个什么机关还有上千人斗,伤必不少。大学这方面训练好些,但办公室的打,砸、抢、夺还是经常发生,无从防止。大民主总得从一个较长时期中训练才可望取得进展。(因为这是个伟大企图,本来又无一个底子,无可避免。)一切活动公开来搞,还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也有趋势搞秘密破坏的,发展下去,不怎么好。江青不久谈话,主张联动公开,捉了的小头头均放释,即是此意。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末后特别提起“教育子女”问题,的确是个大问题,话特别针对到军委而说(大将元帅等等),可知其必不止说贺龙、陈毅、叶剑英……子女,因为凡是知道点内部事情,和联动的联系,或和运动的操纵指使,都有一定关系。有的大人且作了参谋,就更不好办了。其次是“大联合”、“三结合’",日来报刊重点宣传,提法十分好,十分重要。……去医院必从百货大楼前过身,总是见大几万人各处走动看大字报,特别是看漫画,兴趣十分浓厚。一部分像是外来人,一部分是不上工的职员学生或小市民,有什么新传单,即一涌而进,争夺激烈。许多人多像是无所事事,不知作什么好,看来令人忧虑。上万的路人,极少有人在路上看报纸社论。事实上很多大致看不懂报纸社论,不明白重要性。我心中总不免怀有一点杞优。一种深刻的杞优。同时也可以说是不必要的杞优。得想办法正面教育。…………(《沈从文全集》第22卷37-38页)在该信中,不仅表达了对主席言论的不以为然,还对文学创作跃跃欲试!
主席也说起过“习文学的不会写小说。”因为他不明白大学校里教员,主任和教授,很多写小文章也不成。大多数也不会写小说。(有很多写篇像样文章还不可望!)还有各省作协的负责指导写作的人,也多不会写小说,或很少写过几篇又有思想、又有文笔、可以示范的小说。……我说的是短篇小说.这方面我似乎还有发言权。可惜我心脏受了较大限制,不然一定请下乡,或即回来家乡住一年,一月试写一个,一年时间内会至少写得出十个一切都新的样板短篇。到日前为止,这一环成就,是最弱最弱的一环。照《人民文学》过去的鼓励方法,是永远产生不了真正新作品的。学校则改来改去,也决不会从中文系产生起码作家,先生还得再学习,才有资格作先生改卷子!(《沈从文全集》第22卷38-39页)
沈从文先生在信中竟然指责毛泽东“不明白”、竟然为文革中的打砸抢开脱!竟然“妄议时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害怕”、“不敢说话”、“几乎摧毁了他敏感而脆弱的内心”的文人啊?!
1974年1月16日,写给其次子沈虎雏夫妇信:
我近些日子很好。正当不少熟人,都感到仿徨失措,不知干什么好时,我却有的是事可做,总做不了。正在争时间赶工作,经常忘吃忘睡!或许可以写出五,一来个大大小小专题性带图文章,或图册:又还可以把《衣服发展史》继续作下去,搞了不止一万图像。(《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10页)1974年1月19日,写给其次子沈虎雏夫妇信:
还有那个在进行中的《中国服装资料》,若照计划将编十大本,已有了些准备,今年大致将正式呈报上上级,若有必须继续完成,大致将建议外调三五人,并全国去看看材料,也可望一一完成。事实上一个人也还是可以进行,得到不少新解,只是怕时间已来不及,还得争争时间,先就可作的作,三几年内若身体不出意外事故,将证明近廿五年的文物学习有一定收获,远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的小说,对后来人有益。(《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24页)
××××××××××××××××原答案×××××××××××××××××××××
1949年9月8日,沈从文写信给丁玲:
中共实在凡事从大处看事情,在经营一个国家,不是对什么人特别过意不去,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念,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中国工艺美术史。并企图进一步研究,努力使之和现代生产发生关系。如有成果,作的通,我头脑又还有用,逐渐可望回复正常,将来我上课于新的文教机构,担负一个小小职务,为国内各地有区域性工艺美术馆垫个底”。(《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48-49页)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更多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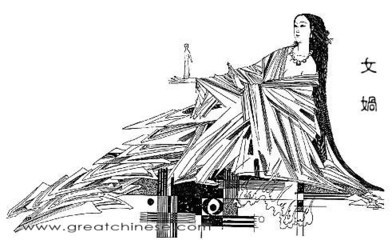
中国古代神话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 中西神话与文学
1、中国古代神话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页。古代神话是远古人类借助想象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故事,反映了原始人类特有的意识形态,它通过幻想的形式,反映了那个时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运用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它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对后

关于在北京从事影视编剧的自由职业者专业职称评定的建议 影视编剧培训
关于在北京从事影视编剧的自由职业者专业职称评定的建议 “剧本和人才培养是发展电影的两大关键,剧本是基础性源头性的创作。”这是去年国家广电总局在宽沟召开影视创作会议上,传达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为我国繁荣和发展影视文化

雷恪生的恪怎么读? 诸葛恪得驴阅读答案
“恪”字究竟怎么读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07-28 发表评论>>王继如,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出生于1943年,广东揭阳人。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改师大);后师从训诂学大家徐复先生和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获文学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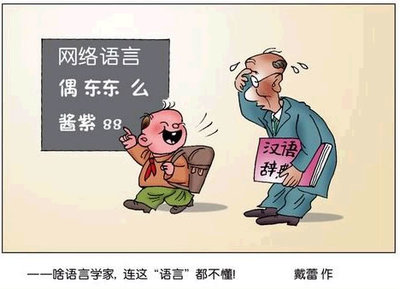
《网络语言对文学创作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材料未整理 掌阅文学创作大赛
概括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粗俗泛滥在网络语言不断追求个性、不断创新的洪流中,语言的粗俗化也是确实成为了一帮人的低级趣味。中国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造就了许多优美的词句。但网络语言如此简单草率,不就糟蹋了中国文字的内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