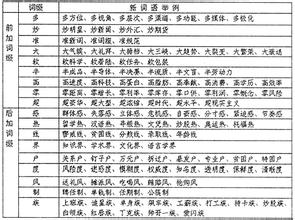下午在房间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旧的泛黄的相册,掸去岁月堆积的灰尘后,意外地发现里面装了很多信和以前读书时传过的纸条。
随手拆开一张:夕遥,下次我要在吃东西,老师来了你就用脚踢我凳子,记住了啊!—-这是初中坐我前桌的大嘴王写的。
再拆开一张:夕遥,下午我看见13号了,他见我一来又不好意思的走了。你说他是不是知道我喜欢他了?好担心—-这是高中的闺蜜陈瑶写的。
那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让我像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潜入深海发现以前扔过的宝藏一般惊喜。
除了纸条也有很多信,信里装着的大多是那个年纪小女生该有的小忧郁、小欢喜、小男生,每拆一封,都看得我直发笑。
我不知道你们,但我小时候住的城市是一座保守的城,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有个知心笔友是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
那时候一放学最兴奋的事情,就是跑去文具店挑信纸。带香味的信纸总是最抢手,我很难抢的到。有了信纸就给笔友写信,写完再把信折成各种好看的形状塞进信封里,用胶水小心的黏上信封,贴上邮票,扔进邮筒。接着又是漫长的等待,窃喜地拆信,珍惜的看信,又快速地回信。
这个写信、封信、寄信、拆信、回信的过程在旧时光里不停循环,现在想起来,依然很惦念那份亲切和期盼。
我交的第一个笔友,是在一本杂志上看见的交友信息。她叫苏蔓,天津人,比我年长几岁。
直到现在相册里还保存着她给我寄过大头贴,照片上的她齐耳短发,笑起来跟娃哈哈矿泉水一般澄净。
我们在信里几乎什么都会聊。她说她爸是个手艺人,会雕小木人,可厉害;她很孝顺,总是把零花钱偷偷攒起来再还给她妈妈,以后长大要赚钱养家;她还说长大以后要做旅游记者,因为这样既能工作又能趁着机会环游世界了。对了,她还曾不怕羞地说她长大以后要嫁给她心爱的人。
小小年纪的我们总是对未来无限憧憬,急着长大。虽然见不着面,但书信让天南地北的两颗心紧密串联起来。
那些你来我往,一笔一划的信,放在今天可能有些矫情,但在过去它无比真诚。
本以为这份知心的笔友之情可以持续很久,苏蔓上大学谈恋爱后,我们通信就变得很少。我寄了两次信都因为地址查无此人给退了回来。
那时候我想,苏蔓也许已经忘了我吧。
如果说每个人之间都是一场萍水相逢的话,那人世间的相遇,可真是件奇妙又美好的事情。
我怎么也没想到过了十多年,竟会在现实中认识这个少年时期的老朋友。
我们真正认识,是在沙巴的一个叫做哥打京那巴鲁丝绸太平洋酒店,时间是2013年10月25号,我记得很清楚。
说实话,要不是在那儿丢了行李和护照,谁会吃饱了撑着去记住这么拗口的名字,一遍遍和当地警察确定丢失地点,简直是耗费生命。
不过幸好,因此我认识了苏蔓。
当时我们谁也没认出对方来。多年过去,岁月早已让大家都改变了容颜,我只知道她会说马来语,长得很漂亮,人也谦和可逊。
她做为目击证人站出来,告诉我有人在酒店门口拿错了我的行李箱。她让我们叫她Judy,随后陪着我和同伴一间一间房找到那个房客。
房客是个爱尔兰人,只会说爱尔兰盖尔语,奇怪的是他们坚持不肯打开箱子跟我核对。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劈头盖脸和对方好一顿理论,最后百般周折爱尔兰人打开行李箱和我们核对护照身份。
就在我说出我的名字的时候,站在旁边的苏蔓傻眼了,我们打死也没想到在异国他乡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见。
确定身份后,我和苏蔓的眼神里,都有一种双胞胎姐妹失散多年再重逢的惊喜和亲切。谁也没有因为第一次见面而感到陌生,说说聊聊直到凌晨,都恨不得把这十几年的空白全部一股脑补给对方。
说起过去,无不深刻。细问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的查无此人是因为她搬家了。
她爸爸不幸得了肝癌,发现的时候已是中期,巨额的医药费让他们家不得不变卖房子,然后一家三口挤在十几平的小房子里。最头疼的怕是遇上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睡觉都没块安生地方,苏蔓总是拿着锅碗瓢盘去接水。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手术,苏蔓爸爸的病情慢慢得到好转。自从苏蔓的爸爸病倒后,她妈妈也没再去工作,全心在家照顾生病的丈夫。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
苏蔓说那几年,她甚至连张邮票都不舍得买,更别说再和我通信了。我无法想象她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那个时候的苏蔓,也就二十出头。真遇着事了,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弱小,书信里的信誓旦旦全成了空谈。

她开始在学校饭堂刷盘子洗碗,清扫校园勤工俭学。每个星期天还去给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做一次英语家教,以试图赚取学杂费和养家。
至于在信里提到的那场大学恋爱,她一脸遗憾。那是一个很好的男生,可那时候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去经营一份感情,就更别说好好陪伴对方。
没有时间和心思维系的感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这场恋爱最后无疾而终。
这是苏蔓第一次爱人,说不伤心,那是自欺欺人。深夜大家都睡着的时候,苏蔓咬着被子哭了一宿,怎么也想不通上天待她是如此不公平。然而更让她想不到的是,第二天顶着红肿的眼睛接到她爸打来的电话,她爸爸哽咽着告诉她:“妈妈突发心脏病,正在抢救,快不行了”。
一瞬间,天都塌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