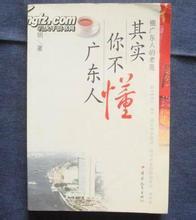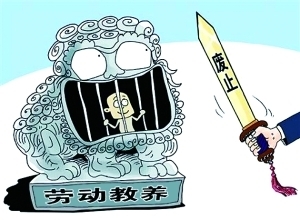郭海晨 曾经听过一个描述德国人和中国人差别的故事,说是商店注明早九点开门,如果一个德国人在八点五十分到达门口的话,他会主动做的选择只有两个:等待开门或放弃离开——这是他们热衷于确定性的体现。 但若是换个中国人,则会有第三种选择:敲门商量,我可以买你的东西,能否通融提早十分钟开门?——这是我们热衷于制造不确定性的表现。 没想到,这个故事真发生在我和从前的两位德国上司身上了。某日我和我两位德国上司去北京中关村[9.14 0.33%]的一家公司拜访,早到了十分钟,我欲带着德国人直接进门去,但他们阻止了我,说是这样做不尊重对方的时间。 最终,我们出现在对方办公室的时间精确到提前三十秒。 其实,德国人喜欢确定性对我倒也不是太新鲜的知识,在被提拔做高层之前,我负责过一段后勤运作,每年的预算,用A3大小的纸要做七八十页,而且都是九号小字足本无删节版,要做到不能有逻辑计算和格式错误以外,用在实际操作中也不会出现偏差。 正是因为每次预算都做得井井有条,上司颇为赏识。 实际上,作为正宗“中国制造”的知识分子,平日生活中我喜欢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就连结婚蜜月去欧洲旅行都不会预先订好酒店,基本上选择火车走到哪里算哪里,呆几天看心情再决策下一步的方式。 但长期的德式“事实、数字、逻辑、计划、细节、结构、确定”等等的熏陶,我及我所领导的业务,变得一切有序,所谓“万幕无哗,一尘不惊”而可预测。 特别是做了CEO之后,每年年中接待上司来访,都要做“最佳情况、正常情况、最差情况”实际预测与预算的比对,一切必须在可掌控的范畴内,九年间没有给我的上司们制造过负面惊喜,只信奉“精确计划、精确进攻”的德式风范底线。 在具体执行中,其实每一年所有的可能不确定或计划偏离因素,都必须被预料、监控、干预、化解之。甚至连员工的快乐满意程度,每年都有总部独立调查,如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则必须制定细化后继行动计划,总部择日抽查执行情况,中国公司因此逐年渐呈“百姓欢忭,耕种不辍”之稳定景象。 可德国人并不是真的事事要去硬顶的。有一年,上司带我和另外一家公司谈判,改变了我对德国人一切都必须“确定”的结论。 一个兄弟公司想让我们接手他们的某一技术服务,但牵扯的领域有一新技术,需要派我方技术人员到第三方机构做认证培训,双方在谁必须支付昂贵的培训费用上陷入了僵局。 对方的德籍总经理认为这是我方具备服务能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是我方的费用,不应向客户方收取。我和德国上司据理力争,作为服务方没理由接受高于成本的服务业务,更何况我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把客户方的项目按时完成,并提供长期战略性合作价值。 双方僵持了多日,不得其解。我私下觉得如果大家都对成本斤斤计较,又互不信任的话,这次合作很可能难以前行。 两个德国人叫了暂停,约好当日下午5点继续。我老板在我办公室灌了三两杯浓缩咖啡,来回踱了四五个小时的步后,回到谈判桌旁,双方决定暂时搁置这一费用的承担方讨论,让合作先行启动,合作半年后再根据合作的满意度,另行讨论决定最终结论。 这一在接下来的半年内“不确定”的结果,让我对德国人刮目,但无论如何,合作得以启动,半年后对结果满意的客户很爽快地承担了原本硬顶着的费用。看来不只是中国人,有原则的德国人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做“模糊”的决策。 在模糊中前行,则是此次我学到的管理决策智慧。向前走,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弄个明白的。 凡事有精明和高明之分,同一物,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但精明了,就要求一个权衡和尺度的确定性,管理决策中,所谓精明,就是算得精,计得明白。 但同一境况,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很多事情要向前走,须登高望旷远,就不能太确定地精算、明计。 我不敢妄言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文明高明,但“不确定,模糊”的智慧,中国人却有自古的传承。春秋时就有楚庄王的“绝缨会”为绝好案例,有臣子调戏大王妃,“暗中牵袂醉中情,玉手如风已绝缨”。但大王不想弄个明白,建议大家都去缨尽兴,“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 几年后有臣子的舍命以报,效果是大王明烛治罪所不能取得的,这不就是高明吗? (作者为前贝塔斯曼旗下欧唯特信息系统中国区CEO, 上海交大-马赛商学院AEMBA在读学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