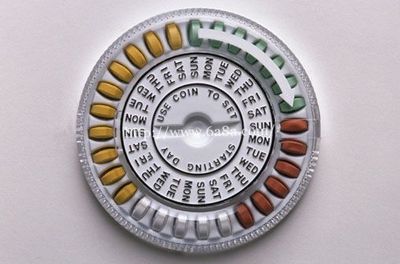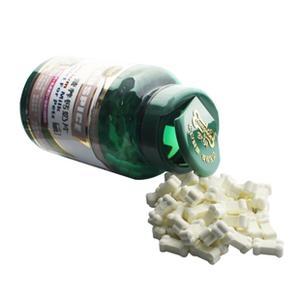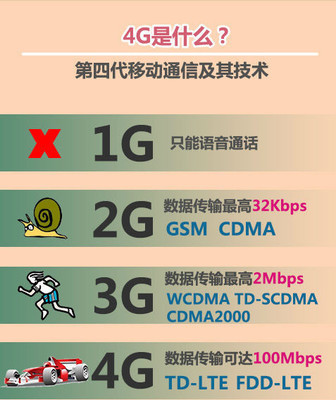只要你把个人的成功与组织的成长联系在一起,那么退休似乎就变得遥遥无期了,因为没有哪个组织能在几年里就长大成人 □ 笑谈 周末,北京城黄沙漫漫,但还是盖不住春的萌动。一年之际在于春,公司高层的一行人又在奔赴郊区的路上,公司内部新的战略实施、组织建设和能力建设的工作会召开在即。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退休呀?”路上,一位同伴忽然问我。我看着前面灰蒙蒙的天,忽然想起了10年前的“豪言壮语”——我们再干十年,然后集体退休!现在想起这句“忽悠”大家的话,不禁暗自好笑,只是笑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是自己当年的“年少轻狂”! 其实,有关工作年限的讨论不仅仅在我们公司高层内部展开。年初,我有幸参加了大连一家企业的“高管训练营”,讨论领导力建设的相关问题。其中一个议题是:未来5到10年,个人愿景和组织发展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记得一位年轻的高管给大家描绘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5年之后,他已经退休了,在蓝天白云下,用笔记本电脑和董事长做沟通,而董事长在一个大屏幕前指挥工作。话音刚落,董事长不高兴了,说:“我这个60后的都没想退休,你这个70后到总想着退休!啥意思?” 我真的很能理解他们两位的想法,20岁时,我想我会在60岁退休。30岁时,我期望能更早退休,在40岁左右就隐退,因为当时觉得10年的时间能让一个人走向所谓的“成功”。现在40岁了,却发现终点线又发生了移动,因为你参与建设的组织还仅仅是个幼童。只要你把个人的成功与组织的成长联系在一起,那么退休似乎就变得遥遥无期了,因为没有哪个组织能在几年里就长大成人。 其实,工作寿命不仅与高管有直接的关系。前不久,听过经济学家的各种报告,在谈到“后金融危机”的对策时,纷纷宣称,使经济免于崩溃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家都工作得更长久。我不太确定,工作五十年是否好过工作三、四十年。但我知道,工作有点像做运动。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沉闷,有压力(随便哪一天我都情愿不要工作),但工作其实比不工作更为可取。工作让我们充实,让我们得到地位和收入;工作让我们动脑筋,让我们走出家门。 年后,我与刚退休了的一位前政府高官闲谈。他说,不工作的问题不止是没有了在位时的收入和地位,而是不再接触年轻人。与年轻人共事让人感觉年轻。当你不再与年轻人在一起时,你会开始觉得自己老了,连举止也相应变得老态起来。 将来,当办公室里充斥着老年人辛苦工作的身影时,对所有其他人也都会有益。年轻人可以从老年人身上学到东西,而中年人会很高兴周围有比自己年纪大的人,这会让他们从比较中获得年轻的愉悦感。 对企业来说,年龄多样化的理由更胜于性别或种族多样化。企业需要记忆,这方面存在明显的分工。年轻人可以负责短期记忆,因为年老者记不住近期的事情;老年人则可以负责长期记忆,因为年轻人尚未获得这种记忆。 由于工作关系,我的身边有几位“师”(师长)、“兄”(兄长)级别的人物,和他们一起工作,你会感到特别的踏实,在他们的工作动力中,充满了“责任感”,与太多为“职业发展和机遇”而工作的后辈而言,他们的敬业往往会令你自愧弗如。 我非常同意英国《金融时报》一位专栏作者的观点——如果所有人心中都多少有着工作五十年的观念,这将从三个有利的方面改变工作的性质: 首先,这将会减轻人们急于求成的心态。对多数人来说,工作寿命延续更多年、以更为缓慢的步伐不断得到修正,可能会更为妥当。 其次,如果我们都接受了工作寿命几乎没有尽头的观念,那么对于职业生涯来说,中途中断很长时间不会再显得那么危险。同时,让工作的鼎盛时期与家庭变动最大的时期重合在一起,委实是十分糟糕的人生规划。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是,一辈子只从事一种工作会被视为世界上最奇怪的事。但我还要加上一句——只要你把个人的愿景与组织的愿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项 “工作”也许几辈子都做不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