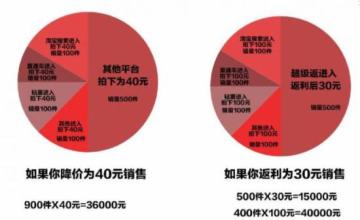第一章 灾难降临
2008年3月16日,我照常来到贝尔斯登上班,但这一次却和平常截然不同。首先,这是星期日,我上一次在周末上班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那时,股票市场在星期六照常交易。但这个特殊的星期日却细雨连绵,阴沉灰暗,似乎老天爷已经为我们即将面临的灾难铺设好了背景(高尔夫球大小的冰雹,再加上一场地震,或许更适合这场我们无论如何都意想不到的灾难)。临近中午时分,我赶到麦迪逊大街383号的公司总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刚刚过去的一周,肯定是贝尔斯登85年的历史中最疯狂、最诡异同时也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周。
偶然一现的坏消息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在坏消息到来时毫无准备。61年前,我搬到纽约,在贝尔斯登找了一份做秘书的工作。当时,这家投资公司还只有125名雇员。在快到40岁的时候,我成了贝尔斯登的当家人。在最高峰时,贝尔斯登总共雇用了15 000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正式头衔包括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及执行委员会董事长;我的主要工作始终是评估和管理风险。我的工作日通常是这样的:起床之后,首先阅读《纽约时报》和《纽约邮报》,早晨8点离开家门,8点15分坐到办公室里,整个上午的工作就是阅读《华尔街日报》及各部门提交的打印报告,了解公司前一天的资金管理状况及经营业绩。如果某个交易员当日的表现非常出色,我可能会马上抓起电话向他祝贺。如果情况相反,我会了解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9点30分股市开盘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通常要打十几个电话。在交易时间里,我必须随时在线,但也不像多数人想象的那么辛苦。我发现,绝大多数电话在超过30秒之后,便会出现收获递减现象。我有很多需要关注的事情,还有很多爱好,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闲聊的时间。如果你只是掏出腰包里的钱,然后就对徘徊在身边的风险置若罔闻,那么,你肯定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找不到饭碗。证券市场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它绝对不是赌场,在这里我们最靠不住的就是运气。一个优秀的风险管理者往往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我在很早就发现,这个原则是长期成功不可或缺的前提。第一章灾难降临在投资世界里,如果说赚钱不是唯一的目的,似乎有点故作清高之嫌,这显然是不真诚的。对任何金融机构来说,赚钱都是不二的追求。但无论是贝尔斯登最初作为一家私人合伙企业还是后来成为上市公司,我都没有把赢利作为企业的终极目标。贝尔斯登发展得越好,我们就能为客户提供越多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的资本实力也就越雄厚,我们就能雇用更多的员工,从而给更多的家庭带来幸福,我就会更加相信,社会存在才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因此,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贝尔斯登的明天更美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上周一,我们的股价开始下跌。到中午时分,股价已经下跌了10%,从每股70美元跌至每股63美元。股价下跌的部分原因在于,债券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刚刚下调了我们的公司债信用等级。但罪魁祸首还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毫无根据的谣言(我不知道这些谣言是否来自那些尽人皆知的阴谋家,他们早已是华尔街上声名狼藉的同流合污者)。我们的部分交易员最早听到这些传闻:坊间传闻,贝尔斯登已遭遇流动性危机。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本或信贷储备用于支撑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几十亿美元的交易,为各种各样的客户进行结算,其中包括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养老金基金和保险公司。银行与经纪商及金融机构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绝非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但是,有一种最简单的润滑剂滋润着这台巨大无比的发动机,这就是信任。对于任何一笔证券交易,如果当事人之间缺乏相互信任,任何人都不会从腰包里掏钱。怀疑和顾虑就是金融市场的空气,它们无所不在,而信誉和流动性则是催生恐慌的主要成分。无论是空穴来风的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的现实,坏消息就像不可治愈的传染病,一旦出现,便无法消除。在华尔街,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问题。而贝尔斯登股价的暴跌更是令人心惊胆战——转瞬之间,几十亿美元的市值便灰飞烟灭、不见踪影。但是在贝尔斯登,我身边的人并没有诚惶诚恐,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失望已经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2007年夏天,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不动产对冲基金经营失败。这次惨败总共让我们损失了10亿美元,这显然给公司声誉造成了不利影响。最近几年,此类资产一直在我们的总成交量中占有较大比重,也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但随着不动产泡沫的破裂,公司资产中的不良资产也开始大幅上升。因此,杠杆率较高的抵押担保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不仅拖累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也影响了我们的士气。进入2007年的第四季度,公司自1985年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亏损。但是在即将过去的这个季度里,尽管最终经营成果尚未报出,但肯定会实现微弱赢利——尽管数字不大,但总归比负数好看。在流动性方面,我们依旧拥有18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因此,我们缺少的并不是流动性,而是遏制谣言的能力。毫无疑问,苦口婆心的说服显然已经无济于事,我们需要借助于财经新闻频道公开辟谣。一位CNBC的记者打来电话询问我关于坊间流传的流动性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这样的说法完全是“荒唐无聊”。尽管我的评论被公开播出,但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效果。第二天,便有一些对冲基金结清账户。当天下午,我们的现金储备便锐减至30亿美元。到星期三的时候,大多数贷款人停止对贝尔斯登发放隔夜贷款,这让我们面对极其艰难的选择——要么找一家接受贝尔斯登净资产并代为承担负债的公司立即收购贝尔斯登,要么申请破产保护。在周末收盘时,贝尔斯登的股价跌至不到30美元,而就在14个月之前,股价最高曾达到每股172.69美元。我们都知道,到下周一的时候,如果没人收购我们,贝尔斯登这个名字将不复存在。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整个周末,大批银行家、投资银行家、并购律师、破产律师、税收筹划专家、证券专家以及来自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的官员都忙得不可开交。两个潜在买家对我们的财务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查,但都因为无法判断风险而感到棘手。在我们的资产中,到底哪些是真实的资产,到底应该如何评估这些不可交易的有价证券的价值,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到星期日早晨的时候,便只有摩根大通银行一家留下来了。在离开住宅去参加这个董事会紧急会议时,我就已经在想,摩根大通到底会给我们开出怎样的报价呢?但是在我到达会议室时,摩根大通也决定撤回报价,有人建议我可以回家了。就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我接到另一个电话,要求我马上返回。贝尔斯登董事会于下午1点召开,距离澳大利亚股市星期一早晨的开盘时间只有6个小时——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搏的最终期限了。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一直认为,一旦贝尔斯登破产,多米诺骨牌效应将极有可能引发全球经济恐慌。而摩根大通则坚持,只有财政部同意提供300亿美元贷款,对贝尔斯登资产中信用等级最高的抵押担保证券提供担保,他们的领导层才能接受政府的安排(这就等于说,摩根大通同意接受第一个10亿美元亏损,只要这些有价证券日后能溢价卖出,联邦储备银行就能实现利润,即:美国的纳税人就会成为受益者)。显然,最大的损失者就是贝尔斯登的股东。就在前一天,我们还以为摩根大通会报出每股8~12美元的价格,但那毕竟是昨天。但是现在,我们的首席执行官阿兰·施瓦茨(Alan Schwartz)告诉大家,我们得作好接受每股不到4美元报价的准备。他的前任詹姆斯·吉米·凯恩(James E.Jimmy Cayne)当时仍在担任贝尔斯登的董事长,如果不是阿兰劝他回来的话,恐怕凯恩还一直在底特律参加桥牌锦标赛呢!听到阿兰的话,凯恩勃然大怒。他认为,如果只是每股4美元的话,为什么不申请破产保护呢?会上,还有几个人同意吉米的想法,但他显然是在意气用事。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持有566万股的贝尔斯登股票,这毕竟是曾经价值高达十几亿美元的财富啊!但他的愤怒最多也只能反映他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相信,即使没有这些股票,吉米一样能照常生活,支付电费和房租。但我们的雇员怎么办?可以肯定的是,破产就意味着清算,这也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规避的结果。在贝尔斯登,相当一部分员工都在用个人储蓄投资于自己公司的股票。清算就意味着我们的股票将一文不值,还要让14 000多人失业在家。在摩根大通确定最终报价之前,整个会议室里的气氛极其压抑。他们的最终决定是:以每股2美元而不是4美元的价格收购贝尔斯登的全部股票。在考虑全部或有负债之后,最后的总收购价格为2.63亿美元,或者说,只相当于贝尔斯登最有价值的非流动资产(总部办公大楼)市值的1/4。“我不接受2美元的出价。”吉米说。“吉米,如果我们不接受这2美元,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对他说,“即使他们报出每股50美分的价格,我们也要接受,因为这表示至少我们还活着。如果你死了,除了想想上天堂还是入地狱之外,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你同意我们在今天晚上就宣布破产吗?”他什么都没有说,在那个时刻,任何语言都没有意义了。不管怎么说,在晚上7点这个最后期限之前,我们毕竟做成了贝尔斯登的最后一笔交易。你也许会说,我们只是完成了一次复杂的器官移植,然后就只能靠生命维持系统维持生存;或是只比僵尸好一点儿,把尚健康的几个器官移植到另一个活体上。不管怎么说,贝尔斯登的一部分幸存了下来。在投票表决结束一个小时之后,我乘坐出租车回家了。虽然心里隐隐作痛,但是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明天早晨,我还会像往常一样来这里上班。那一天乃至那一周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可能改变我的管理原则和投资信条,它们是我对这份职业的毕生承诺。但不可否认的是,按照这个行业里的任何标准,这场变故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毁灭性灾难,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我们曾骄傲地以为,作为一家独立的投资公司,拥有85年光辉历史的贝尔斯登是永远坚不可摧的,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但是,这个假设现在已经不攻自破。我们的未来将会怎样?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