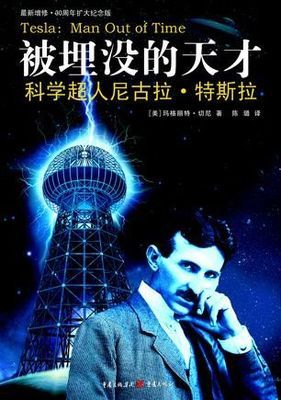第四章 成长的轨迹
1948年,约翰·斯雷德因暂时休假离开风险套利部,作为美国夏季奥林匹克代表团的一员,斯雷德参加了伦敦奥运会的曲棍球比赛。不过,美国曲棍球队空手而归,他们输掉了全部比赛,斯雷德的位置是守门员。不过,他得到的奖励却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一套奥运会运动服。在整个比赛期间,斯雷德一直自豪地穿着这套运动服(据我所知,他只有在洗澡和睡觉时不穿这套运动服)。 比赛成绩不佳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激情,他利用这段时间拜访了几家欧洲银行。此时,他的身份马上就变成了贝尔斯登的代表。
在成为约翰·斯雷德之前,他在德国用的名字是汉斯·施莱辛格。年轻的汉斯一直野心勃勃,他原本希望能在柏林、法兰克福或是日内瓦实现自己的银行业梦想,直到有一天,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如发现任何犹太人当众亲吻女士,将被处以监禁。”他马上意识到,一定要移民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1936年,他远渡重洋,来到纽约。一踏上美洲大陆,斯雷德就在贝尔斯登找到了一份做信使的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在不同的公司之间传递信息和证券,每周的工资是15美元。在泰德·洛(他自己的原名是洛温斯坦,在我遇到的犹太人当中,也不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名字)的劝告下,汉斯·施莱辛格马上改名为约翰·斯雷德。12年之后,斯雷德再次来到欧洲寻找潜在客户。事实证明,那套奥运会运动服给他带来的收获只是暂时的,最多也只能让斯雷德得到一个见面的机会,仅此而已。但是,斯雷德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在日内瓦,他找到一家银行,下了一份购买1 000股皇家德意志公司股票的订单;然后,他又随便再找一家银行,下了一份卖出这1 000股股票的订单。佣金是50美元。实际上,这50美元是为日后合作播下的种子。从技术上讲,贝尔斯登现在已经和两家瑞士银行“做成了生意”,如果多一份想象,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贝尔斯登的海外部已经开始萌芽,只不过还没有成型。第四章成长的轨迹回到美国,斯雷德依旧没有闲下来。铁路和公用事业的重组大多已经尘埃落定,从总体上看,并购活动已呈明显减少趋势,每个月只有一起左右。尽管最初设立海外部的计划一直没有得到落实,但这个想法至少具有指导作用:与欧洲银行建立业务往来,鼓励它们购买美国公司发行的有价证券,由贝尔斯登充当经纪人。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但是,斯雷德已经有点儿厌烦风险套利业务了,他急于让贝尔斯登脱胎换骨。尽管没人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还是想办法让他们知道,如果斯雷德另有高就,我希望能成为风险套利部新的领头人。我认为,在风险套利部处于低潮期的时候接手,无疑是接过一个烫手的山芋。斯雷德并没有反对,塞尔和其他高级合伙人也没有意见,于是,在1953年春天,我正式接手风险套利部。尽管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我的运气似乎依旧不错。股票市场即将步入8年的牛市周期——到底算不算牛市,谁知道呢?这也许是股市历史中最长的牛市。经济形势正在转暖,企业的胃口越来越大,收购业务越来越频繁,风险套利逐渐活跃,而且油水也越来越大。有些套利者喜欢借助于第三方的独立律师,把目光集中到新发起的收购或合并上(多年前,伊万·波斯基就声称这是自己最喜欢的套利方式。他经常吹嘘,自己有一个庞大的会计师和律师团队,他们的工作就是分析每一笔新的并购交易。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依据这些专业意见作出的决策,清一色地以失败而告终了。而他的成功,却无一不是借助于贿赂银行家和律师得到的内幕消息)。我的起步方法就是从理论上对每一笔交易进行研究,然后预测未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这种方法似乎很有效。只要注意到存在有利可图的机会,我就会马上给收购公司的财务总监打电话,询问我们最快可以在什么时候就收购达成文件——当然,它们并不属于内幕消息,而是对外公布的资料。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研究部”几乎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帮助。当时的研究部只有一个人——戴夫·莱维。只要你问他问题,他总能给你一个答复,至于这个答复是否令人满意,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一个人怎么能了解8 000家美国公司呢?莱维当然也做不到。公司管理层对这种方法的理解可以归结为塞尔·刘易斯的一句话:“在牛市里,我们不需要研究部;在熊市里,研究部会吓死你。”在当时的环境下,把我的交易方法称为“跟着感觉走”似乎很贴切。父亲经常用零售业的情况说明道理,“如果你不打算在应收账款上赔一份钱,那就意味着你永远不会有潜在客户”。风险套利也一样——如果你过于谨慎,就没有办法玩这种游戏。在风险套利中,你肯定要涉足很多笔交易,虽然你希望每一笔交易都能赚钱,但如果你不在其中的某些业务中赔点钱,也就没有赚大钱的机会,更说明你的工作还不够努力。没人怀疑过我的工作原则。此时,我还与约翰尼·罗森瓦尔德住在同一所公寓,他是在1954年进入贝尔斯登的。约翰后来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同时也是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销售员之一。那段时间,我们一起坐车上班,经常在一起对公司的薪酬体系互诉怨言。通常,我们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和相当于5倍基本工资的红利奖金。合伙人经常会告诉你,这就是你的全部收入,如果你不满意,“等到明年再说吧”。在负责风险套利部的第一个年头里,我的全年奖金达到了35 000美元,在1954年的时候,这显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你不能光看收入,而忽视我对公司利润的贡献。我找到了戴维·芬克尔,发了一顿牢骚。同一年,圣母大学刚刚聘用25岁的特里·布莱嫩担任美式橄榄球教练。戴维问我多大年纪。我觉得戴维是想让我领他的人情。我告诉他,“我比圣母大学的主教练大两岁”。他忍不住大笑,对我说:“你在挑我的理了。”我们的会面就这样结束了。尽管这次谈话暂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变化,但是从长期来看,我的身价还是有所提高。很快,我的年薪就涨到了10万美元。每每提到我的年薪,我就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与泰德·威廉姆斯的收入相比,这个数字已经很可观了。之后,我遇到了麻烦。某些客户成为我们交易室的常客并不是什么难得一见的事情。他们几乎在每个工作日都要出现在贝尔斯登的交易室,而且也要占据公司客户代表的办公桌,看着客户代表执行他们的交易。如果你不了解情况的话,还会以为他们也是贝尔斯登的雇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此时的中产阶级依旧是提倡勤俭节约的守财奴。直到20年之后,他们才变成对信贷如饥似渴的消费者和对冒险乐此不疲的投资者。至于在线折扣经纪商则是更遥远的未来了,人们更是不会有这样的幻想:只要有一台计算机,对市场有感觉,手里有1 000美元,你就可以杀入股市,打败市场。我认为这样的想法太离谱)。在交易室的常客里,有一个名叫约翰尼斯·斯蒂尔的人,他是一名专门研究政治和经济的报纸专栏作家和电台评论员,在政治取向上具有明显的右翼倾向。他曾写过一些稀奇古怪的文章,让人们觉得他更像是一个预言家:他曾提前一周预测到“珍珠港事件”,在晚年的时候,他又预测到了1987年10月的股市大崩盘。但是,他在预言希特勒的灭亡时间上似乎有点儿太乐观。|!---page split---|斯蒂尔曾向我们推荐了一家位于阿拉斯加州的金矿企业,但我已经记不清他当时的具体说法了。(我真希望自己后来能预言到最糟糕的情况:斯蒂尔被指控涉嫌股票欺诈。)他给我和其他五名客户代表印象最深刻的是,只要我们帮他卖出股票,他就会让我们优先购买。对他看好的股票,我们当然也愿意接受,最后,我把这些股票卖给父亲和他的兄弟,还有加斯·林,我为自己也买进了一些。所有这些交易都是公开进行的。在我们的心目中,斯蒂尔就是贝尔斯登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之处。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违反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条规定:雇员在代表客户执行证券交易过程中获得的报酬,均属于其所在的经纪公司。但如果由贝尔斯登获得该选择权,然后再转交给我们,那就是合法的。因此,我们均被指控技术违规,并被调查了近两个月之久。我利用这段时间到俄克拉何马城进行了一个计划之外的休假。这让母亲喜出望外,因为她曾经说过我再也不会回家,您可能还记得她的话吧。尽管我的失足给贝尔斯登的老家伙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但此后从未有人向我提到过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歉疚。不到两年之后——也就是在1958年,我在31岁的时候成了贝尔斯登的合伙人。我之所以能够深刻了解风险套利,还要感谢一位对我帮助最大的导师,伯纳德·拉斯克(Bernard J.Lasker),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巴尼,他是一位注重实效、头脑冷静的套利大师(后来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巴尼和我是在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认识的,我们都是这家俱乐部的会员。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尽管他的年龄是我的两倍,但这丝毫未能影响我们的忘年交。之后,我们便定期在交易所的餐厅聚会聊天。他经常会关心地询问:“最近过得怎么样?”我们简单地寒暄几句之后,他就会告诉我:“好吧,再替我买1万股。”或是说些其他让我高兴的事。我们的佣金水平很高。实际上,有很多人可以替巴尼买卖股票,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取悦于我。即使买进股票,他也不会持有很长时间。他对我们的一贯原则就是:“如果股价涨1点,就继续买进;如果再涨1点,马上通知我;如果下跌2个点,马上抛出。”这个冷酷而简单的建议道出了股票投资的真谛——及时止损,有钱就赚。这个原则也成为我日后最根本的投资秘诀。但是,为什么大多数投资者却未能掌握这个原则呢?塞尔·刘易斯甚至发现,很多投资者正在做相反的事。塞尔的优点恰恰也是他的缺点之一。作为销售员和交易员,最让他名声显赫的是勇敢和自信,而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他一贯的成功纪录。但是在内心深处,他根本就不习惯于接受亏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这段鼎盛时期里,贝尔斯登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三个部分:为机构投资者提供的经纪交易、套利交易及公司的自营交易。此外,塞尔还联合高盛的格斯·利维率先开展了对机构投资者提供大宗普通股交易的业务。例如,如果我们通过自有账户持有1万股××公司的股票,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公开市场上分批卖出这些股票。通过大宗交易,也可以对多笔交易打包,进行一次性交易。在进行大宗交易时,贝尔斯登的合伙人就必须把大笔资金投资于某一只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股票。塞尔认为,贝尔斯登买进的所有大宗股票都会上涨,原因很简单:他是股票的持有者,他手里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这需要对市场走向作出相当精确的判断。股价的微小变动就会转化为相当可观的利润。但是,把胜负寄托在某个人永远不会犯错这样一个前提上,显然是一把风险很大的双刃剑。目标股票的卖家是已经研究过这只股票的金融机构,很多股票的代码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听说过。说得直白一点,我们就是赌场中最容易出错的一方,而对股票的卖家更是知之甚少。1954年,斯蒂尔斯去世了,贝尔也辞世了。在随后的一年,戴维·芬克尔退休了。在这个时候,约翰·斯雷德找到了我,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请求:我是否愿意接替戴维的位置,担任交易部的主管,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我是否愿意做塞尔的助手。这不是让我自找苦吃吗?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婉言谢绝了。无论是在待人接物还是经营理念上,塞尔和我之间几乎就没有什么共同点。而且当时我还不是贝尔斯登的合伙人——那是1958年的事,但是在工作中,我一直把自己当做合伙人。我认为,在表面上,我和塞尔完全能做到和谐共处,而斯雷德的要求将会彻底改变整个游戏的内容。尽管斯雷德也知道我的苦衷,但是他认为,眼前的意外打击已经让贝尔斯登陷入危机,甚至让贝尔斯登的未来蒙上了阴影。“只有你能接过这个重任,”他说,“因为这个位置将成为塞尔的继承人。”奇怪的是,塞尔居然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异。谈到我更喜欢抛售股票的时候,塞尔在几年之后曾开过一个玩笑,“艾伦把股票当成了卫生间的手纸”。的确如此,只要是我觉得股票表现不尽如人意,我就会像扔手纸一样扔掉任何股票。我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好。我甚至根本就介意他告诉记者:“艾伦永远是一个比我更出色的交易员。如果他持有一只股票,只要股价下跌,他就会马上抛出。即使这家公司的总裁是他的母亲,他也不在乎。只要价格下跌,就必须卖掉,生意就是生意,生意和感情完全是两回事。”这句话似乎表明,塞尔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客观公正,但这并不表明他已经掌握了改掉自己老毛病的自律原则。我自己的信条来自父亲的另一句忠告:“如果市场发生了变化,今天就卖掉,因为它明天也许会更不值钱。”我逐渐理解了巴尼和我曾经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没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个公司内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即便是这家公司的总裁也一样。他们只是感觉自己了解而已。如果一只股票最初的表现差于大盘,可能有两种原因:要么是股票的异常变动,要么是公司确实出现问题的一个信号。但不管是哪个原因,都说明已经到了该退出的时候。我说的情况不包括大盘下跌,仅指大盘走强、个股下跌的情况。如果个股下跌确属市场的不规则波动,只需重新购回即可。根据我的经验,均价本身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随着股价下跌,持续买进,以不断降低每股平均价。对于这种做法,我有一个忠告:如果你的目标是在公司即将破产时成为最大的炒股人,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塞尔似乎认为,只要他买进一只股票,这只股票就不可能下跌(即使股价下跌,也与正常情况毫无关联,不值得关注,不需要记住——然后,继续保留在公司的账户上)。这样的自信让我很难接受,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自负和错误。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塞尔对合伙企业的整体利益漠不关心。这也导致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到1960年,我已经在贝尔斯登工作了11个年头,也是我做合伙人的第二年,我持有公司3%的股份。尽管贝尔斯登依旧赢利,但塞尔仍然无法改掉守住赔钱的股票不放的习惯。1962年春季,肯尼迪总统成功地拯救了美国大型钢铁制造企业,整个行业进入复苏期,钢铁价格开始上涨。通常,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经济整体过热,形成通货膨胀。美国企业界担心政府会采取进一步干预措施,从而造成股市急转直下,持续低迷。这样的形势让我非常气馁。对于塞尔的固执,我早已经忍无可忍。股市的颓势,再加上糟糕透顶的不满和郁闷,让我感到一片迷茫。每次查询公司投资账户时,我都会看到很多毫无理由继续持有的股票,而每次都会让我浑身不自在。最后,我终于再次鼓足勇气,在一个下午来到塞尔的办公室,我提出了辞职申请。“你不能辞职。”塞尔说。“我当然可以辞职。”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根本就不会理解。”“不行,你必须说清楚,”他再次显露出自己的固执,“你知道我家在哪儿,今天晚上到我家,把这件事情和我讲清楚。”于是,我在晚上去了塞尔的家,这是位于公园大道73号的一个豪宅,共有18个房间,7个洗手间。我非常熟悉这里,因为我们经常在周末到这里打桥牌。塞尔一直是一个人,家里只有一个男管家。我们的谈话是在藏书室进行的,两个人都开门见山。“好吧,你说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辞职啊?”“你听说过拉德·麦里吉恩这个名字吗?”我问塞尔。“没有,这是个什么东西?”“是一只股票的名字,是你买进的股票。我们现在持有1万股这只股票。股价已经从每股20美元跌到5美元。我们还有20种类似的股票。对这种情况,我一天也不能忍受了。”他坐在座位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说:“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我没有办法卖掉这些破东西。”我没有答话,希望能听听这些尚不知道的事情。最后,他终于谈到了这个问题:“好吧,艾伦,我和你也做一笔交易。从现在起,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卖出任何股票,即使出现亏损也无所谓。你听到了吧?任何交易都可能会赔钱。我自己也保证,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学着接受亏损。同意吗?”“同意。”第二天,在我来到办公室时,塞尔还没有来。我给指令部主管莫·贝克尔打了一个电话,并告诉他:“给我一支铅笔和一张纸。我要给你布置几个抛出指令。”我拿起公司的股票明细账说:“卖出1万股拉德·麦里吉恩,卖出2万股XYZ公司的股票,卖出1万股这只股票……”我突然注意到,身边的人都不说话了,都在盯着我。他们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几分钟之后,股市开盘。贝克尔拿起电话,给我们在交易所的首席经纪人比尔·梅尔打电话。比尔是一个出色的家伙,我非常喜欢他,他也是贝尔斯登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持股比例最大的合伙人。但是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不想绕过塞尔。他想知道这些指令是由谁发出的。贝克尔告诉他,是我发出的指令。于是,比尔在交易所外找到一部电话,在电话中问我-爱华网-:“你想找死吗?”我说:“没问题,我昨天晚上和塞尔谈过了,我们不能再守着亏损的股票不撒手了。我们必须卖出这些股票,这只是个开始。”“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向他保证,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这个决定的。当时,一个大型并购案件还在审理当中——著名化工企业美国纤维胶公司(American Viscose)可能被收购,但政府以违反反垄断法而制止了这笔交易。我认为这次并购最终很可能会得到批准,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孤立。我告诉比尔,我打算把清理这些亏损股票的收入买进美国纤维胶公司的股票,价差收益非常可观。华尔街最大的投机商之一乔·格拉斯对此深信不疑,他一直鼓励大家去买进美国纤维胶公司的股票,因为“它们似乎不比国库券差”。就在我们执行抛出指令的时候,我对比尔说:“如果这次合并没有通过,那么,你就回到内布拉斯加的老家,我准备坐船回俄克拉何马。”实际上,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被我们抛出的股票可能会全线上涨而美国纤维胶公司的股票则一路下跌的情况。幸运的是,在六个星期之后,并购案最终得到批准。|!---page split---|这个插曲成就了我的事业,也成就了贝尔斯登。很多年之后,当我想再次转变贝尔斯登的战略方向——大幅扩张零售网络,或者建立一个大型清算中心时,塞尔依旧没有阻拦我。塞尔从来没有破坏过我们之间的协议,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为了帮他以更宽的视角看待市场,我提出了建立风险委员会的建议,对大量收购或持有某一只股票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并对公司投资于各市场板块的资金效率实施跟踪。这个委员会由我和其他几位合伙人组成。但是,塞尔对这道程序感到很不耐烦,于是,风险委员会的设想很快就夭折了。不过,随时抛售任何发生亏损的股票依旧是我的权利。偶尔几次,塞尔曾经试图说服我回心转意,但我从不让步,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呢?业绩记录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在股票市场顺利时,风险套利部创造的利润占到公司全部利润的50%;在熊市年份里,公司的利润几乎都来自我们的部门,风险套利部就会成为贝尔斯登的顶梁柱。不过,只要塞尔还负责股票交易,我们每年都要不可避免地浪费一大笔资金。因此,我们之间每隔一段时间还是会爆发一场争执。例如,他曾从华纳通讯公司的斯蒂夫·罗斯手里批量买进10万股AT&T的股票,之后股价持续下跌,我认为应该立即抛出这只股票。我的建议终于触发了他的老毛病。“你不能卖掉这只股票。”塞尔说。“为什么不能?”“它就代表了电话,你不能把电话也卖掉。”他的意思很清楚,AT&T就是上帝和母亲的同义词。我说:“塞尔,除了股票,它什么都不是,它做什么业务与我们无关。”但他这一次显然不准备让步,坚决反对我的意见。“等等,”塞尔说,“我们还是让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吧。”在交易室,我坐在塞尔的左边,右边是约翰尼·罗森瓦尔德。由于是一次私人谈话,我们选择了他的玻璃墙办公室。我们关上会议室大门之后,塞尔说:“约翰尼,我刚刚以大宗交易的方式买进了AT&T的股票。我认为这只股票肯定会上涨。如果我的判断正确,我就会给你们和其他年轻合伙人带来一大笔利润。”约翰尼说:“不过,塞尔,如果它继续下跌的话,就会让我们的年轻合伙人损失一大笔钱啊。”我感觉塞尔差一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离开办公室之后,我马上开始抛出AT&T股票,之后,这只股票持续下跌。直到几年之后,它才开始反弹。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套牢这么一大笔钱,等着这种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事呢?从此,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如果我卖掉塞尔买进的股票,他什么也不说;但如果随后出现反弹,他就会在自己的计算机里标出这只股票。这样,电子报价机的定期汇总报告中就会突出显示该股票,所有人都会注意到这些突出显示的股票。有一天中午,塞尔去吃午饭,我走到他的计算机旁边,清除了他跟踪的所有股票,然后输入我在前12个月里卖出而且一直没有反弹的股票。塞尔回到办公室时问:“这是什么?”我说:“塞尔,我觉得你应该看看你买进的那些一直表现很糟糕的垃圾股票。”我们之间的矛盾有点儿像永无休止的游击战。两年前,我们在塞尔的公寓开会之后,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具戏剧性的口角。这一次的起因是他大宗买进赛拉尼斯公司(Celanese Corporation)发行的可转债。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注意到这只债券的表现一直差强人意,于是,我决定抛出。但塞尔马上编出一大套新颖、独特的逻辑。“你想干什么?”塞尔说,“你不能卖掉它们,它们是债券,不是股票。”“塞尔,债券也会贬值。我们得卖出了。”(在2008年,我们会发现债券价格一样会快速下跌,给投资者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如果你打算卖出,我马上就买回来。”他说。“好吧。你想要多少?10万美元够吗?”我转向坐在交易台上的助手马尔文·戴维森,“马尔文,填一张交易单。你把10万美元的赛拉尼斯债券卖给塞尔。” 马尔文目瞪口呆,“还要吗,塞尔?”“是的,我再追加100万美元。”“马尔文,再填一张单子……还想要吗,塞尔?”塞尔又加了100万美元,然后,他径直走向大门,赶着去新泽西度周末,一边走一边对我说:“我们星期一早晨再见!”我依旧继续抛出债券。星期一上午,我很早就来到办公室,我已经做好了揍他一顿的准备,我真想杀了他,只不过这不太可能,因为他的体重足足比我多出100磅。这当然是玩笑,撕破脸皮当然毫无必要。就在我刚要质问他的时候,塞尔首先说话了:“我错了,你是对的,我向你道歉,我们都回去工作吧。”随后的几件事再次确认了我们在他的公寓里已经作出最终摊牌的事实。在名义上,塞尔可能一直是贝尔斯登的老板,但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对我个人以及贝尔斯登历史来说都至关重要的时刻。我对塞尔在交易习惯上的彻底否定,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已经接管了贝尔斯登的指挥权。我们两个人彼此都清楚这一点,贝尔斯登的每个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奠定了贝尔斯登之后40年的基本领导构架。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