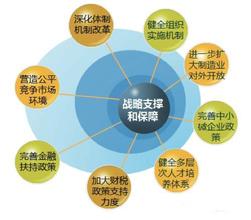从2008年中央政府首次启动“大部制”改革以来,各地政府纷纷效法中央,一时间,“大部制”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所无法绕过的一个关键词。如今,“大部制”改革自提出起已经过去了两年有余,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我们不难看到诸如深圳模式、顺德模式、成都模式、随州模式等形形色色的地方模式已经相继涌现。各地改革的样板纷纷树立,这自然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在进行到30多年后的今天,改革本身已经被提升为一种价值、一种正面符号。这就导致很多利益的重组与博弈—无论是否在根本上利于民众—都会打着改革的旗号或披着改革的外衣进行。也正是基于此,我们今天对于各地“大部制”改革的近距离检审才显得格外必需。大部制改革的背景时代周报:十七大以后,“大部制”这个名词首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且在数年之内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涌现了“深圳模式”、“成都模式”、“顺德模式”等各有特色的地方大部制改革样板。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大部制改革”热呢?肖滨:关于提出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只要你去搜索一下这些年无论是学界、官方还是社会舆论方面的一些分析,我想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一些说法。但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我想首先要注意到的一点是中国经济增长这个大背景,或者可以更确切地说,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这样一个背景。如果我没有记错,大部制第一次提出是在2008年3月的两会期间。从1978年到2008年正好30年,30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一个长足的进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来了,下一步中国该怎么保持增长?一般来说,我们肯定会说要调整经济增长的方式。但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绝对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领域本身的问题,换句话说,它也不仅是一个经济改革的问题,这种调整肯定要涉及政府层面的改革。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政府也很清楚:如果在经济上不能保持一个较高位的增长,这个社会必定会出大问题。第二个背景还是要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整整30年,一方面是私人空间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诸如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自主空间也在不断扩大。此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这些宏观描述背后隐藏的就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和缠绕,不断涌现的社会冲突已经严重压迫着现有的这个政府。这里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30年的经济增长虽然做大了蛋糕,但在分蛋糕上却失之公平。当然,我并不是说大部制改革可以包治公平缺失的问题,但大部制改革的初衷确实与分蛋糕相关、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相关。面对社会层面这么大的变化,国家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所以概括来说,大部制改革的首要一个背景是如何调整做大蛋糕的方式,第二个背景在是如何调整分蛋糕的方式。|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55239|25时代周报:是否可以这样归纳,这次改革的第一个背景基本是政府与改革开放以来培育起来的市场领域的一个呼应,而第二个背景则是政府与正在成长的社会领域的一个调适。肖滨:我同意你的归纳。不过,我认为还有第三个背景。政府机构的改革实际上是老生常谈,从1982年至今,我们至少已经经历了5次行政机构改革。在历次改革中,我们都作出了幅度不小的改革,举个例子,现在的政府机构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计划经济时代耳熟能详的“轻工业部”、“冶金部”、“机械工业部”等一些为单一行业而设的部门了。又比如我们之前颁布了《行政许可法》,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概念。这说明我们的政府机构改革一直是有延续的,大部制改革只是政府机构改革这样一个总体图景中的一个新阶段。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我们改革的步骤在应对社会巨变上还是有点滞后,在落实先前制定的法律法规上还是有不足,但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我们是拥有改革承接的,我们的政府本身是有改革动机和传统的。全球化是第四个背景性因素。全球化力量的不断增长及其对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冲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在英美闹得沸沸扬扬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一理论的本意是通过引入市场力量,解决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低下的困境。但这一理论在90年代一经介绍到中国,马上得到了应用,结果造成了很多原本属于政府的责任被推给了社会和个人。就中国具体的情况而言,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这一问题当然也很严重,但当时改革实际的原因却是为企业“甩包袱”,而不是让民众的福利增加。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博弈时代周报: “新公共管理运动”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提高公共物品提供的效能,在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引进企业模式。但其前提是公共物品的分配基本是公平的,而且政府承担着很大的一部分责任。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公共物品的分配是很不公平的,很多该国家承担的责任国家也没承担起来。这就导致新公共管理的举措一进来,很多公共物品的提供机构开始产业化,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很多问题都被推给了个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努力学习。但在很多时候,限于各自社会状况的不同,反而起到反效果,大部制改革是否也有这种问题?肖滨:我赞同你的忧虑。尽管从初衷上我并不否认大部制改革的良好动机和愿望,但在具体的改革利益过程,毕竟要涉及很多切实利益的分割。愿望是一回事,具体的改革又是另一回事,既得利益者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益被吞噬。况且,政府本身肯定也是有其利益自主性的。大部制改革和之前的很多改革一样,某种程度上都是参照西方改革模式的产物。但真正进入改革阶段,这就是一个各方进行利益博弈的阶段,很多部门在面对大部制改革时发现自己完全被裁掉了。面对生死问题,各个部门肯定会奋起抗争。如果持续地保持不能缓和的竞争,那么很可能原先的改革计划就会流产,或者即使表面改革的了,实际上却沦为几个部门进行利益分赃的勾当。时代周报:正如您所提到的,大部制的改革必定会涉及激烈的利益博弈,相对而言,基层不像中央那么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否改革的阻力就相对较小,您一直在观察广东的大部制改革,您能谈谈广东大部制改革的一些具体情况吗?肖滨:的确,要谈改革中利益的处理技巧或艺术,我们必须要回到具体的改革案例中。坦率地说,地方层面由于牵扯的利益方相对中央各部委要少很多,所以改革起来相对容易一些。而且对于我们学者而言,观察起来也更为方便。我这里举一个例子,顺德的改革中有一个较为温和的处理方式,就是在新的部门设立一个“局务委员会”,将很多原先部门的副职官员纳进去。这些“局务委员会”的存留要看情况,如果需要就长期保留,如果不需要就逐渐裁撤,但至少让原先的副职官员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归宿。这些措施对于缓和改革的反对声是很有好处的。基层改革动力停留在治理需要时代周报:对于很多民众来说,大部制改革和之前的政府机构改革一样,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在于“精简机构”。但从2003年起,政府在提机构改革的目标时逐渐将重心转向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精简机构已经只是作为改革的一个附属目标?肖滨:我认为谈这个问题还得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比如“文革”结束之后的80年代,由于当时很多平反的人都重新进入了政府机构,造成政府机构极为庞大,我记得当时国务院部委数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数目。所以,从早期来看,精简机构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也是一个深入人心的目标。但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仅仅是精简机构这一目标显然不能涵盖政府改革的所有诉求。以顺德这样的县域政府为例,当地政府除了要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应对各种上级机构的事务,更重要的是,直接面对基层的他们必须要应付各种具体矛盾、冲突、突发事件。只要看到了这一点,我想今天的大部制改革就不可能单纯为了精简机构这一目标。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打造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从基层的角度来看,大部制改革的目的则在于打造一个可以应对更多更复杂社会问题的治理型政府。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从字面上理解主要是机构的合并与整合,但这里的合并并不是简单的人员、机构合并,而是要在组织架构、决策方式、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融合和重组。可以说,大部制改革不是物理反应,而是化学作用。时代周报:您刚才提到了顺德大部制改革,媒体上一般把广东的大部制改革划为三个模式,即广州模式、深圳模式和顺德模式,您能做一些比较吗?肖滨:广东的大部制改革走得比较前面,但如果从典型性来看,我认为主要还是深圳和顺德两种模式。深圳模式可能媒体报道得比较多,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08年之前。早在于幼军主政深圳之时,他就提出了决策、执行和监督“行政三分制”的政府架构,这基本是一个行政体系内部的改革。到了2008年大部制改革提出以后,深圳方面直接实现了与中央政策的对接,这一行政体系内部的改革当然是很富有意义的。尽管在我看来,深圳市的党政机构的僵硬并没有因为高度市场化而异于内地的很多政府,但深圳市敢于先从行政系统做改革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改革的尝试。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任何一种地方改革都是值得鼓励的,因为只有改革进行下去了,我们才能真正知道哪一种改革的模式更好。那么,相对于深圳市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改革,顺德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党委和政府一起改,顺德方面叫做“党政联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地方,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改革一直局限于行政系统内部,都没有把党委拉进去。但在我们国家权力的实际运作层面,党政完全是交织在一起的,分不开的。尤其是在基层,党政的重合、粘连程度更高,在面对非常复杂的社会局面时,如果仅仅从行政角度进行改革,而不涉及党务系统,改革的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因此,先不说顺德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效果,仅仅从“党政联动”这一理念来看,就值得我们重视。|!---page split---|时代周报:是否可以这样讲,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是有不同的改革目标?中央可能更注意经济增长,这是关乎全国政治稳定的事情,而地方政府则比较关心直接的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肖滨:是的,对于顺德这样的基层政府来说,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基层治理,如果社会不能稳定、不能和谐,不但要面对来自官僚系统上层的压力,也无法实现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护航保驾。我记得顺德的地方领导曾说过这样的话:“改革之初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河水深了,没有石头摸了,你不过河?你也要过,潜水也要潜过去!”对于基层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决策权,主要就是执行权,目的就是要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所以,现实层面非常严峻的挑战要求顺德地方政府在改革时必须要尽可能调动最大的资源,作为掌握巨大资源的党委没有理由不纳入改革的范围。从目前来看,顺德的做法是一种比较令人赞赏的回应模式,顺德的做法没有拘泥于一些意识形态或者条条框框,而是从实际出发,开辟出符合实际逻辑的一条改革路径。“社会工作部”需警惕吞噬社会时代周报:顺德作为一级县域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遭遇来自上下级政府的阻力。比如乡镇一级持什么态度,又比如顺德将41个县府机构改编成16个,这里如何与上级厅局对接,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要如何解决?肖滨: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可能相对而言下级政府的阻力要小一些,毕竟下级的乡镇也是基层政府,他们的改革可以在县(区)一级政府的主导下配套进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和上面的各个部门打交道,举个例子,顺德大部制改革之后把财政局和税务局改编成“财税局”,但上一级政府不可能有一个财税局。所以顺德采取的办法是保留财政局和地方税务局的牌子和公章,但人事编制和组织架构已经融合,简单地说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类似的情况有很多,比如社保、教育、城建、卫生、安监组成经济促进局,统战部与民政、外事、侨务、农村工作等部,再加上共青团、妇联、工会、残联等群团系统一起合并为社会工作部等等。这些部门的整合都需要与上面做好对接,反过来说,没有上面的支持肯定是不行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顺德的改革不能违法,必须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顺德不是一个改革特区,在法律上没有可破例之处。所以,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改革,但同时又要处理好法律问题。顺德采取的办法就是将问题细化,在可执行的空间内消化掉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局务委员会”,设立这个机构也是得到上面同意的,因为很多原先的副职领导干部也是人大选举上去的,不可能你说改革马上就把他们拿掉。另外,前面提到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也会涉及法律问题,但这一模式并非顺德首创,中纪委和监察部不就是这样的情况吗?顺德的改革不过是把这种情况照搬过来,这样就避免了很多法律问题。所以,这样看来,顺德今天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端盘子”,不但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诉求,还要避免触及法律问题,更要与上下级实现良好对接。时代周报: “社会工作部”是统战部整合了很多原先的行政机构和群团系统而形成的一个大的统战部,这应该就是顺德改革的“党政联动”的体现?

肖滨:是的,对基层的统战部门来说,坚持以往的统战工作模式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面对今天社会的很多变化,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也是很有必要的。顺德改革虽然将统战部置于社会工作部内部,但实际上它的统战工作面反而扩大了,因为除了原先的统战,它还涵盖了民政、共青团、妇联、工会、残联等各个部门。另一个变化在于,统战工作在法理层面获得了更多支撑,因为在一个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政党直接治理社会并不是一个很合时宜的做法,政党只有借助政府机构才能进行干预社会。那么,现在顺德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党务系统拉进政府系统,这样一来,党务系统在进行社会管理时便可以名正言顺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