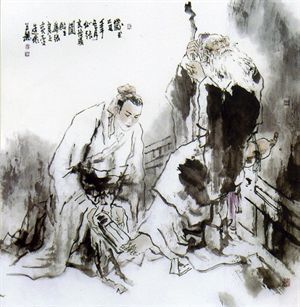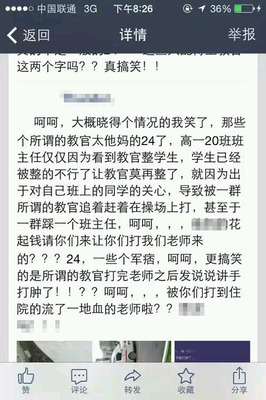宜黄县干部网上发文为强拆辩护,“没有强拆就没有崭新的中国”,言下之意,县政府的动机是良好的,符合广大民众的长远利益,仅仅因为方式方法不当,导致了自焚事件。表面上看,这是公权与私利的矛盾,政府要发展地方经济,推进城镇化,强拆强迁,原居民抗争无路,只得采取了自焚的极端手段。这位干部护主心切,但良好的动机并不是宽恕暴行的理由,况且动机未必就那么纯洁。在“天下为公”的旗号下,是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土地增值的巨大收益。充实地方财政是含蓄的说法,银两主要用于长官的政绩工程。直白一些的干脆赤膊上阵,贪污受贿,转眼便是千万富翁。这不是公权与私利的对抗,而是挟公权的私利与草芥私利的博弈,力量对比的悬殊,早就决定了博弈的胜负。败退者不仅承受利益的损失,亡灵还要遭到无耻文人的羞辱。“强拆是无奈的选择”,“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依傍胜利者讨得一杯羹,作践民权用的是秦始皇的逻辑。让我们回到两千年前,复原修建长城的公权与私利之辨。秦始皇因孟姜女哭倒长城,急召见大将蒙恬询问。蒙恬奏称:“臣奉旨督建长城,苦于经费不足,不得不强征民夫,令军校监押,昼夜施工。孟女之夫不堪劳役,倒毙于地,其体弱如此,非臣之过也。”秦始皇又问:“长城阻匈奴南下,黔首安居乐业。寡人为兆亿黎民计,孟女何悲之有?”蒙恬对曰:“百姓愚昧,不能体谅圣意,一人滋事,百人呼应,媒体亦推波助澜。”

|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56275 | 14虽是故事新编,对照今古,宜黄县政府的逻辑与秦始皇如出一辙。宜黄:强拆住户是为了推进城镇化;秦始皇:强征民夫修长城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宜黄: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在所难免;秦始皇:为建成统一大帝国,强征势在必行。宜黄:政府不能因为强拆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秦始皇:朕不能因为死了人就停建长城。不要以为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的错误仅在于方式方法。同样,宜黄县政府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补偿标准过低,或者强拆过于粗暴。实际上,他们有着完全相同的逻辑。所有帝王的逻辑起点都是“朕即国家”。“朕即国家”的现代版就是官员天然代表“公意”和“公益”,官员因此可以任意使用公器以维护“公益”。在现代社会中,公意只能来自于民众,在未得到民众的认可之前,任何人不得宣称自己代表公意,不得将自己的决定冠以公益的名号。无论能给民众带来多大的效益,没有民众的认可,长城和宜黄的城镇化就既非公意,亦非公益。在这个逻辑下,秦始皇无权启动长城的修建,因而也就无权强征民夫;宜黄政府无权决定城镇化的进程,因而也就无权强拆民房。现代社会中的公意是如何产生的呢?直接的方法是全体公民一致同意。因一致同意的协商成本过高,而且很难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公民制定规则和程序,在政府承诺严格遵守的前提下,委托政府提出公共工程的计划和预算,交公民或公民的代表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公民的代议机构即各级人代会的决策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似乎违反了少数人的意愿,但决策规则和程序本身经过全体公民的同意,因此而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威性。少数人必须接受规则和程序产生的结果,因为他们自己事先已同意按照这些规则和程序决策,他们可以表达对结果的不满,但不可拒不执行,更不能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多数人的决定。少数派只能在下一次决策时争取成为多数,或者动议修改对他们不利的规则和程序。公民社会的程序是繁琐的,费时又费事,决策效率低而且是有成本的。秦始皇的决策虽快速有效,但他的问题是成本更高。秦始皇的成本不仅体现在多少孟姜女失去丈夫,多少母亲失去儿子,而且超出民力、财力的“跨越式发展”激起了陈胜、吴广的大起义,连年战争,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两千年的循环,两千年不断重复的故事,除了主人公的变换,没有其他丝毫不同。同样的诉求,同样的手段,同样的逻辑,同样的结局。在以暴制暴的循环中,社会怎么可能进步?该打破这千年循环了。将皇帝和农夫转变为公民,公民个人权利至高无上,谁也没有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除此之外,似乎不存在第二条道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