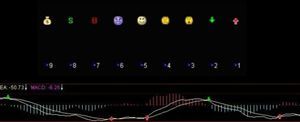村里叔叔十七岁当知青时的留影
①1966年至1976年,中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城市里的学生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也被叫作“下乡知青”,简称“知青”。
村里叔叔
2010年的暑假,北京热得要死,我哪儿也不想去。这当然是谎话,其实我很想出去,去山里、去海边……总之就是不想呆在家里。可是,一想到烤人的热气和比热气还可怕的人潮,我宁愿藏在家里的地下室看书,书的字里行间可以把我带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可以把我引入甜蜜的睡梦里。
那天,我在读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竟如饥似渴,走火入魔,这是少有的状态。说实话,在日本我没看过他的书,不是说只没有读过他的书,别人的书我也基本上没读过,只有在北京,在快要热死人的北京,才有这个机会。
她二十一岁,属羊的,比我大三岁,晚上在知青① 食堂吃饭的时候,她故意加塞,挤到了骨瘦如柴的我的前面,把剩下的唯一一盘炒土豆片拿走,于是我面前什么菜也没有了,端着空饭盒站在那里。她招呼说:“过来,一起吃吧。”我们蹲在地上,把炒土豆片放到了三块红砖叠 起来的“饭桌上”,谁也不言语。吃完饭,她站起来说: “你在西瓜地里干活罢?”我“嗯”了一声,她接着说: “明天中午拿个西瓜给我送来。”我没吱声。
她个子不高,身体很结实,家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城市,她家在城南,我家在城北。她是三个弟弟的姐姐,听说她中学(也许是小学吧)就不念书了,靠捡垃圾帮父母维持生计。父亲有病,长年卧床不起,母亲会一手针线活,给邻居和附近的工人缝补衣服。听说也有些人特意大老远地跑来让她补衣服,当然都是单身男人。她妈长得比她好看。我不明白她怎么也来当知青。
我们在地里干活,她看水泵,住在一个用破帆布和几个树枝搭起来的、被我们叫做“泵篷”的帐篷里。这份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帐篷里面呆着,清闲得很。这是别的知青得不到的闲差,她得到了。
不知道是谁惹怒了太阳,让他把眼球瞪的大大的,把风都吓得不知逃到哪儿去了。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就是一块蓝布挂在了望不到边的田地尽头。庄稼把大地染成了一块绿色的布,在绿布和蓝布相交的地方有一个像坟头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泵篷,是她呆的地方。
我光着上身,抱着西瓜,撩开了破帆布帘子。她正坐在一个下面垫了草、上面铺着军大衣的铺上剪指甲。
“拿西瓜来啦?”她说,我“嗯”了一声。还有三个月就十八岁的我除了“嗯”以外,好像什么也不会说。她把西瓜抢过去,放到了水坑里,“泡一会儿再吃。”她又坐下来剪指甲。
我俯视的视线正遇到她浅绿色衬衫里包着的乳房,她衬衫上面的两个扣子没系,也没穿内衣,上身就挂着这么一件薄薄的浅绿色的衬衫,下身穿着红黑格的大裤衩,好像是用什么旧床单改做的,又宽又大,裤腿里可以钻进去一只猫。
她抬起头,目光与我死盯着她乳沟的眼睛相遇,她并没有生气,笑了一下说:“看啥?没见过?”我僵硬地站在那里,身体被烧焦似的。她站了起来,贴近我说:“让你摸摸吧,傻小子。”她把我的手放到了她的胸上,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胆量,我一下子死命地抓住了它。她用力地把我推开了,“疼死了,小色鬼!”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她又笑了,把刚抬起来想系衣扣的手又放下了,说:“吃西瓜。”
我快速地从水坑里捞起西瓜,摔在地上,西瓜四分五裂。我抓起一块啃了几口就丢了,她也抓起一块吃了起来,西瓜水从她的嘴角流到了脸上、脖子上,沿着凹凸的胸往下淌着。
吃完西瓜,她看着我,笑着说:“看你裤裆都支起伞了。”她一只手伸到了我的两腿之间,一只手解开了 我的裤腰带,嘴贴在我耳边说:“来吧,姐姐让你成为 男人。”
第二天,我又抱着西瓜去了,以后又去了几次。
有一次我问她:“你怎么也来当知青?”她说:“快十六岁那年,有一个叔叔来找我妈补衣服,我说:‘妈妈去给爸爸买药了。’他就把我按到了炕上,我没反抗,从那以后他经常趁我妈不在的时候来补衣服。
以前这些人来我就出去捡垃圾,爸爸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脸一直对着墙,弟弟们去上学或在外面玩,爸妈各睡炕的两头,我挨着妈,三个弟弟挨着爸。我生出来不久爸爸就卧床不起了,三个弟弟谁也不像谁。后来,来找我的人多了,找我妈的人就少了。补衣服的人来了,夏天我妈就抱着衣服坐在屋外的板凳上补,冬天她就出去买药、买菜、买米什么的。
我打了三次胎,每次都是不同的叔叔用自行车把我驮到老远老远的乡下。每次我都感觉这次是死定了,可是,妈说,宁可让我死也不准生出来。
有一次在革委会当个小头目的叔叔和一个在派出所做事的叔叔几乎同时来了,为了我,他们打了起来,两个人从屋里打到屋外,打得头破血流,把妈吓坏了,把他们拉到屋里,脱光了身子求他们。我和妈同时躺在了一个炕上,当然,爸爸也在。第二天,妈妈就去知青点给我报了名,接着我就来到了这里。”
大概隔了一周我都没有去给她送西瓜,但我怎么也忘不掉西瓜的滋味。那天我又抱着西瓜去找她了,用手撩开了帆布帘子,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生产队长的傻儿子,正爬在姐姐的身上,屁股像捣蒜一样用着力。谁都知道队长的这个独生子有点“二”,三十多了还找不到媳妇,整天游手好闲,除了赶马车、卷烟叶子,剩下的就只会傻笑了。他的笑比别人哭还吓人,他一次可吃六个馒头,人长得又高又大,加上皮肤黑,大家背地里都叫他二骡子。听村里人说,叫他二骡子还有别的原因,他排行老二,他原来有个哥哥,在水坑里玩,淹死了。他经常撒完尿之后也不把老二塞进去,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走来走去,队长看见了就骂他:“把那玩意儿塞进去。”他就会傻笑着:“嘿嘿,刚才撒尿了忘了。”据说他那玩意和他的高大身躯还是很匹配,又长、又粗、又大,同骡子的差不多,有人说比骡子的还大,所以就叫他二骡子。城里的知青来了以后,他撒尿忘塞老二的事就更多了,尤其在女知青面前。
我看见二骡子的肩膀上一左一右长出两条腿,那是姐姐的腿。我逃走了,西瓜掉在了地上。因为偷西瓜,我被队里扣了三个月的工分,写了三次检查,在会上被批了三次,也从西瓜地里被调到黄豆地里去干活了。
在日本东京,有个地方叫上野,在东京的山手线上(注:东京的环城电车),日本人称它为艺术的上野。这个小丘上集聚着很多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当然,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唯一一所国立艺术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也在这里。用日本人的话说,东京大学是天下第一的大学,东京艺术大学,是云天之上的大学,可见这所大学在日本人眼里的地位。
我就在这里读的研究生。当然,对于上野而言,我在不在并不重要,老一代艺术家东山魅夷、平山郁夫、加山又造这三座大山在这里,新一代的村上隆、板本龙一都出身于此。从这里出去的人几乎个个都是名人,当然,我是例外。上野除了艺术以外,还有四个东西也很有名,用日语说叫上野的“四大名物”。
第一个是上野的樱花,每年春季,上野公园樱花盛开,来上野赏樱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抬头望去,上面看不到天,全是樱花。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在樱花树下抢一块空地比在北京的地铁里挤一个空座还难,他们搬来食品和各种各样的酒、饮料,把音响的声音开到最大,在樱花树下饮酒狂歌,手舞足蹈,尽情狂欢,那情景仿佛是世界毁灭之前的最后一次狂欢。
每年这个期间,报道上野的赏樱全民大狂欢也成了电视台的一个热点节目。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让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播音员去上野探访“樱欢族”(这名是我起的,在日本没人这么叫,也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没人这么叫)也成了一个惯例,这更成为电视台考验这些初来乍到的女播音员的一个环节。我的一个在电视台里当总监的前辈说,通过采访这些疯癫至极的人群,他们可以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机智与胆识。

当然这样的节目也给人们乏味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乐趣,记得那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女播音员(实习生)去采访上野的“樱欢族”,开始无论如何她也挤不进这“樱欢族”当中,根本没有人理她。后来她急中生智,拿出啤酒发给大家,人们拥了过来抢她的啤酒,这时她拿出麦克风对抢啤酒的人采访。还没等她开口,啤酒就被抢走了,她想去追抢走啤酒的人,有人从背后紧紧的抱住了她,两只手死死的抓住了她的乳房。她拼命地想挣|!---page split---|
脱,这时麦克风也被人抢去,冲着镜头唱起了日本民谣。她死命地挣脱,向人群的外环跑,因为跑得太急,她的长裙不知被什么东西挂住了,或者是有人故意暗中扯着,结果人跑出去了,可是裙子留下了。
中国送给日本的国宝熊猫“欢欢”就下榻在上野动物园,这“欢欢”自然而然地成了上野的“名物”之一。
第三个上野的“名物”是乌鸦。在上野路面上有很多鸽子,还专门有人卖喂鸽子的食物,年轻的情侣和带着孩子来的家长,买些食物放在手里引来成群的鸽子照相的情景到处可见。可是,乌鸦没人喂,数量也一样不少,就像长安街上的乌鸦一样,赶都赶不走,黑色的乌鸦也有 它们的生存之道,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它们个个吃得又肥又壮。
上野第四个“名物”就是流浪汉。到上野之前,就知道上野有很多流浪汉,我一直认为流浪和艺术总有点什么血缘关系,许多艺术家都是先流浪后成名,成名之后又去周游,说到底还是流浪。中国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八大山人”就是这样,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边走边画,风餐露宿,用画换取食物;扬州八怪之一的唐伯虎成了名还到处走,不仅爱美景还爱美人。看见秋香就走不动了。
在上野的流浪汉让我感到了许多不同的东西,首先,他们不向行人乞讨,决不骚扰你;二是他们很时尚,虽然住着用废纸盒箱搭起的住所,但其设计不仅有功能性,还有造型,甚至连纸板箱的色彩和文字露什么面都好像是设计过的,也许这纸板箱露的那个面都经过精心设计。流浪汉们穿着耐克的运动服,喝着啤酒,在避风、有阳光的一角,手里翻着最新出版的成人杂志。想想周围高楼大厦里的职员,只有中午放风时的一个小时才可以跑出来吸一口
含有大量汽车尾气的空气,找个楼缝晒一晒阳光,甚至还有很多人只能在办公桌上吃流水线上制作出来的盒饭。过去我下乡当知青的时候,顶着星星出,披着月亮回,这些城里人,早上被阳光逼进拥挤的车厢进城,晚上被路灯抽打进还是拥挤的车厢出城,在人生中属于上野流浪汉的阳光真不知比他们多多少倍。
一个流浪汉用手抓着寿司不慌不忙地吃着,他一点也不着急,因为,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
“非典”②把北京变成了一座空城,在平静的表层下隐藏着无比的恐慌和不安。静与安宁并不是一回事,古诗云:“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时人们都有一些厌城感,昔日对大都市的狂热恋曲在此时中断。当然,这只是暂停,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市是欲望的凝结体,是制造与消耗欲望的场,只要他活着,欲望就缠绕他的身心,除非欲望和死成了一条直线,像“非典”一样。只有当人们遇到死亡的时候,他们才会放弃所有的欲望,只剩下活下去这件事。可活下去又是为了什么呢?没空多想。
这是北京东南角某个村里的较为像模像样的饭店了,有着丰满身材的老板娘也就二十七八岁,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一个性情直爽的人。她两颗硕大乳房要从T恤中爆出来一样,摆来摆去,象胸前挂了两个西瓜,一个刚刚会走路的孩子坐在她怀里,撩开她的T恤一边嘬着乳头,一边用眼睛警觉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似乎在提示我,这个只能他吃,其他人谁也别想碰一下。老板娘也不站-爱华网-起来,更不理会裸露的大奶子展示在客人的面前,其实,店里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客人。② 2003年春,有一种叫“非典型性肺炎”(SARS)的病毒在中国传播,北京是当时的重灾区之一。
我说:“来一瓶冰的啤酒,一盘拌黄瓜,一盘清炒西兰花,一碗米饭。”老板娘说:“冰箱坏了,啤酒只有常温的,西兰花都烂了,你换个茄子、豆角什么的我们村里种的菜吧。”我换盘烧茄子,她朝挂了布帘子的后厨把我要的东西重复了一遍。
因为“非典”,大家都不愿意呆在城里,我也借着这阵风来到了北京东南角的这个村。其实,没有“非典”我也会逃城,虽然不知道那时我会给自己找个什么样的借口,但逃城肯定是会发生的。
“这村里有地卖吗?能盖房子的。”我问。
老板娘放下孩子,朝后厨又喊了一下:“孩子他爸,这个人要买地盖房子,咱把那个臭水沟卖给他吧?”
一个比她小了一圈的男人撩开布帘走了出来。不知道他那个东西是不是也小,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这个无聊的问题。
他说:“我家有块地,一亩左右吧,吃完我带你去看看。”
跟着他,我来到了北京东南角的这个村的东南角。一道要倒塌的院墙,破铁板门的上面用铁链围着,还上了一把锁,锈得已看不清门的油漆是什么颜色,也许根本就没涂过油漆。他没有开锁,只是把门推了一条缝,便和我穿了进去。这门纯是装饰品。里面到处是垃圾和野草,苍蝇和野猫为伴,在靠东侧有一条臭水沟,水沟旁是一个巨大的水坑。这里曾经养过鱼,现在里面已经没有鱼了,只剩下一米多深的水,发出一股恶臭的味道。
“行的话,我可以把坑里的水抽干,给你填平。”“用什么填呢?”“大部分是垃圾,上面盖点好土。”“这地我买了,但坑不填,把水抽干了就行了,剩下的事不用你管。”
我要了他的手机号,也要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他说:“以后都是村里人了,有啥事说一声就行。”
就这样,我又成了村里人。
光华路不宽也不长,在北京来说,这并不是一条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路。
光华路的西端连接日坛路,那里是北京最干净、最安静、最舒适的使馆区,东端连接西大望路,与建国路平行。在光华路与三环路交叉点的东南角,有一座大学,这是中国最著名的艺术设计大学。从国徽、国旗、建国初期的十大建筑,到毛主席纪念堂,甚至连纪念堂里的水晶棺的设计,都有这所学院的人参与。
1984年秋,北京依旧是灰濛濛的,在这所学校东南角的礼堂旁有一个小小的展厅,油漆桶盖、旧木板、废纸板、油毡纸、麻绳,这些建筑工地的垃圾被重新组合,拼贴挂在了墙上,还有被分割了的人头,手中拿着星球的背景……这些油画还真带来些立体派风格的味道,我就是这些作品的主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当时,如果我知道“波普艺术”,知道“立体派”、“毕加索”就好了。不过这些垃圾已给观者带来了不小的好奇和刺激。其实,我从小就画画,写实能力极强的,因为这个特长,我在文革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实惠。若不是我能画批林批孔的漫画,我偷西瓜的事说不定就不会只扣三个月的工分就完了,进“局子”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进去了,就没人能画漫画了,所以,我也就检讨了三次,事就过去了。当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给姐姐送西瓜。
因为这些垃圾艺术作品,有好心人找我谈话了:“还有一年你就毕业了,你应该把精力用在设计上,弄那些破垃圾,把人都画成四分五裂的,是啥意思啊?我建议你还是好好想想,别影响你的学业。”在好心人的暗示下,我人生的第一次画展提前关门了。不久,我就抱着解放全人类的想法去了日本。
1984年,在北京光华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展厅展出,具有立体派风格的油画作品同时还展出了用油漆桶盖等生活中的废弃品创作的作品。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来到曼哈顿码头,不是乘船,而是等待排队上飞机,从上空欣赏这个美国人用1美金买来的曼哈顿,这是我很早以前就有的愿望。
一辆黑色的超长林肯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位身材极好的金发美女和两位帅哥保镖。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明星就是某大家的千金,他们站到了我的后面。我们开始测量体重过安检。这种观光用的直升机只能一次载四位客人,于是我们四个就组成了一个临时观光团。
来到飞机的前面,驾驶员给我们讲解安全须知,我什么也没听懂,心里只想着我是否会和美女坐在一起。讲完一堆我听不懂的话之后,驾驶员指了指两位保镖帅哥,又指了一下后排座位,说了句“请”,这句我听明白了。然后驾驶员又指了指我、美女、他自己,指了指前排的座位,又说了一句“请”,这回我也明白了。就这样我和美女一起上天啦,天上人间啊!
到美国看当代艺术是我最重要的目的,一切都是为了它而来的。去画廊的路上,我的朋友对我说:“我刚到画廊打工的时候,做了一件很傻的事。那天画廊里来了一位有绅士风度的客人,估计有六十岁左右。他站在一幅画前看了很久,我心想,这可能是一个买主,主动热情服务一下。便走到他面前打招呼,给他讲画家叫什么名字,都做过什么,绅士点了点头。我看他有反应了,更来劲了,接着给他讲起他这幅画画的是他自己的梦……这时,这位绅
士愣愣地看了看我说:‘我眼睛好使,脑袋也正常,自己会思考!’说完就愤愤地走出了画廊。”我明白了朋友的话。艺术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用大卫.林奇的话说,“生命充满了抽象,我们唯一能理解的方法就是直觉——看见它,认知它。”艺术正是如此。
易拉罐是个便利的东西,用过了,踩扁了,也不占地方。现在的人们喜欢易拉罐,更喜欢易拉罐式的便利生活,一年换一个城市。一月换一个职场,一周建一层楼房,一夜换一个情人,易拉罐引发的一次性消费成了现代人的生活符号,一次性餐盒,一次性筷子,一次性内衣……人在无数个一次性中,消耗了只有一次性的人生。
我把喝空了的易拉罐踩扁了,粘到了小笼包的笼屉上,西洋快饮的包装物与中国式便餐的生产工具就这样相遇了。民以食为天嘛,吃喝便利了,接下来,其他便利性的行为自然就会出现。
买了地就要盖房子,盖什么样的房子呢?我没仔细的想过,但有一些明确的原则:一要实用,不要任何多余的装饰;二要结实,不能一地震给摇晃倒了;三要有趣、好玩;四要充满阳光,和自然的隔阂越小越好。当然,要自己设计自己建,这样既省钱,又好玩,还锻炼身体。
人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身不由已,能让自己尽兴玩一把的地方不多。家是仅存可以让你尽兴的地方之一,所以,一定不要像参加晚会挑外衣似的,尽想着别人看了会怎么样。“家是私物”,我对采访的记者说了这样的话,她让我写下来送给她们刊物,我照办了。
我喜欢看天,就有意识地把楼梯上的天井忘盖了楼板,改成只镶一块玻璃,白天看蓝天白云,夜里赏星揽月,二十四小时自然采光,不用点灯,省钱呵。
那天我推着小车在村里转悠,捡到了几个大鹅卵石,我想起了浮在海面上的一个个小岛,就把楼梯两侧的墙挖了个洞,把鹅卵石镶了进去,墙里一半,露出一半,楼梯扶手就是水平面飘浮的几个小岛。
“哎呀,你这墙凹凸有致的,好有肌理感,还有露出来的树枝、石头,真有感觉。”记者说道。
我心中暗笑,我砌的能平吗?有那技术我早不至于呆在村里,而是去工地上当瓦工了,说不定还能混个工头什么的。石头、树枝都是我推着小车捡来的,捡到什么就往墙里堆什么,能没感觉吗?我还从工地上拾来一块巨大的废混凝土块,放到家中的园子里,做镇宅之宝。那天外甥来了,看见了就说:“舅舅,人家院里都放太湖石什么的,您摆了这么一块工地上的大垃圾,太寒碜了。”
“太湖石盖的房子你能住吗?混凝土里都是最平凡的东西,碎石子、水泥、水它们凝聚起来了,比什么都结实,所以才能盖起高楼大厦,人生就是靠把平凡的小事一件件凝固起来的。”外甥没理我,心里估计在想:“明明就是葛朗台,还找什么理由。”
推着小车在村里捡别人不要的垃圾,既锻炼身体,减少了垃圾,又省了钱,真是一举多得。不仅如此,有时还有额外的收获。
村里有个安徽来的小伙子,开了个理发店,像我这样剃光头最省事,两三分钟搞定,一次五元,我每周都要去理一次。小伙子心地很善良,他对我说:“叔叔,你常推着小车捡那些石头瓦块的,多累呀(话外音就是生活不易呵,当然,生活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后我每次收你四块钱吧。”我当然不能推托,但是这四块钱的待遇我没能享受几次。在05、06年,中国电视老搞什么选秀活动,弄的人人参与,沸沸扬扬的,有一次还把我弄了去当
什么海选评委,这就出问题了。那天我又去理发,电视里正在播选秀的节目。我刚坐在椅子上,理发师的助手就喊了起来:“哎,这不是咱村里的这位叔叔吗?”理发师看了看电视,看了看我,一言未发。理完发,我赶紧拿出5块钱,交了走人。
出了门我还回头看看小伙子有没有拿着一块钱追出来,这次没有。村上春树在他的书中不仅写了他喜欢“性交”这个词,还提出了“冥交”这个词。我在想,“冥交”是什么
呢?是否就像是看着电脑上的色情图像“打手枪”那样的行为呢?那不是叫“意淫”吗?总之,就是指没有实物接触而产生某种满足感的行为吧。
对于“冥交”的解释,不知是否像我所说的这样,但是“冥想”这个词倒是以前经常听到过。大卫.林奇就很喜欢冥想。他说他每周要去一次瑜伽教室做冥想。大卫.林奇喜欢去瑜伽教室冥想,我喜欢在村里拉着小车一边转悠一边冥想。
在冥想中,大卫.林奇拍出了电影,
村上春树写出了小说,
我啥也没想明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