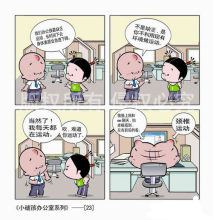高华教授走了,这些天来,我的心很是忧伤,一如一年前蔡定剑教授的离世。一说到高华,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宏篇巨制,它标志着一个历史学的时代。不过,我对于高华著作的解读,却因为这些年自己跋涉于宪法学,而不同于历史学的视域。在我看来,高华的著作以及他的思考,具有着独特的宪法学的蕴含,或者说,他的延安整风和毛主席的研究,对于我近年倡导的政治宪法学别有一番指导性的意义。
记得前不久我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会议,曾经与许纪霖教授谈到他们学校的几位中国现代史的教授,高华、杨奎松、沈志华他们殚精竭思所勾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立国之宪法,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国家总有自己的国家纲纪,不是宪法就是别的什么,它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中一言九鼎,势如破竹,不可抵挡。中国的宪法虽然可以写在纸上,中看不中用,但肯定还有另外一种实质上发挥强大作用的“宪法”。它们在哪里呢?高华他们的著作可以隐微地为我们提供一扇探其奥秘的门径。

独自漫步在香江边上,我曾经闪过一个念头,他日去南京,一定找高华好好聊聊,听听他对于我所解剖的中国宪法序言的看法,因为,中国宪法其实与毛主席思想有着一体性的关系,而这个思想的历史生成与高华的研究若合符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搞清楚延安整风运动,搞清楚高华的研究主题,也就对于中国宪法之政治性、阶级性、革命性、组织性有了历史的理解,对中国宪法本性有了真切的理解。我不知道高华对此有何高见,我很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历史学的评点。
然而,这个念头再也无法兑现了,我很悲伤。我知道高华的患病,也曾去过电话谈些我过去战胜疾病的经验什么的,但总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总会好的。此次高华的辞世,尤其是严搏非的一番陈词使我感到震撼。50年代的一帮人开始去世了,我们60年代的一帮人该如何呢?时间过得好快啊。
说起来,我是最近几年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历史的,尤其是现代中国历史,当然我说的现代指的是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现代史,我觉得马关条约以降,我们经历了三个半的中国,一个是晚清开始到1912年的中华民国,其中辛亥革命是转折性的标志;另外一个是1927年开始的中华民国,国共两个党制国家的斗争史,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与毛主席思想的崛起,决定了第三个中国的建国方略;此后,大陆中国作为主体,经历了“文化大革命”,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时期,而台湾地区,则经历了专制独裁、民主宪政,至今这两个政治体还没有“宪法”性联合起来。对于真实地理解现代中国,高华的著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这样说,不仅是指一般的历史学价值,而是从政治学、宪法学来说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革命建国的,革命的正当性来自哪里,来自中国革命史,来自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这里的灵魂就是党的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高华历史学的独创性,在我看来,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话语,用一个客观性的史家的卓越见识与缜密的实证材料,揭示了这个现代中国的生命密码。
作为一个宪法学者,我从高华的笔缝中,读到的不仅仅是过去多年的一段风雨如晦与金光闪闪的历史,而是宪法背后的那股魔力—一种塑造中国国家本性的那种力量。也许高华并没有宪法学的意识,但他有良史的洞察力和正视幽暗的勇气。都说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根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高华的著作似乎并没有简单地服膺于这套说教,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人民的个体之如何如何,而是一个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是如何升起来的。在此我想到马克斯?韦伯,他笔下的卡瑞斯玛,这也是一个国家得以立国的法统。但每个国家的卡瑞斯玛是不同的,现代中国的卡瑞斯玛,高华自然有着自己冷静的解读。
苏格拉底被雅典的民众判处死刑,因为他亵渎了雅典的神灵。这些天我翻读着高华的著作,不禁黯然伤神,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个老大的中国是否走出了自己的神灵世界。我们是否已经不需要一个救星了。对于现代中国公民来说,高华的著作无疑是一部宪法教科书,他启蒙我们走出神话世界,做一个自由担当的个体公民。要知道,现行宪法也是以保护公民权利、人民福祉为标尺的。但是,公民意识是要培育的,我感觉读历史,尤其是高华笔下的历史,毋宁是最好的公民培育书,是最好的建国叙事书,它使我们在当今浮华喧嚣的盛世之声中,领略到另外一种真实的面相。历史没有过去,也不会过去。
高华,现代中国的苏格拉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