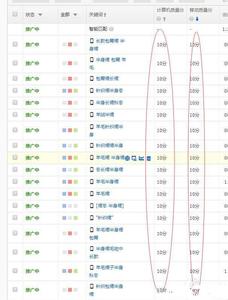转变增长方式与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后危机”期间的核心议题。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史显示,产业层面大的调整或我们所说的转型与升级,多半发生在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没有衰退的产业转型升级未有先例。无论是多产业联动的转型升级还是单个行业的技术升级,概莫能外。 美国最近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型升级,发生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主线是制造业扬弃了长期形成的传统产业,以全新的以IT产业为龙头的新兴产业取而代之。表面上看,此次产业转型升级似乎是与经济强劲增长同步发生的,实际不然。实际的演化轨迹是,产业转型升级是以一场旷日持久的“滞胀”为前奏的。1970年代的经济停滞与通胀并发症,逼出了政府经济政策与体制的大调整与“里根经济学”。 美国最近一次颇具启示意义的产业转型升级案例,要数汽车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了。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把美国这个传统制造业推入了灾难的深渊。2009年一季度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无一例外地负债累累,在破产的边缘挣扎,全球没几个分析家看好其前景的。 然而时隔两年之后的2011年一季度,这个行业却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起死回生”了。三大汽车制造商不仅利润空前地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技术与制造效率的同步跃升,2011年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所售汽车,70%以上属于创新产品! 历史何以如此展开?原因很简单,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硬的约束条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裸泳者”出局的市场竞争环境,迫使那些“裸泳”的低效率企业淘汰出局。迫使企业乃至整个产业去寻找新的增长点。 或许有人要说,先行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这些经验不适合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不是已经经历了无衰退的增长吗?但我要说的是,以往增长多半属于一种“无衰退的粗放”,目前的紧迫任务是实现从无衰退的粗放到“无衰退的集约”。 沿用经济学大师马歇尔的视点,把企业比作树木,把经济与产业比作森林,则30年前我们的“林地”上“树木”稀少,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栽树,现在,林地上已经栽满了树木,要保持林子的生机则需要砍树!问题在于,究竟是砍大树还是砍小树? 先行工业化国家将这种选择交给了市场,经济史明白无误地显示,这个时段两方面的因素在强化着市场竞争机制:一个是衰退。衰退——尤其是适度的经济衰退——加速着企业与行业优胜劣汰进程,迫使那些业已失去创新能力的低效率企业出局。另一个是政府政策。最有效的政府政策包括反垄断与非管制化。衰退与政府强化市场竞争的政策协力,将那些低效率企业推入困局,迫其重组甚至破产出局,而腾出资源给那些富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

自上一轮刺激政策实施以来,资源越来越多地在通过政府而非市场配置。更为严重的是,上一轮宏观政策对于传统体制内外两类企业的“非对称”刺激与“非对称”紧缩,多半强化了低效率企业,而将高效率企业置于“融资难”的困局之中。这种状态如若持续下去,势将难免滞胀厄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