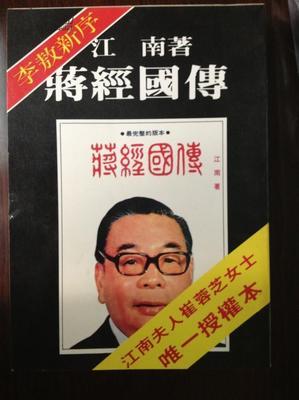我和米切尔——那位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独立软件公司的老板,第一次见面是在1984年,那次他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了我的办公室,并且问我人工智能和个人电脑的关系是什么。当时他问我这样的问题是很符合逻辑的,因为我5年前刚刚在该领域获得了博士学位。
1979年我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斯坦福大学不但在做事速度和风格上有着浓厚的乡村色彩,而且他们的基金好像总也用不完似的。后来在多年的研究和努力工作中,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就像进了天堂。那时几乎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只要你努力研究,偶尔写些报告,简直就像在做梦一样。在没有任何衡量成功的标准的客观条件下,那些电脑科技部门的教授就只能通过内讧和争学术头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在经历了一年半这样近乎毫无压力的日子后,我还是决定离开,因为对于28岁的我来说,“退休”实在是不太健康的一件事。
1981年是个只要是人就想要创业的年份,我当时很意外地被邀请加入了一家叫做Teknowledge的公司,那是一家由斯坦福教授一起创建的人工智能企业。他们做的是专家系统,就是一个将人类专家的知识编到电脑里,然后用来论证各种疑难杂症,比如说诊断难以发现的癌细胞的程序。

由于学术环境的影响,这些学者和研究专家总是无视个人电脑的快速发展,而喜欢那些庞大的,采用符号式计算的LISP机器。LISP机器特别费钱,这些基本上都是国家出钱制造,主要用于国家研究项目的电脑。LISP这种昂贵、高性能的机型和个人电脑比起来,就好像是F-15战斗机和塞斯纳150那样的私人小飞机一样。
两年之后,我发现同样的研究结果大可以在比它便宜许多的个人电脑上完成,于是我开始在空闲时间里用我新买的IBM电脑写程序。后来没过几个月,我就写出了好几个很不错还可以马上应用的程序。更巧的是,这刚好是米切尔来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们马上开始了合作,并且不断讨论如何设计一个可以管理个人资料的足够灵活的数据库——包括记录、想法、工作列表以及电话信息——而不只是企业的数据,好像账号和库存之类的东西。米切尔给了我一个顾问级别的合同,而我要做的,是与他和另一位名叫Ed Belove(爱德8226;比拉夫)的科学家一起将这些想法打造成产品。我当时在斯坦福西边的自己家中工作,然后偶尔去莲花公司在剑桥的办公室看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经常一个人工作和生活,陪伴在我身边的就只有我的猫“鞋套”,它是那个早已离我远去的同居女友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后来我发现总是一个人也不好,于是就卖了一些Teknowledge的股票,然后在旧金山那条弯曲的伦巴第街上买了套公寓。看到那些每天在门口经过的游客,我终于不再感到自己是住在野外了。高兴的不只我一个,就连我的猫也因为人多了而开心了不少。
那时我大概一个月会去一次波士顿。当时我、米切尔还有爱德,一直非常紧迫地为莲花公司的新项目奋斗着,而我们的努力后来也成就了一套叫做PIM(个人信息管理员)的程序。在那个程序接近尾声时,我们给它起了个正式的名字叫做莲花议事日程表(Lotus Agenda)。后来到1987年2月,我搭乘米切尔的新飞机回旧金山的途中,在飞机上向他展示了我们在产品问世前所增加的一些功能。
我们刚起飞,米切尔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东西,不一会儿,满地都是他的手提包、皮箱、各种电脑、手机、记事本、充电器、适配器、电线、电池、最新的业内周刊、电脑杂志以及报纸等。我当时在想这是不是就是米切尔需要私人飞机的原因——因为那些东西如果是通过商业客机托运,将是噩梦一场。后来当他坐在了成堆的电器中间时,他终于脱下了自己的滑雪夹克,露出了他典型的穿着:白底的夏威夷衬衫加上宽松的牛仔裤。米切尔是一个身高将近一米八三,走起路来活像个大男孩儿的人。在他深色的头发中,由于两鬓些许的灰色,却使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36岁稍老一些。还有他那两颗有点歪的门牙,再加上他勤奋而又热诚的态度,确实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土拨鼠。我当时从他的反应可以看出,那次比较突然的飞行着实让他感到有些紧张。
至于我,则是一个典型的小号米切尔,唯一不同的是,我比他瘦差不多20磅,而且头发天生就更灰一些。我也和他一样喜欢穿那些不太合身的时尚牛仔裤——那些为了猛男,而不是像我这样没身材的犹太人所设计的——只不过穿上后往往是肚子大屁股小。所以接下来不可避免的就是衬衫的边儿总是够不着腰带,导致经常会被人看到大肚子。和米切尔一样,我也一直在和体重较劲,但我们的风险不一样——他已经有老婆了,而我还是个王老五。
我们后来坐在了前面的两个位子上,然后米切尔半警告半嘲弄地对我说:“请将你的座椅调正,然后将你的安全带系在腹部下。”
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一直在模仿客机上的各种指示,还歇斯底里地狂笑,服务员肯定认为这些人是疯子,后来我们终于起飞了,飞机爬升的过程中我们都变得异常安静。看着地面离自己越来越远,我们的心中不禁冒出了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