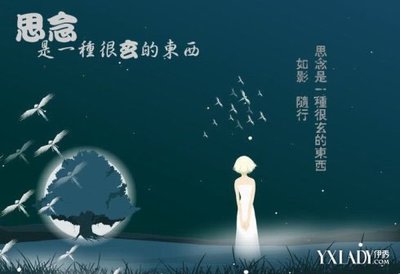第一章 草原恋歌 草原啊草原,我可爱的家乡。 马背啊马背,我成长的摇篮。 …… 多年之后,尽管往事已成追忆,但每当《草原恋歌》那曼妙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沈怡方的神情都会变得凝重,他沉醉而有些迷离的眼神告诉我们: 他,又在想“家”了。 内蒙古,那个被沈怡方称作“第二故乡”的地方,曾经留下他和夫人金佩璋的靓丽青春和蓬勃朝气,留下了他们一生当中最稚嫩的梦想和最充沛的活力,也留下了只有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才拥有的一腔热血与执着追求; 内蒙古,那个被沈怡方称作“第二故乡”的地方,曾经见证了两个上海毕业的大学生在祖国边陲曲折艰辛的奋斗历程,见证了两个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所遭遇的种种困惑、委屈与彷徨,更见证了两个白酒行业的“殉道者”如何在28年当中收获喜悦、硕果与成长。 内蒙,那个让沈怡方、金佩璋魂牵梦萦、终生眷顾的地方,他们的故事注定要从那里开始…… 远方的呼唤 1953年9月的一天,作为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第一届毕业生的沈怡方、金佩璋,正式接到通知,他们分配的去向是:绥远省归绥市。 翻开地图,家里人吓了一跳:这个平时很少被人关注的地方,竟然远在中国的最北端,与蒙古接壤。 这件事放在今天年轻人的眼中,无异于一片愁云惨雾、满目惆怅。而那时的沈怡方和金佩璋,却是欢歌笑语、轻松愉悦、充满了向往。 在那个满怀理想与激情的年代,到远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一代年轻人的最大渴求! 正是这份向往与渴求,让金佩璋这位出身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的大小姐,一口回绝了姐夫让她到自家工厂上班的要求,她的回答掷地有声:我才不要呢! 尽管当时父亲刚刚离世、母亲卧病在床,金佩璋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留在大上海。但是排行老九的她却坚持认为:我又不是大夫,留在家中何用?现在国家建设正需人才,国家困难是大困难,家庭困难是小困难,国家需要我,必须服从分配! 也正是同样的向往与渴求,让沈怡方这位出身苏杭贫困渔户、后被官宦人家收养、在上海长大的公子哥,毅然放弃家庭荫庇,义无返顾要去做一个凭借自己双手和智慧贡献国家、造福社会、开创未来的新一代有志青年。 沈怡方对自己的家人说:钱正英的报告讲得多么好,是劳动人民养活了我们,我们必须把知识文化还给劳动人民!离开大上海,脱离剥削家庭,我才能大有作为! “那个时候,我们全校毕业生很少有留在上海的,绝大部分人分到东北,我们最远,分到了绥远。当时心里没有一点不满,就想着一定要好好干,报效祖国,为国家建设出力!”——沈怡方说。 “虽然我的家庭出身是民族资产阶级,但我进步得非常早。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加入了人民解放革命青年先锋队,也就是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后来转成了共青团。所以,响应党的号召,献身国家建设,是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真诚渴望。”——金佩璋说。 少年不知愁滋味 他们是一路唱着歌到绥远的。 从未坐过那么远的火车,自上海出发,向西、向北、再向北,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祖国大好河山,兴奋之情无法抑制。 二天二夜过去了,在北京换乘了辆火车,城市的繁华被渐渐甩在身后,窗外的景象开始变得荒凉。然而,两颗年轻的心却依然热血澎湃,兴奋逐渐被强烈的责任感所替代:这里不正是梦中那片可以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吗?! 终于,广播告知火车已经到达归绥车站,两个年轻人再次欢呼雀跃:看那一片片的烟囱,这里竟有这么多工厂! “其实,当时绥远哪有什么像样的工厂?那些烟囱都是各个单位的取暖锅炉。远远望去鳞次栉比、好不壮观!”——沈怡方笑道。 归绥,呼和浩特市的前身,直到1954年绥远与内蒙合并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它才正式更名。 那时的归绥市,只有1万多人口,全市就一栋三层小楼和一座稍微像点样的联营百货商店,其它全是一水儿的土坯房。街道狭窄、黄土垫道。 沈怡方、金佩璋和来自其他院校的九个年轻人,是当时绥远省工商厅化验室分来的第一批大学生。化验室就设在一间砖木结构的平房里,跟宿舍紧挨在一起。白天在化验室工作,晚上大家就在旁边的土坯房里休息。 土坯房很小,进屋就是火炕,南方来的学生睡不惯,只好在上面搭块木板。他们要过的第一关,是适应当地气候。这里不光冬季气温降至零下30度,而且每年“一场风”,从入秋一直刮到第二年春天,白天刮起来飞沙走石,晚上停下来“风平浪静”,跟人们的作息时间“默契”配合,天天如是、从不爽约。 “当时我们11个大学生里有两对恋人,除了我跟沈怡方,另外还有一对。谁知两个月后,那对恋人吃不了苦,半夜开小差跑回内地去了,所以9个大学生中就剩下我一个女生。我来的时候下定决心要背叛家庭、改造思想,所以处处事事不甘落后。那时每家都有水缸,可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拿,铁锹握在手里总是转呀转。别人笑话我,越笑我就越是咬牙干。后来我这个上海大小姐,无论工作、学习甚至劳动都比别人强!”——金佩璋自豪地说。 他们要过的第二道关,是饮食习惯。当地以粗粮为主,70~80%是棒子面、大碴子、高粱面、高粱米、小米、莜面和荞面。上海人别说吃这些东西,过去连见也没见识过。仅有的细粮是馒头、面条,偶尔赶上一点碎米便如获“至宝”。南方吃惯了大米的人,这道坎儿着实难过。而且,当地还奇缺蔬菜。土豆、胡萝卜、圆白菜“老三样”,每年8~9月份开始储存,一直要吃到第二年5月冻土开化…… “我这个人吃不惯牛羊肉,别人问为什么,我常开玩笑:在内蒙吃多了。其实那会儿内蒙哪有牛羊肉吃啊?一家人一月两斤猪肉,只有回民才配给牛羊肉。粗粮刚开始我也吃不下,但吃不下也得吃。记得我第一次下酒厂与工人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都是粗粮,莜面上锅蒸了当主食,又黑又糙,吃了就往上翻,真的是吃一口吐一口,还不敢当着别人面吐。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生活可以改变人。如果那会儿真能吃上牛羊肉,我想今天我吃肉的习惯也会改变。”——沈怡方笑言。 两关过后,还有第三关,那就是自己烧炕取暖。劈劈柴、买煤块、升炉子,这些在大上海从没干过的活,到那儿第一年他们就被“逼”会了。 1953年春节,在领导的张罗下,沈怡方和金佩璋举办了简朴的婚礼。自己买了10块钱喜糖,同事们送了一块玻璃台板、一面花镜子,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两个铺盖卷往炕上一并,他们就算完婚了。沈怡方清楚地记得,那间单位分给的新房只有几平米大,进门就是炕,炕边上摆个小桌子,然后什么也没有了,有也摆不下了。 曾有人问:为什么刚到那儿半年就结婚?金佩璋说,那时候能来几个大学生不容易,生怕吃不了苦再跑掉,所以厅里的一位领导比我们还着急,一个劲儿催着把婚礼办了,成了家也就扎根了。多年后那位领导还总是跟我开玩笑:是我把你包办了。 “绥远的生活水平,与奢华、优越的大上海有着天大落差。但是觉得它苦,却是今天回过头来才有的感觉。那时候再难也不觉得苦,而且还有种‘苦中作乐’的享受。”——金佩璋说。 “那是我们那代年轻人自己想要的生活,放弃奢糜享乐、在艰苦生活中锤炼自我、将青春奉献给祖国的边疆建设,这不是唱高调,是我们自觉自愿的渴望和追求。”——沈怡方说。 在挫折中成长 到绥远后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在实验室里搞化验。 这对于心高气盛的沈怡方和他的伙伴们而言,无异于大材小用。他们心里抱怨:我们是大学生,千里迢迢到这儿来不是为当化验员的,我们能有更大作为。 化验室的头儿,是一位国民党时期留下的老技师,姓王,人挺随和。他看出这帮孩子们不满,却什么也不说,每天把外单位送检的样品,布置给他们去检验。这边几位大学生查书的查书、商量的商量,只管自顾自做起来。化验完了,王技师看看报告,从来不说对与错。 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沈怡方他们心中有点打鼓。果然,一天单位里几位领导一起找他们谈话,这才知道原来两个多月统统白干,化验结果都是错误的。临走时,领导们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你们这些大学生啊,这样下去可不行! “实际上我们这些大学生,在学校里搞实验吹吹玻璃泡、看着水红红绿绿一变就完了,都是纸上谈兵。进入工作后,临时翻书‘抱佛脚’,没有一点实际经验,实验结果怎么会准确呢?这件事让我明白个道理:大学生初出校门,最重要的一条是放下架子,老老实实从头学起、虚心求教,否则很可能一事无成。”——沈怡方说。 在大学里,沈怡方学的专业是有机合成,选科是硅酸盐。然而到绥远才知道,这里根本没有化工产业可言,只有白酒在当地还算是重要的工业,所以酒注定了要改变他的人生。而沈怡方与白酒第一次结缘,则是在1953年的11月。 当时地方工业部华北局召开华北地区白酒生产技术交流会,绥远工商厅决定选派一位大学生前去参会,沈怡方由此参加了他白酒生涯中的第一个行业会议。 技术交流会在河北衡水老白干酒厂举行。第一次出差、第一次接触衡水老白干酒,沈怡方兴奋不已,扛着一大包行李来到酒厂,里面装着冬天的被褥和衣服。酒厂提供了一个大屋子,里面一溜大通炕,参会代表们把各自的行李往炕上一摊,密密麻麻住了下来。 由于从未接触过白酒工艺,技师们在交流会上的讲课他基本听不懂,参观车间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沈怡方有个笨办法:人家讲什么他记什么,一句不漏。 回到绥远,沈怡方根据整理好的记录向厅长作详尽汇报。望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厅长大喜: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而且不懂这个专业,居然能讲得头头是道,着实难得!他当即决定,让沈怡方在每周一次的全厅干部业务学习会上给大家讲讲白酒! 任务接受下来,沈怡方心里七上八下。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行业,要给全厅干部讲课,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情急之下,他赶紧四处找书翻资料。谁知当时有关白酒的教科书根本没有,最后还是在陈騊声的《酿造学》里发现了一点有关高粱酒的介绍,还没来得及彻底搞明白,就仓促上阵了。结果可想而知,当他讲到白酒“老五甑”工艺、混蒸配料过程中粮食进去后酒糟如何出来时,一下子卡壳了。见沈怡方憋了个大红脸,厅长赶紧解围:不要紧,不要紧,小伙子年轻,以后好好学,这段儿下回再给我们讲吧! “尽管领导再三鼓励,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铭记。我知道自己差得实在很远。”——沈怡方说。 1954年,绥远省与内蒙古合并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原绥远省工商厅更名为内蒙古工业厅,所属化验室升格为工业实验所。

1955年,工业实验所增设食品研究室,做了一年半“化验员”的沈怡方,被任命为食品研究室负责人,他的任务是主抓白酒。 沈怡方开始与酒正式结缘。而进入白酒行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研究和推广麸曲法白酒。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保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粮食匮乏。而传统工艺酿造的大曲纯粮白酒,在出酒率比较低的50年代,被视为食品行业中的“耗粮大户”。因此,节约粮食、降低粮耗,是那个时代白酒行业生存与发展亟待和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 1955年,“烟台操作法”在白酒行业树起了“丰碑”,其精神实质“低温发酵,定温蒸烧,黄曲加酵母”成为后来整个白酒行业酿造与生产的规范。而其核心内涵,便是通过推广麸曲法酿酒解决白酒耗粮问题。 实际上,烟台试点及其操作法是对麸曲酿酒经验的总结和集大成。早在“试点”之前,北方许多省区即已开始对这一工艺进行探索,其中就包括沈怡方他们在呼和浩特酒厂进行的一系列富有成效的试验。 在探索麸曲酿酒和推广烟台操作法的过程中,有两件事让沈怡方颇有成就感: 第一件事,是内蒙化验训练班的开办。麸曲酿酒和烟台操作法给行业带来的一个巨变,是白酒第一次开始用分析化验方法指导生产。为此,他们在工业实验所里首次举办了一个白酒化验训练班,学员均来自全自治区各大重点酿酒企业的一线工人。这些学员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勤奋好学的精神让人深受感动。这个培训班,为日后在全区酿酒企业中普及麸曲酿酒工艺播下了人才和技术种子; 第二件事,率先组建起全国第一家白酒曲种站。与传统大曲酿酒方法不同,麸曲酿酒和烟台操作法的独到之处及其“技术要点”在于:把过去完全依靠自然培养的微生物——大曲,改为人工选育的优良菌种——黄曲霉和酵母菌。然后将这两种纯人工培养的菌种制成麸曲,应用于发酵生产。因黄曲糖化力很高,酒精酵母的发酵力也高,这样便可极大提高出酒率。但是,由于当时各地酒厂生产条件普遍较差,这两个菌种在人工扩大培养过程中极易被污染,酒的产量难以保证。于是,在沈怡方主持下,全国第一家专业培养黄曲霉和酵母菌的曲种站在内蒙古率先落成,定期向全区白酒企业免费发送人工培养的优良菌种。 内蒙曲种站的组建,为全自治区乃至北方地区推广麸曲酿酒和烟台操作法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与后来贵州轻工研究所组建的根酶曲菌种站并称为南北两大曲种站,自1955年组建以来历经50余年,时至今日仍在为生产企业服务…… 在工业实验所里,金佩璋日常负责检测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即便如此,她跟酒还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最早接触白酒,始于她对酿酒原料的检测。 酿酒原料的淀粉分析,是酒行业用来检查原料质量和计算淀粉出酒率的一项必备工作。而分析粮食原料中的淀粉含量,通常采用酸水解法。但是随着麸曲酿酒工艺的推广,各酒厂开始大量采用非粮食原料酿酒,特别是麸皮使用酸水解法检测,因其中大量半纤维素被水解,造成检测结果往往偏高一倍左右,因此不再适用。 为解决这一行业难题,金佩璋和她的伙伴们进行了大量探索性实验。一开始,她们改用酶水解法进行测定,之后又尝试用黄曲霉浸出液加以替代,但均不理想。酶水解法,也就是用纯淀粉酶法测定麸皮中的淀粉含量,测试结果为19~23%之间;而用黄曲霉浸出液即曲酶法替代,测出的结果则在27~31%之间。也就是说,对于麸皮样品的测定,曲酶法的结果往往比纯淀粉酶法高出30~40%。 实验证明,曲酶法确实适用于一般非粮食原料的测定,但对于麸皮的检测,结果偏高太多,只能弃用;纯淀粉酶法显然是各种植物原料淀粉测定中最标准的一个方法,也是测定麸皮淀粉含量的有效方法。 不过,普及应用这种检测方法的最大障碍,是当时纯淀粉酶多系进口试剂,在市面上难以买到,所以无法推广。 金佩璋认为,必须找到一种能够适应各地酒厂生产控制分析要求、对麸皮淀粉近似值可以快速测定的方法,以满足行业生产的迫切需要。 为此,她饭吃不香、觉睡不着,夜以继日地和同事们一次又一次实验,苦苦寻找着各种解决方案。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科学而大胆的方法最终在她的不懈努力下被找到了。 这个方法的基本要点,是先将麸皮样品浸泡在热水中加以糊化。由于麸皮中的淀粉在糊化过程中绝大部分能够溶解抽出,而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均不能溶于热水,所以在糊化当中趁热过滤,就能使麸皮中的淀粉基本全部抽出,滤液再经酸分解,淀粉含量就能比较准确地测定出来。 金佩璋很快将这个方法在业内刊物上公开发表。别看它并不复杂,但在麸皮淀粉的测定中却既实用又有效,在当时整个行业迫切需要解决生产难题、提高检测水平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为响应轻工业部进一步降低酿酒耗粮、开发野生资源代用品作酿酒原料的号召,沈怡方被派到内蒙东部地区的乌兰浩特酒厂展开实验,探索试用野生橡子果酿酒新工艺。 那些日子,每天一早他和厂里的工人们赶上马车,到林区去收购橡子。回来后,晒干粉碎、调整工艺、热火朝天地试酿橡子酒,忙得不亦乐乎。 之前,沈怡方和金佩璋刚刚被评定为9级工程师,月薪101元。两个24岁的年轻人,毕业不过几年,就有了如此高的职称和待遇,心气儿自然不低。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让沈怡方颇丢面子,也让这位年轻工程师一下子头脑冷静了下来。 那是在试验橡子酒时,乌兰浩特酒厂的曲子(麸曲)在扩大培养过程中出了问题,一房接着一房酸败。麸曲一旦酸败就再不能使用,整个酒厂面临停产。厂长、书记找到沈怡方说:正好你这个大工程师在,快帮我们找找原因吧。 除了在所里做原种比较内行,那时候沈怡方工艺实践上其实也没啥经验,于是赶紧回去翻资料。书上说,曲子的水分不能小,一般应在52%以上,水分越大糖化率越高。酒厂当时的曲子水分是48~49%,因此沈怡方提出:水分应当加大。谁知水分越大,曲子酸败得越厉害,一坏就是几千斤麸皮的损失。原因找不到,酒厂面临停产,望着厂长、书记信赖而又焦虑的目光,沈怡方心急如焚。 在此之前,一位工人出身的老技师曾经提出:麸曲的培养,水分不能大,应该减少到45%左右。当时厂领导比较迷信大学生工程师,其意见未被采纳。此时一筹莫展,只好回过头来再试试老技师的办法,把水分从49%降到46%。结果一试即成,曲子再也不酸败了。 “这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教训,让我终生难忘。它让我真正懂得:书本理论必须跟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自己的‘学问’。‘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沈怡方说。 让我们相互感动 挫折是成长的动力,失败是成功之母。 沈怡方曾经深有感慨地说:我搞了几十年白酒科研,体会最深刻的一点是:出点儿错并不可怕,失败也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善于在错误和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最终获得成功。一个人如果总不出错、不失败,也很危险。 乌兰浩特酒厂的挫折,让沈怡方冷静和成熟了许多。他跟企业和工人们在一起的感觉不一样了,知识分子的架子渐渐放了下来。 搞白酒少不了下酒厂,解决技术问题必须深入一线。在酒厂,他什么活儿都干过。 跟工人们一起打过铲、踩过曲,起过糟、上过甑,什么脏活儿、累活儿他都干。 那个年代,制曲是一件苦差事。大冬天外面零下30几度,一进曲房,里面高温高湿,衣服都穿不住,只能赤身裸体。曲子翻完后,大棉袄一披,赶紧出来烤火,两个小时曲子再升温,又要进去翻,就这么一干48小时,沈怡方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有个酒厂的食堂,前面是食堂,后面是猪圈,好不容易吃顿馒头,上面落满苍蝇,白馒头变成了黑馒头。吃的时候,工人们用手赶一赶,吃得很香。沈怡方也用手赶一赶,同样吃得很香。 跟工人们打成一片,工人们也就把沈怡方当成了朋友。他们说,这个大学生好,一点架子没有。这样的工程师,我们欢迎。再后来,赶上重活儿、累活儿,他们总是拦着沈怡方,不让他干。 在酒厂跟工人们同吃同住睡大炕,回到家毛衣毛裤、棉衣里面到处爬满虱子。每次回家,金佩璋都让沈怡方先把衣服统统脱在门外,进屋时只穿着裤头。因为虱子生命力极强,即便零下几十度将它冻得通红,一进屋仍然能活过来。毛衣毛裤不能总拿开水烫,金佩璋就把衣服全部撒上六六粉,在外面一直捂到虱子被杀死,再拿回来洗。 1959年,沈怡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上海滩上的公子哥到小知识分子再到一名共产党员,沈怡方从内到外确实在发生变化。 其实,发生变化的何止沈怡方一个人,他的爱人金佩璋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同样脱胎换骨。从一个上海大小姐到研究所的主力工程师再到一位称职而坚强的家庭主妇,她的角色转换,让每一个了解她的人为之感叹。 金佩璋生第一个孩子时,是在距预产期还有四天的时候才离开内蒙、返回上海的。从内蒙到上海,一路上要走三天时间,中途还要在北京倒车,她一个人挺着大肚子、拿着行李倒来倒去,随时要下厂的沈怡方根本不可能陪她;她的第二个孩子是在内蒙出生的,中午11点多,宝贝女儿几经波折终于降生。从产房出来,金佩璋既饥渴又疲惫,她让护士把早晨送来的冷饭在暖气上靠靠,西里呼噜就吞下去了,一旁的护士看得直摇头。 “出院那天,正赶上沈怡方下厂不能来接我。那时候好像也挺能理解,不能来就不来吧。分析室里叫上个小姑娘、雇上个马车,就回到家了。”——忆起那段往事,金佩璋的话语轻松依旧。 回到家里,正是寒冬腊月,宿舍楼刚刚盖好,暖气还未接通。把婴儿包裹打开来看看,尿湿了,脐带还没完全脱落,跟尿布粘在一起。吓得金佩璋赶紧把孩子湿着又包起来,等着邻居前来帮忙。下班后回来的沈怡方满脸抱歉,说太可怜了,先张罗着把炉子装上。那时单位刚给他们分了间北房,炉子装好了,可是北风一吹,煤烟全部倒进了屋里。没法子,只好又向单位申请,搬到另外一间南向的土坯房里,好歹可以升炉子取暖了。可是又没水,烧水做饭都要自己去挑。 “屋漏偏逢连天雨”。出院后没几天,金佩章又患上了乳腺炎,疼痛难忍,必须每天去医院治疗。医院离家好几里地,公交车一小时才一班,实在等不了,她就用棉大衣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起来,每天步行往返……连医生都不忍了,说带上婴儿住院吧,可她舍不得把孩子送回医院,就这样走着走着,直到乳腺出脓、治愈。 有付出终会有回报。曾经一上街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这两个是上海人,曾经一个只会讲上海话而每次开会发言都要靠另一个人做翻译的两个年轻人,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从最初的格格不入到入乡随俗、再到后来在那里成家立业、生根开花,他们真诚的付出换来了很多人的由衷认可和感动,赢得了周围领导、同事、朋友和众多酒企员工们的赞许、关爱与支持。而这一切,对沈怡方和金佩璋来讲,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支撑。 “我们永远忘不了,三年困难时期,在大家都吃不饱饭的时候,有那么一位酒厂的老工人,竟然把自己的口粮节省下来,悄悄给我寄了60斤粮票。那时候粮票何等珍贵!不过,比这更珍贵的,是那位老工人对我们年轻知识分子质朴的关爱!这件事让我们感动了一辈子!”——沈怡方动情地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