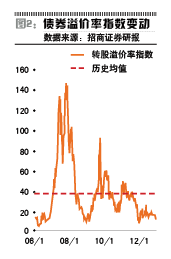在我国实践中,绝大多数股份有限公司(含上市公司)的股份过于单一,仅限于典型化的普通股。而其他类型的股份,如优先股等并不常见。其实,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未禁止优先股制度。相反,该法第132条设立了一项授权性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另行作出规定”。因此,国务院可以通过出台行政法规推出优先股等种类股份制度。
春江水暖鸭先知。孕育于市场经济的优先股制度对于满足特定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协调不同种类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财产利益上处于优先地位的优先股东要舍弃一些控制权,在控制权上获得优势地位的普通股东要舍弃一些财产上优先分配的利益。各类股东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这也是种类股份尤其是优先股制度在美国等其他资本市场大国普遍运用的主因之一。
实际上,我国法学界已经注意到优先股制度的重要性。去年夏天,中国法学会委托我从事一项省部级课题《股份公司类别股份制度研究》的研究工作。这里的“类别股份”指典型的普通股以外的其他各种股份形式,包括黄金股和优先股等。
笔者认为,优先股(特指优先分红而无表决权的,狭义上的 “优先股”)可用于解决两方面的重大现实问题:一是国有股的进一步改革问题;二是VIE(协议控制)模式,即我国互联网公司境外上市过程中外国投资者的身份问题。
国有股一股独大根治良方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很难在短期内扭转,即便股权分置改革结束,股权结构过于集中的问题也并未根本解决,且近几年之内都难以根本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国有股转成优先股,既可以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有利于广大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同时还能减轻国家股东的负担,可谓“一步好棋,全盘皆活。”
优先股本身是良药,但有人提出让中小股东持有优先股以解决分红问题。我认为这等于开对了药方,却找错了吃药的人。如果让中小股东持有优先股,而国家股东依然掌握着股东大会的控制权,还是做出不分红的股东大会决议,那么中小股东还是只能嗷嗷待哺、无计可施。所以,建议把表决权还给中小股东,而把优先分红的利益给国家股东。
我在1993年就撰文建议,把国有股改成无表决权,但在分取股息红利、剩余资产及其他财产利益方面享有优先权,而且是可累计的优先股——股息可以历年累积发放,例如第一年没分红,可以转到第二年。
首先,把国有股界定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以后,中小股东获得了更多的表决权和控制力。他们将更热衷于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投票,积极监督上市公司。现在国有股东是由国资委代表的,但国资委哪有精力监管那么多上市公司,那么多高管?
其次,把国有股界定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既减轻了国家股东的负担,又能缓解内部人控制的问题。目前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独立董事的人选,都是大股东在控制。如果国资委、国有企业总公司持有优先股,就是把包括董事监事任免在内的公司决策权交给了公众股东,解决了选择代理人、监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等一系列难题,减少了利益博弈,又换取了实际利益。同时,优先股并不剥夺除表决权之外的其他权力,国家股东依然可以参加股东大会,还享有质询权、知情权、监督权、提案权、诉讼权等;并不是说国家股东就无所作为了。
第三,把国有股界定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以后,有助于解决我国国有控股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遭遇的身份尴尬。例如,陕西的一家冶金投资公司西色国际在2009年收购美国优金公司时曾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出于国家安全审查的刁难。部分原因就是西色国际被看成是陕西省政府控制的企业,威胁其国家安全。一旦国有股东没有表决权,外国人还能说是政府控制的吗?所以国有股转优先股,可以消除国际上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误会。
VIE法律难题治本之策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公司(如网易、百度、新浪等)赴境外上市的过程中频繁采用VIE模式, 即“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变利益实体”,也称“协议控制实体”,为企业所拥有的实际或潜在的经济来源,但是企业本身对此利益实体并无直接、完整的控股权。
其基本架构就是首先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建立一家私人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东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两个人以上。在BVI设立公司以后,BVI公司又在开曼群岛设一家全资子公司。这家子公司再到香港设立一个全资孙公司,然后经由香港再到国内设立一个100%的、第四级的曾孙公司。但是,第四个层面是依据外商投资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法设立的,从性质上看是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独资企业,其实具有中国企业法人的地位。

由于我国对互联网产业高度敏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不允许外资企业进入,外商独资的也不可以。如何绕开法律规定进入到第四个层面,成为摆在这些企业面前的难题。于是,在国内从事实体经营的真正实体企业(VIE)都是内资公司,但是内资公司的股东也往往是境外公司的发起人。他们在国内设置第四个层面的外商独资企业遂与内资企业或VIE的股东缔结一揽子协议,包括但不限于融资协议、技术支持协议和控制权协议等。其目的是使外商投资企业在第四个层面上与国内的实体公司牢牢地被契约捆绑起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法律不允许外资企业通过股权形式控制境内实体公司,他们只能通过这种契约协议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控股。
长期以来,监管层对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去年以来收紧了,其主要标志是商务部于2011年8月发布的《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而我国互联网企业在成长初期,往往财务业绩不佳,还处于“烧钱”阶段,而境内股市不愿意让其融资。于是,这些公司被迫去境外融资。
因此我建议对外资开放互联网产业,但把境外投资者对互联网企业持有的股权限定为无表决权的优先股。如此一来,外国投资者可以进来投资并取得投资回报,只是没有表决权而已。这样我国互联网企业既可使用外国投资者的资本,又排除了外国投资者的控制权,确保我国的互联网领域的国家安全。当然,互联网公司要努力确保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以实现各方利益多元共享的和谐局面。
从立法进程上讲,虽然推出种类股份制度并未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的近期立法规划项目,但是相关研究必须抓紧。就解决当前最为棘手的国有股权进一步改革和VIE模式的瓶颈问题而言,无表决权的优先股应当成为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面前的首选法律方案。
(该文是教育部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公司法现代化研究》、2008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弘扬股权文化,完善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与中国法学会省部级课题《股份公司类别股份制度研究》CLS(2011)C19的部分研究成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