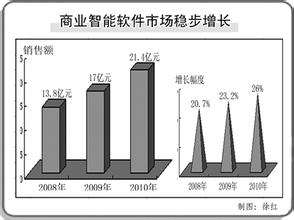日前,《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认为“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并且提醒“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这种论调,其实就是“腐败容忍论”。 事实上,此种论调了无新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容忍腐败不但是长期存在的事实,而且也往往有动人的说辞。今天,执政党虽然声言决不允许腐败行为存在,但是腐败案件涉及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纪录不断被刷新,不但说明反腐败确实有难度,而且也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腐败在某些层面,可能有相当的共识。《环球时报》不过戳破了这层窗户纸而已。 容许腐败,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从皇帝来说 ,容忍腐败往往是向官僚集团购买忠诚的明智选择。相反,反腐败则很可能使官僚集团失去忠诚度。在获得官员的忠诚与保持官员的廉洁之间,统治者经过权衡,往往为了获得忠诚而牺牲掉对官员廉洁度的要求。《资治通鉴》记载说,针对满朝文武贪污腐化成风的现实,有人建议东魏实际统治者高欢严加惩治。高欢便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当时萧衍在南,宇文泰在西,都是东魏的巨大威胁,若打击贪污,“我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皆归黑獭(宇文泰),士子悉奔萧衍”。而高欢所说的南方萧衍,居然也有与高欢不谋而合的看法,也极力放纵贪污腐化。萧衍是南朝梁朝的开国皇帝,其弟萧宏既贪婪又无能。因为他屋后有百间仓库,有人便告发他私藏武器,准备谋反夺权。萧衍听说大惊,乘机前去查看探访。探访发现,原来藏的不是什么武器,而是聚敛来的无数财物。这明显是贪污聚敛所得,但作为皇帝的萧衍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大加称赞:“阿六,汝生计大可。”此后这个萧宏更是“夺民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 高欢和萧衍,其说法和做法,体现出历代统治者同样的选择:为了得到政治忠诚,皇帝放松对于官员的廉洁的要求。毕竟与政治忠诚相比,腐败行为对王朝的威胁是间接的,其直接承受着也是广大的老百姓而不是统治者自身;而势力强大的官僚阶层的离心离德,则直接威胁统治者的江山社稷。两害相权取其轻,皇帝虽然知道官僚贵族的腐败是危险的,但也采取宽纵和容忍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常态,这恐怕也是今天“腐败容忍论”者的难言之隐。 统治者除了主观上用允许、宽纵腐败来换取官僚集团的忠诚外,在中国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下,从客观上看,反腐败的难度确实是非常的大。因此,一些皇帝也知难而退,不想在反腐败问题上自找苦吃。所以,历史上严刑峻法反腐败的皇帝,也不过明朝的朱元璋和清朝的雍正这样不多的几位。其他的皇帝大多对于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是容忍放纵,睁只眼闭只眼,轻易不予处理。

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天然地带有腐败的基因,而且天然地无法消除腐败。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下,上下之间信息不对称,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扭曲,因而存在监督困境。这种制度下,政府分成很多层级,每一级都向上一级负责,每一级又都负有监督下一级的责任。但事实上,由于地域、交通、信息传播等等的限制,每一级都掌握着上级所根本无法弄清楚,也无力弄清楚的独特信息。利用信息不对称,被监督的官员就会弄虚作假,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对于这种腐败行为,深受其害的地方老百姓要么根本不知情,要么即使知情,但因为皇权制度下老百姓并无监督权,质疑权,所以不能对于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任何监督制约。这样形成的后果是,官僚机构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那里。皇帝虽然有时也模模糊糊知道下面弄虚作假,但无可奈何,只有选择宽容的政策以羁縻笼络之。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清朝皇帝对于地方官员普遍榨取陋规的腐败现象的态度:虽然皇帝也大概知道各地官员通过陋规大量榨取民脂民膏,但是皇帝无力处理整个官僚系统,只好默许非法榨取行为,最后甚至将非法榨取行为合法化了事。 在君主专制的皇权社会下,腐败行为是其政治癌症,是无法克服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就像《环球时报》所说,在任何社会制度下,腐败都是不可能克服的。腐败的根源在于专制制度下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监督困难,也源于皇权制度下皇帝向官僚集团换取忠诚的需要。所以,结束腐败的最好方式,当然在结束这种政治制度,克服因为信息不公开因而信息不对称对委托代理关系的扭曲,让作为权力委托者的人民充分知情,让人民充分行使监督权问责权。只要由作为委托者的人民而不仅仅是由上级政府来监督政府和官员的制度建立起来,反腐败将不再困难,宽容腐败也就没有任何理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