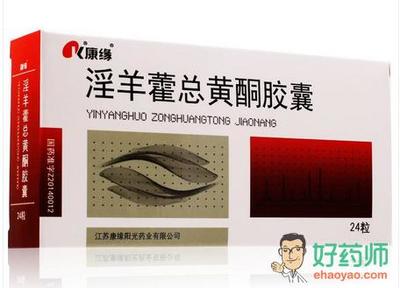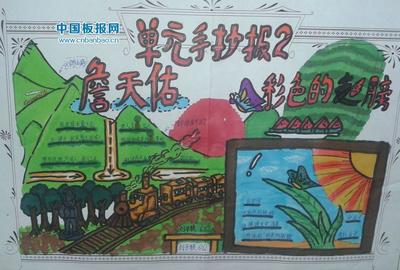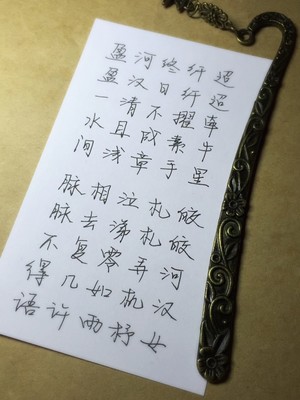小时候睡过榻榻米,但不是铺在地上,而是当了床垫子。那是在长春,光复也好多年了;如今年轻人,不论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不大知道长春还叫过新京,曾是伪满洲国的京城,日本人的乐土。不过,那垫子就是榻榻米,却是在年将不惑东渡,住进日式房间,一股子霉味儿呛鼻,才恍然大悟的。 铺满榻榻米,进屋即“上床”,大概可算是日式房屋的第一元素。起初榻榻米并不是铺满房间,如京都御所清凉殿,地板上只放有一块厚榻榻米,那是天皇的“玉座”。后来把铺满榻榻米的房间叫“座敷”。乡下普及榻榻米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了,历史也就百余年。日式事物在城里日见其少,没睡过榻榻米长大的人越来越多,倒是落后于时代的乡下总在替城里保持着所谓传统。

温泉旅馆一般是日式。风尘仆仆,一到了旅馆,脱下鞋,踏上榻榻米,脚底板顿感舒坦。泡过温泉,穿浴衣坐在沙发上,窗外或是山,或是海,暮色渐浓,更觉神怡。落座的这部分空间叫“缘侧”,多译作缘廊。它是檐下走廊,里侧是“座敷”,外侧是园地。旅馆的缘廊当然被间断,大都封闭在房间里。缘廊类似中国建筑的檐廊,亦即谢灵运“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闺之清阴”的步檐。不同之处是缘廊铺地板,用处也就大不同。缘廊与“座敷”以纸屏相隔,不仅是过道,拉开纸屏便用作出入口,搬进钢琴之类的大件也不愁通不过“玄关”。办红白喜事,缘廊又充当正门,和尚、神官、胥吏等由此登堂入室,新娘从这里进,尸棺从这里出。有的地方当作日常出入口,也有的地方因它出棺而忌讳日常之用。 最妙的是缘廊还可以坐,炎暑纳凉,中秋赏月,冬季像懒猫一样曝日,胜似大陆北方农村蹲墙根。秋风起,有人说真想坐在缘廊吃西瓜。那该是孩提时代的快乐,使劲儿吐出瓜子,看它落向土地。山口百惠在《秋樱》中唱道:妈妈坐在缘廊上翻开相册,又一遍讲述我小时候的回忆。缘廊和井边(“井户端”)往昔是人际交流的两大场所。路过邻家,无须脱鞋进屋,在缘廊边垂足而坐,聊几句田中家长铃木家短,其乐融融。 日式房屋没有坚固的四壁和固定的间隔,纸屏是墙,也是门和窗,似隔非隔,几无隐私可言。秘密谈话不是关起门来,反而大敞四开,窃听者无处藏身。现代的隔音意识是受了西方生活及文化的影响,于是丧失了传统。夏日里游玩,住在农家院,各处纸屏全敞开,房屋好似只剩下木架,恍如置身于野地,八面来风,通体清爽,不禁叫一声快哉。檐下挂着风铃,中国古代叫檐马,丁当作响,更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了一句古诗:自从环佩无消息,檐马丁当不忍听。呵呵。 古时候普通农家没有缘廊,江户时代甚至有地方视之为奢侈而予以禁止。缘廊具有多功能,也是做一些活计的场所。檐下悬挂,廊上堆积,譬如萝卜或鲑鱼,现今仍然是农家或渔户丰收的一景。缘廊本来是生活样式的实用性部分,渐渐也具有审美功能。剧作家木下顺二说:日本人的思考方式中好像有喜好把界线弄暧昧的侧面,现象之一即缘廊这个一半内一半外的场所。诚然,缘廊既不是屋里,也不是屋外,显现了日本人特有的暧昧。中国的檐廊断然在屋外,而缘廊暧昧,仿佛是人工环境与自然的衔接与过渡。 自从被美国占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大变,以至于说日式,前面要加个纯字,纯日式才可能是地道的传统风格或样式。城市里寸土寸金,为使室内面积更大些,把出檐缩进去,更无余地设缘廊。于是乎日剧里缘廊多起来,在那里谈情说爱。如今要体会缘廊之趣,恐怕只好去乡下,或者去京都。京都的“町家”(市坊人家)是老屋,探头往里看,甬道深深深几许,想来那屋里是阴翳的。实际上四面房屋,当中有庭园,起到了采光、通风的作用。缘廊临园,园里栽种些低矮的观赏植物,若铺上白砂,更显得亮堂。但是以町家为代表的京都景观及传统生活方式也正在消失,前年(2010年)甚至被致力于保存建筑物及文化遗产的世界遗产基金会(WMF)列入了危机遗产名单。 游到京都龙安寺,欣赏枯山水,就是坐在缘廊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