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去世,二十四年矣;尤其这十几年来,台湾的政客,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所谓政客,只要是当着群众之面、在镁光灯前,总能神采奕奕、口角春风;他们能言善道,专擅表演;他们长于讨好,谀笑取媚;他们随时随地,总有法子弄得大家心花怒放。但私底下,你若和这些人相处,只要不涉功利地闲聊两句,其无趣,其乏味,较诸他们神采飞扬的公众面目,恰好,形成了最大的反差。 他们的政治,只是表演,没有性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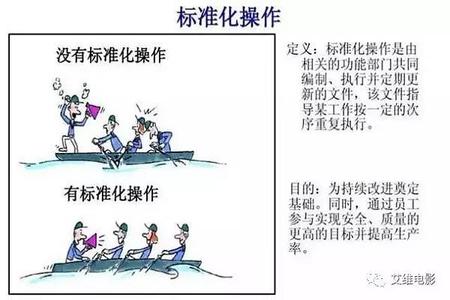
同样的,我记得上回在大陆时,有位大四学生,陪同我数日;有次闲聊,他谈起学校里的老师,才说几句,竟是满脸的不服气。这年轻人心思干净,不是个轻易憎恶之人;我看他反应激烈,遂问其原由。他言道,大学里有许多老师,课堂上言理滔滔、口沫横飞;不仅会讲,更是爱讲。可私底下,言谈相处,只需半晌,便顿觉索然;平日夸夸其言,但真正面对事情时,其无能、其昏聩,都让人觉得,课堂所讲,果真只是空口说白话。而且,他们平常爱发议论,时不时,就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个个都像是正义之化身;但见其实际为人,却又和这样的慷慨激昂,极不相称。换言之,他们所言,与他们所行,有着极严重的断裂;他们的学问,又与他们的为人,两不相干。 他们的学问,没有真性情。 没性情的政治,是政治的最大堕落。没性情的学问,则是学问的最大异化。 学问的异化,古来已多难免;言行之断裂,更早在孔子对宰予“听其言”而后又必“观其行”之时,就已不乏其例。但中国儒释道三家的学问,终究是生命之学,都是体证的学问;体得多少,便说多少;证得几分,也只能老实说那几分;若是未证言证,空谈瞎扯,虽可瞒却世俗眼目,却难逃方家法眼。譬如那孔门,子贡聪明绝顶,常唱高调,但孔子也不客气,几回都直接泼他冷水。尤其禅宗,只要语涉浮夸、不真不切,就难免受斥遭喝,甚至一棒打杀;那班横眉竖眼、峻烈非常的禅师,岂容你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又岂容你絮絮叨叨地玩弄概念? 这样的体证之学,忌空言,也忌抽象;凡论理言学,总以真切为要;“能近取譬”,不骛高远、不玩概念,必归结于具体真实的近前之事。正因如此,中国传统学问的异化与断裂,其实并不严重。 但是,自宋之后,形势丕变。宋、明两代,理学大兴,心性之学呶呶不休的形而上争辩,早落入了抽象思考,不再是孔门的平实与真切。因不平实,故理学家多不可亲;因不真切,故其末流也多有伪善。流弊所及,遂有日后朴学之反动;可这一反,却是越离越远。盖干嘉之学虽不涉抽象,但其竟日寻章摘句,埋首于饾饤考据,不仅脱离了自身,也远离了现实。正因如此,到了清末,乍逢变局,这群满口圣贤学问的士大夫,就只颟顸漠然,一个个成了无用之人。 到了五四,这考据学问,又因“科学主义”而借尸还魂;他们奉“为知识而知识”之名,让这种毫无情性的细琐纠缠之学继续在文史学门中大行其道。而后,在“全盘西化”的呼声中,西方的抽象学问,又在大学体制里取得无上的正当性。于是,人人竞言“哲学”,人人大谈“逻辑”。中国的体证之学,因讲究具体亲证,常常“一步到位”,在学者先生眼中,既无“逻辑”、又非“哲学”、更不能写成“客观”的学术论文,结果,轻蔑之、鄙视之,最后,干脆就摒弃于大学门外了。 于是,多年之后,大学的衮衮诸公,久不知何谓“体证之学”矣。即使标榜儒释道三家的研究者,因受限于抽象的概念分析,又受限于“客观”的学术研究,讲了半天,仍与真正的体证,毫无干系。从此,学问后头那真实的人儿,已杳然难寻。正因如此,在当今大学里,所言与所行的严重断裂、学问与为人的两不相干,已成必然;而眼下许多文化名流与学术明星在人前人后的巨大反差,也早已司空见惯。如此一来,那位大四学生对当下大学的满脸不服气,又何足怪哉?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