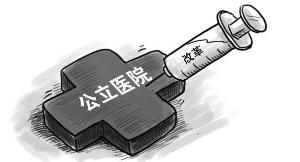历时八年历经多次反复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目前已进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意见的阶段。据透露,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方案两次上报国务院,均未通过。对此,舆论普遍认为系受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所致。 如此判断不是没有道理,三十多年改革造成了未经清除的旧体制因素和不够成熟的新体制因素之间奇特的结合,在社会资源配置体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各个集团及其附庸,为维护既得利益,肯定会在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阻挠收入分配体制发生不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变化。问题在于,这一分析思路有倒果为因之嫌,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从来不是人的意志可以简单决定的,包括这些利益集团及其所处有利位置和维护位置的努力,都只有放在中国社会自身运行逻辑的框架内才可以得到理解。现实生活中,“裸官”成群和富豪移民成风本身就反映了强势群体对个体意志及其历史后果缺乏信心。某些看似能够左右历史的集团,最后证明也只是社会生活逻辑的执行人。 由此出发,我们在探讨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可能的方向和结果时,与其纠缠于哪些集团阻挠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如追问那些集团是如何获得既得利益的,这一利益结构得以生成的逻辑条件是否出现了松动,改革的契机和空间是否已悄然形成。 已故的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教授在其最后的著作中曾经评价道,“中国政府以其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统治如此规模的人口,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组织体,之所以能历经沧桑,绵延至今,就是因为找到了解决所有组织体都面临的“效率悖论”:人类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组织起来,组织规模越大,整合资源的效率越高,同时自身消耗的资源也越多,最终将到达一个临界点,即所消耗资源多于所整合的资源,因而走向崩溃。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开始,经过汉朝的“官山海”,宋朝的“尽收天下之利”,到新中国成立后先是计划经济,后才“放开搞活”,不久又“国进民退”,“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其中一条“超历史”的逻辑主线。只要这条逻辑主线不变,国家本位的资源配置体制不变,围绕国家资源配置资源体系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和确保这一集团既得利益的国家收入分配体制就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当前,中国需要应对的恰恰是国家本位的社会运行逻辑在效率问题上再次遭遇到的挑战。为了提高效率,国家采取资源垄断的方式,但垄断扼杀了创新,而没有创新,效率失去了基础,“山寨成风”不可能形成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提高效率,国家采取了“低成本发展”模式,但经济成本向环境成本、社会成本、道德成本乃至政治成本转移几乎到了极限,污染严重,能源资源耗竭,社会冲突频仍,道德恶性滑坡,经济发展留下的“按揭”到了还贷的时候;为了提高效率,国家采取基建投资拉动GDP的方式,但过于超前的基建最后所消耗的资源远多于所整合的资源;为了提高效率,国家超量发行货币,人为刺激房地产,在转移国民财富的同时,也让自己逼近了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灭的前夜。一句话,传统的集国家之力,通过资源集中来解决效率问题的策略,差不多走到了尽头,国家本位的中国社会要继续存在,就必须突破国家本位策略,通过非集中的方式来提高效率。 所谓“市场导向”,所谓“改善民生”,所谓“拉动内需”,所谓“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其实都是一个概念:分散资源,变国家集中为个人分持,变国家积极性为国民主动性,变个别利益集团有限意志的主导为无数个体的无限能动性的对冲,为巨大组织提供新型的效率提升机制。对于国家本位的中国社会来说,收入分配改革形同“革自己的命”,八年蹉跎的根源尽在于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只是表层现象而已。

最后的问题是:中国这个超大组织体准备好了吗?不改,还有效率提升空间吗?改,可能获得效率提升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