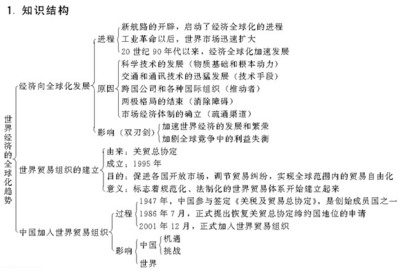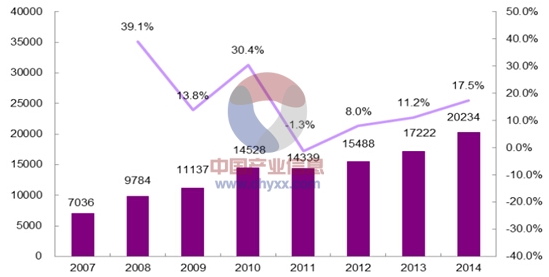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不论是诗歌形式、作品数量还是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都是其他文学样式无法匹敌的。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诗歌,我们可以从诗体的演变、近体诗的格律、意境和章法几个方面入手浅论中国诗歌。 1.诗体的演变 我们都知道文艺起源与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主要观点。在上古“诗、乐、舞”是同源的,总体来说,和音乐、节奏和曲调分不开的中国诗歌,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其演进轨迹,乃是从民间歌谣走向文人创作,从依附于曲调走向立足于词章,从叙事走向抒情,从即事名篇走向注重立意与谋篇布局,从相对于较成熟的四言走向更加完备的五言、七言,从古体走向近体、走向格律。格律诗之后,白话文盛行,西风东渐,新诗出现。 上古诗乐不分,歌谣共生。歌谣之起,起于人心之触动,情感之激荡。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起而嗟叹之,继而永歌之。冲口而出之嗟叹,多为感叹词,即噫、吁、乎、哉之类。叹之既久,由虚转实了。如“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易经·贲·六四》。又由感叹词发之胸臆的简短一言变为二言,由二言而成一节拍。而《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通篇已无虚词,皆为实词。其后一节拍又发展为二节拍,如《涂山女歌》之“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这便产生了四言。四言既成,而没有直线递进为六言、八言,是因为四言一句,四句一章,二三章节,重章叠句,回环往复,足成一篇。这就是上古的歌唱,也是大多数歌唱体的惯例。 四言诗、二节拍,属于嗟叹之词。嗟叹不足,故永歌之。所谓永歌,大体是拖腔拖调,也就是延长节拍。节拍延长了,便需要补充音节,实词有实际意义不便充当此任,语助词就在这时候填补进去了。如《诗经》“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魏风·十亩之间》。随后,语助词又逐渐为介词、副词、代词进而是名词、动词所代替。如“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魏风·木瓜》。如此便产生了第三节拍。第三节拍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三节拍的句式,在两两相对的骈偶节拍之中介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节拍,使得音韵具有抑扬顿挫的变化之美。奇偶相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想境界,经由秦汉,三节拍的杂言逐渐形成了整齐成篇的五言句式。这便是汉乐府与文人五言诗的兴盛。 汉乐府具有较为明显的叙事讲唱倾向,而文人五言诗则逐步转向抒情为主。从《古诗十九首》到曹魏诗人,在对五言乐府的模拟继作中逐渐建立了“上二下三”的句式,一韵到底的押韵,重寄托,尚词采的立意,摒弃叙事讲唱的民歌模式,而代之以抒情言志的文人技巧。从此,作为诗体意义上的五言诗,不再是授之于口耳的声歌,而成为授之于视觉和心思的案头诗。 七言诗的兴盛晚于五言诗,虽然节拍相似,但它并不是五言诗的直接推进。一般认为,它来自于骚体诗和歌行体诗,张衡的《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行”就是很好的例证。直至南朝齐梁时代,诗人们所作七言也主要是乐府歌行体。

齐梁时期讲究声律的五言新体,风靡一百多年,经过包括北朝、隋朝以及唐初诗人的共同努力,古体诗完成了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转型。五言、七言的律诗和绝句从此便成为中国传统诗型的代表样式。 2.近体诗的格律 格律诗成为了代表是有其原因的,中国传统诗歌的格律是在长期创作积累过程中形成的,也是汉语语种及语法特性决定的。 汉字是一种保留了象形特征而又以形声为主的表意文字。简单地说,方块字便于整齐排列,四种声调适合错综搭配,单音节适合于一字一意的意义对称,这便为句式整齐、抑扬平仄、意义相辅相成的句法安排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诗人对句式、声调等方面的格式与规律的讲求形成了诗的格律。 格律诗以格律严整而得名。全篇8句,一韵到底,二四六八句押韵,多数情况下,首句也入韵;韵脚则需用平声和平仄二声的分合,遵照平水人刘渊刊定的107部《礼部韵略》。律诗两句一组,为一联,分别称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其中颔联、颈联必须对仗,即上下两句位置相同的字词词性相同、平仄相对、意义相对。 律诗分为三种,即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排律。排律就是对律诗的一种扩展和延伸,一般为10句、12句或者更多。 绝句分为两种,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绝句的平仄和对仗,是截取律诗的一半。8句平分或首尾拼合即可产生不同的平仄格式。 与对仗同时出现的还有黏合,同一联中的上下句平仄相反即为“对”,上一联末句,与下一联首句平仄相同即为“黏”,这里的要求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3.意境与章法 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的优良传统,近体诗篇幅短小,所以它的行文用字、篇章结构不能不格外讲究,它注重意境含蓄和章法的井然。意境的主要创造方式就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表现情志是“写什么”,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是“怎么写”。诗歌重抒情,抒情最忌直白,需要借助环境。大凡优秀的诗歌,几乎没有刻意写景、纯粹写景的。 古往今来,众多的优秀诗篇在我们眼前展现了纷繁复杂、无穷远尽的意象。有雄壮的,“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有深沉开阔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有以动感取胜的,“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有以静取胜的,“明月松间照,青泉石上流”,有意象纷呈的,如:“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有朦胧深致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有阴涩晦暗的,“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有凄惨激越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以怪为美的,“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有主体鲜明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幽怨悲苦的,“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有纤细柔弱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意象多种多样,很难作出无所不包的统计。塑造意象第一贵鲜明,即写物能抓住其关键特点,作到传神而生动,写人物能抓住其最典型的神态,直入其精神世界,使人物形象如在目前。如写猪“明日钢刀犹未扰,今朝锦梦莫相违”,写猴“褐尾方藏双股下,红臀已跃从人前”,写女孩的娇嗔“巧嗔忽来风打水,雷霆乍去鸟依人”,写自己“仰天大笑出门去”;第二贵深遂,即深沉博大,或意境开阔,或引人深思,或体现作者深层情感,古人这方面的句子很多,不举例了;第三贵自然,即使意象繁复,也应举重若轻。 4、格律诗语言形式的文化特征 如果从语言和文化的深层关系看,近体诗的形式不仅在文本操作层面上具有内在的价值,在深层结构上,它还直接或间接地表露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精神内核侧重于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其背后,是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从地理环境看,中华民族一直以黄河流域为主要生活区域,自然条件优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居住环境相对稳定,因而他们的性格就不像西方游牧民族那样骠悍,敢于抗争,感情也不如他们奔放,而趋向含蓄理智。狭小的活动范围、浓厚的乡土意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很自然地孕育了汉民族喜欢和谐、追求统一、讲究中庸的思维定势。政治上,汉民族的政权、神权、主权高度统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无从立足,从而也产生了把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混为一谈并为“王权天授”寻找理论依据的“天人感兴”的迷信说教,以及要求个体绝对服从群体的东方人际关系模式。所有这些,都使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存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物我合一”等带有整体观念色彩的哲学命题,以及尚实、含蓄的表现特征。反映在传统诗歌创作上,就是“诗言志”这种物我合一、主客体统一的美学观念。 近体诗沿着诗歌言志缘情的古老传统,特别突出并发展了艺术中的情感表现功能,重主体主观情态的抒发,强调以情动人,情景交融,情和景以相融相洽的整体性形成了诗歌意境本身固有的自然本质。而意境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境界的特殊性,在于它必须具有给人以“境生于象外”的审美效果。与之相应,意境的描绘要求既含而不露,又自然明白,因此古代诗人都颇重含蓄,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等多种说法。这也是近体诗布局谋篇尚简,用字简约而在文法规则上自由切割意合的主观原因。为达到言简意远、意在言外的意境,诗人不得不抛开正常的文法规则,省去各种外在的语法标志,利用高度密集的意象、切割文法、锤炼“诗眼”等方法,拓宽了诗句本身的表达容量,使语言符号产生了极大的伸缩性、延展性和多义性。具言之,密集的意象,强化了诗歌重重叠叠的画境,给读者留下艺术想象的“空白”,产生旷远朦胧的美感效应;各种动词的省略,提高了意象的视觉性、独立性,诗的空间玩味也大大增强了;各种虚词的省略,不仅使诗语充满了宛转屈伸的灵动之美,而且摆脱了逻辑链词的限制定位,从而使诗呈现出一种浑然直观的境象;“诗眼”的锤炼,使得意由神来,一字生辉,把诗歌的语言潜能发挥到极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近体诗形式的简约灵动,是我国一贯崇尚的讲究“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传统文风的反映,也是传统思维模式在文化层面上的折射。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08 2、鹏鸣著.中国诗歌史略.作家出版社, 2012.09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