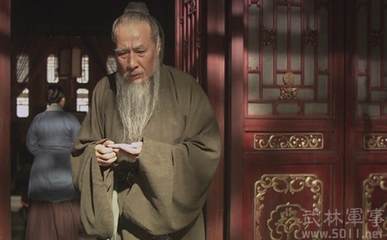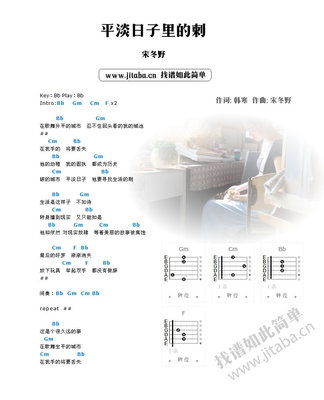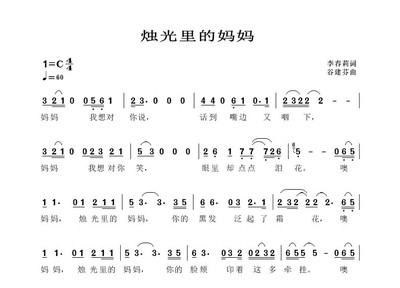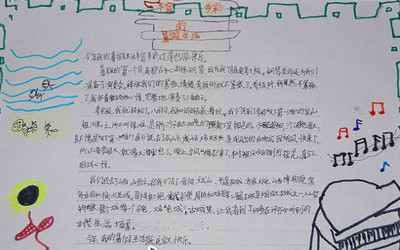一位朋友谈及最近在他所在城市的一桩劫案:男性劫匪向女事主亮出刀子,威胁她不把钱物交出就要遭伤害。女事主镇定自若,一边拖延时间,一边柔声对劫匪说:“大哥,你一定有难处!不然不会走这条路。唉,谁一辈子不遭过罪呀!我同情你,大哥,不想你为了这么点钱去坐牢10年,害你的妈妈天天哭肿了眼。我就这么点钱了,你抢也只能抢去这个数,送你好了!”女事主从手袋掏出200元,放在劫匪没拿刀的手上。劫匪瞪着钱看了一会,不作一声,忽然,掩面大哭,疾步逃开,刀子掉在路上。女事主僵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朋友说,各行各业都评先进,我看这个劫匪也该受列入“好”一列。我说,列为“坏”中的“良心未泯”类,是不是准确些?

由此可见,尽管是“匪类”,不加分析地贴上划一的标签,并不稳妥。鲁迅曾粗略地区分为“损人利己”类和“损人不利己”类,前者因不损人无从利己,好歹合乎逻辑;后者如劫掠之后杀人放火,恶得莫名其妙。上述例子给我们的启示,自然是正面的。一些人遭遇困厄,感情上特别脆弱,邪念占了上风,便铤而走险。这时候,如果有人及时做出适当的心理干预,犯罪者可能悬崖勒马。这样一来,年纪尚轻的罪犯免于进入万劫不复的歧途,不必受追捕,受检控,把人生赔在亡命或者坐牢上。连带地,罪犯的父母及其他亲人都得到好处,社会资源上的节省,更难以计算。这位女性,实在是最值得赞美的见义勇为者,她以理性和温柔所制造的奇迹,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效益,比和凶徒搏斗的勇敢者大得多。可悲哀的是,劫匪一旦犯案,就被受害者和执法者归入“穷凶极恶”一类,性命交关的场合,谁来得及采取软性的迂回的“动之以情”?以200元换来“双赢”,实在太稀罕了。 一般而言,世间并无“好的”劫匪,然而,在木心先生的诗集《西班牙三棵树》里,读到这样一节:法国的山中盗寇 / 托人到巴黎 / 买了最好版本的 / 《帕斯卡随想录》 / 行劫之暇 / 读几页,心中快乐。这类“盗寇”,是罗宾汉式大侠还是切·格瓦拉式的革命家?无从得知。也不知道,这伙强梁一边擦拭杀过人的枪和染血的匕首,一边读几页《帕斯卡随想录》,所得到的“快乐”,是来自思辨,还是来自幽默?难说。能肯定的只是:这并不诲淫诲盗的“最好版本”,并没有像前面所提到的慈悲女事主一样,让盗寇中止犯罪;也许,里面的内容,让强盗读起来,更加认定其行为是正义的。 我随即上网购买了《帕斯卡随想录》,并非打算在抢劫之暇读几页,而是早知道木心先生对它推崇备至。而我敬仰的木心先生,是纯粹的文人和画家,笔拿得,刀子却未必,除非是木刻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