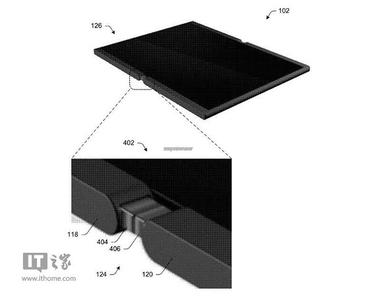“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坐在你的位置上我会做什么?”
1952年的一天,在《纽约时报》公司工作了44年后,戴维·约瑟夫走进总编辑特纳·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高声问道。
卡特利奇离座后,约瑟夫坐在他的位置上说,“现在,如果我是你,我会要求你辞职。”卡特利奇默默站了一会儿,然后温和地说:“好吧,戴维,你这话正是我想说的。”于是约瑟夫正式退休了。
作为总编辑助理,约瑟夫的年纪太大了,他也不可能再往上升了,但是割断这么多年和《纽约时报》的联系如此困难,以致于他不得不选择了一种戏剧性的场面。
对于投身于跨国公司的华人经理人来说,上面的戏剧性场面是无法企盼的。也许,约瑟夫的“职场杀手”不是年龄,而是跨国公司的中国经理人难以逾越的鸿沟。
看上去,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出入高档写字楼,出行坐飞机;衣装笔挺,说话中英文夹杂,高薪,享受假期;经常一群人聚在一起,频繁在各大公司跳槽。他们的“职业生活质量”要从薪酬水平、工作内容、工作氛围、个人发展、工作稳定系数等五个角度来衡量。
他们是中国对外开放与世界接轨以后诞生的一个新群体,一个体面的特殊阶层——跨国公司职员,他们有着不为外界所知的“江湖”;随着跨国公司进入数量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这一群体的经历和命运,开始逐渐为外界所知。
但是,使外界对这个群体感兴趣的,远不是他们的体面与优裕,而是他们所效力的都是赫赫有名的跨国公司,是一个个经济王国甚至帝国。华人经理层掌管着这些经济帝国在中国的命运,而这些经济帝国又影响着这群华人经理的命运;这种互扼命运咽喉的博弈过程,对局外人而言,热闹与门道兼而有之。
然而,行走在跨国公司高速列车上,华人经理们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们的处境怎么样?
远处有座粗线条的高山,那是大部分跨国公司的中国经理人的职场生存图:有的人站在山脚下,有的人到了半山腰,有的人已经接近于山峰。越往高处走,人越来越少,空气稀薄、空间逼仄、莫名的冲突。他们的表情也越看不清楚(有时他们注定了出局),内心更未为可知(有时不无民族情结);他们开始投身国企(真的多了起来),要不就干脆自己去创业(年岁却已不饶人)。
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表现在跨国公司的中国经理人身上,就是“玻璃天花板现象”(glass ceiling)。“玻璃天花板现象”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指欧美大型公司中,外来移民尤其亚洲人只能担任技术等低层职务,或者做到相对高位后很难再升,无法进入核心决策层这一现象。
这绝不是偶然和小圈子的谈资,一向都是热门和敏感的话题。本刊2001年1月做过一篇《跨国经理人的全球化难题》的报道,如今我们把视角更多地转到了中国经理人在跨国公司的生存状态,以及“跨国公司的本土化难题”。
著名华人经理人名单
名字 年龄 经历 现职 备注
吴士宏 45岁 微软中国总裁 TCL集团副总裁 人称“打工女皇”
叶 莺 50岁左右 当过记者、外交官 柯达全球副总裁
李亦非 38岁 博雅公关中国区总经理 MTV音乐电视频道中国区总裁 入选《财富》2001年度50位国际商界 女强人
韩 颖 48岁 惠普中国首席财务官 亚信首席财务官
李汉生 43岁 惠普中国副总裁 方正数码总裁 2002年8月离职
高群耀 40岁左右 微软中国总裁 华登国际投资集团中国区总裁
李金水 46岁 康柏中国总裁 安雅咨询顾问公司总裁 6年间经历了4次被收购
刘持金 40岁 爱立信中国区副总裁、 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长 诺基亚中国区副总裁
张醒生 47岁 1990年加入爱立信 爱立信中国执行副总裁 2001年3月, 被授予首席市场执行官 这个特殊的职位
刘江南 40岁左右 阿尔卡特中国副总裁
舒 奇 40岁左右 10多年海外经历 中国惠普副总裁
刘小明 40岁 百事可乐中国总经理 伊莱克斯中国总裁
朱德淼 40岁左右 瑞士信贷中国业务主管 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总裁
杜家滨 43岁 微软中国首任总裁 思科中国总裁
黎修树 54岁 戴尔中国总裁 SGI中国总裁
唐 骏 40岁 上海微软技术中心总经理 微软中国总裁
孙振耀 40岁左右 中国惠普总裁 新惠普中国总裁
到底有没有天花板跨国公司的人事变动,尤其是总裁级人物的下课或离职,总那么轰动和引人注目,这里面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性因素: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精英们幸福或不幸的生活,以及社会人生的高度浓缩。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参见附表)。但是,“天花板现象”到底有没有?达到了什么程度?
柯达全球副总裁叶莺说:“我觉得,glass ceiling在人的心里。我在美国政府工作时,作为一个归化的美国人,可能有些高度达不到。不错,按照美国宪法,我只有一样位置达不到,那就是美国总统。这是一个玻璃天花板,除了这个,我为自己定一个目标,走到哪一个路程,我都可以做得到。”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用爬山做比喻。前戴尔中国总裁、现SGI中国总裁黎修树比划着说:“从这里爬到这里,精力这么多,但这里再爬一点点,精力就耗很多。值不值得呢?对个人的价值是不是提高?每个人都会想的。”
前康柏中国总裁李金水则反思道:“在跨国公司有什么问题呢?这是一个玻璃房,大风大雨我不怕,也晒不着,多舒服呀,为什么要去外面碰机会?我想问一问经理人,经济好你不走,经济不好,你更害怕。你永远一辈子在跨国企业打工了吗?”他把跨国公司比作一条船,“你站在船边的话,风平浪静没事的。如果大风大浪,谁最容易被抛出去?站在船边的人!于是你踩人家,推开人家,尽量走到船的中央。这就造成在一般的跨国公司为什么有那么多政治斗争。”
专门为跨国公司搜罗高级经理人的王李亚洲资源公司CEO王承伦是好多跨国公司的“救星”。与大多人认为“天花板”的问题出在跨国公司身上不同,王承伦说:“国际老板希望给本地人机会,问题是他们还没准备好。”他提醒道:“你不要被一层玻璃挡住了。很多人想到上面的地方,但是从这个角度,他们不知道哪条路可以走。他们有一点迷路了。”
“Know the game(游戏规则)很重要。”王承伦曾对外企经理人演讲过“如何在跨国公司发展事业”,不管在高科技、服务、消费品以及金融行业,“并不是没有位置,而是合适这些位置的人不够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理想的candidate(候选人),都是有两种语言背景的,专业化,品质要高,有可以承受的薪水,很容易在国内取得成绩等等。”
王承伦很推崇北电中国的一个30岁的销售部主任,他没有海外经历,直觉、思维却十足地国际化,“他代表了‘新中国’。”不过,对于大陆的经理人来说,不利的仍然是“软技能”稍逊,越高越难,“跟外国人在跨国公司抢一个职位,至少得付出好几倍的努力。”而跨国公司要在中国发展,必须本地化,因此,“天花板是个时间问题。再过3、5年,在较高位置上本地人的比例会多起来。”
微软“滑铁卢”与IBM培训
2002年3月26日,唐骏从上海微软全球技术中心赴京,接替高群耀出任微软中国总裁。从精明细致的杜家滨到敢闯敢干的吴士宏,再到沉稳持重的高群耀,微软在中国10年间,走马灯般地换了4位总裁,几乎成了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滑铁卢”。
尽管微软频繁换帅成了在华跨国公司的一个纪录,被称为“微软人事现象”,但也说明,跨国公司的人事变动是正常现象。这其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几位外企人士都谈到了IBM对人的培养和尊重,“那真是没得说,几乎没有一家可以做到。”黎修树在IBM工作了十几年,对IBM的培训极其推崇。“在IBM,叫fast track,即很快地升上去。只要IBM认可你,它所希望的人,几十个、几百个很早就定下来了,给你机会,你做成功了就能上去。而如果按步就班的话,很难很快升到这个地步的。”
连身在康柏的李金水都对IBM“很感激”。1998年康柏收购DEC,作为原天腾(1997年被康柏收购)中国总裁,李金水被降了两级。带着某种“负气心理”,李金水做成了康柏在中国的电子商务项目。一年后,他“重新冒了出来”,做到了康柏中国总裁。李金水对本刊记者坦言,他就是从IBM学到了电子商务的概念。
IBM给职业经理人的这种“天堂”感觉,堪与已经创刊100年的《纽约时报》相媲美,“在创始人奥克斯时代,《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事经理——上帝。”不过,即使“上帝”活到今天,也可能会为“一根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问题而头痛不已吧。
也有人对记者大吐怨言:“所谓CEO,名字非常好听,但是实际上你的实权有多少?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每一天的工作就是执行、运营,完成任务。在跨国公司你越做的高级,你的培训越少,脑筋也越来越死,从这个角度我们很吃亏。我们这些所谓的精英,根本不能抓住新的机会,也根本没有机会给我们抓住。这是我们最惨的地方。”
难道说中国的经理人注定了只能是跨国公司的过客吗?李金水反问道:“你看过哪个不是过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做不同的过客,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落点。”叶莺则感慨:“在企业中的起落,跟人生路上的起落,以及经济指数的起落,都是一样的。这是规律,没办法抗拒的。”
上司、下属和派系
自言“在惠普工作20年,老板换了18个”的孙振耀,对如何与上司相处有独家心得。
1982年孙振耀加入惠普,1991年由台湾派至北京,2000年4月,升任中国惠普总裁。2002年5月,惠普康柏合并后,孙振耀接任中国新惠普总裁。在新惠普总裁卡莉·菲奥莉纳面前,孙振耀把自己比喻成“七八成的狮子、两成的骆驼”,即既有进取的精神,还有吃苦耐劳的能力。
把握好心态同样重要。身为思科全球高级副总裁、思科中国总裁的杜家滨极力淡化自己的角色,他坦诚地说:“作为职业经理人,每个人上面都会有一个老板。”
“一定要让员工支持你,服你。有一两个不服就很麻烦,因为直销需要百分之百地投入。”曾使戴尔中国高速增长的黎修树,看问题的角度与孙振耀、杜家滨不尽相同。有一本《王子》的书说,做一个好的领导,你必须让员工既怕你又爱你(fear and love)。“当你跟总部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时,一定要很坚决,让员工觉得你这个领导是强的。”
不仅如此,在外企还流传着“香港派”(或称“港系”)、“台湾派”(或称“台系”)、“美国派”的不成文说法。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台湾的经理人更扎实、稳正,香港的经理人更活泼但有点轻浮;按行业分,台系多在制造业,金融领域则是港系最明显;相比而言,港系的经理人不太歧视大陆人。当然,也有人修正说,“他们可能不是故意这样子的,而在一起饮茶、讲话方便,不一定就会怎么样。”
有人则说得很尖锐:“团结就是力量!你觉得自己太单薄了,靠大家,我就不容易被干掉。如果没有利益的结合,怎么会有香港帮、台湾帮呢?”职位越高,权力斗争越厉害。有一位中国总裁(不愿透露名字)就遭遇过“攻击”,美国同事去他那儿看一眼,即使情况好也回总部说不好。“不用想得太多,知道就行了,但要把结果做出来,对自己负责。”
见了很多外企“斗争的过程、下场”,让人觉得“很过瘾”。美国是分权式管理,怕“天高皇帝远”,所以会找个人监控。而要把你挤走,老板不用出面,发动“所谓的群众力量”就行了。“群众们”自己也心知肚明,据资深业内人士透露,在某一国际著名手机品牌的北京总部,有所谓的“上海派”,10个市场总监里6、7个都是上海人,他们过从紧密,在一起开会时都讲上海话,外人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这种小利益团体使跨国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国企”,这也许是“本土化”的一种悲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