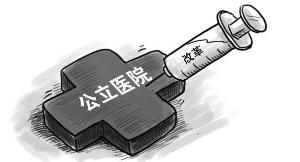《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书名跟它的作者华生一样,理性平和,保持建设性的姿态。 他坦言,希望通过这本书思考历史在行进到岔路口时的方向选择:是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现代化和民主转型的东亚道路;还是堕入贪腐和贫富矛盾激化,动乱革命后仍在陷阱中挣扎的南洋道路。两条道路,优劣自明,如何实现好的结果才是关键。 亲自参与了多项重要改革设计的华生相信,良好的机制设计仍是中国未来启动改革,成功实现转型的保证。 国企改革核心是去行政化 如果今天央企私有化,那倒真会把中国带入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经营报》:在你的新书中把未来经济改革的焦点定在国企和土地制度上。我们知道,当年国资委的成型,其实是您最早参与设计并推动的。 华生:对,是我们在1985年提出来的,1986年在专列上我向国务院领导们还做了两次专题汇报。 《中国经营报》:但现在很多人认为国资委已经成了国企的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未来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之一。你对国企直接私有化的改革路径一直持否定态度,那么,你认为未来国企应该怎么定位或者说它的改革路径是怎样的? 华生:我觉得国企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去行政化,即不能政府办企业,政府办企业在各国都被证明是有问题的。但也要看到,存在很多大型国有企业不单是中国的情况,金砖国家印度、巴西,包括俄罗斯都是这样的。俄罗斯曾经把国企都私有化了,国家垄断资源都集中到私人家族手里,但我们看到,结果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这些获得巨大利益的私人家族到西方去购买豪宅,花数亿英镑去买足球俱乐部,这种状况下,社会是很难稳定的。所以,俄罗斯走了一条先私有后来又部分再国有化的路子。很多人说,只要是私人企业,是自己挣来的,我们就服气。但实际情况是,国家垄断性资源转移到私人家族手里的过程,怎么可能没有官商勾结?我们可以设想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如果转移到私人家族手里,中国老百姓会是什么情绪。这些家族能跟政治没关系吗?一般的老百姓能变成中石油的老总吗?所以,我反对简单的国企私有化。如果今天央企私有化,那倒会真把中国带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大企业是一定存在的,你不可能都把它拆分了。比如,移动通讯运营商,中国最多搞三四家就不得了了,英国就一家,美国也就是两三家。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想透了,中国国企要发展的道路是去行政化,是通过资本市场等形式,使它的股份逐步地多元化,使它跟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少,使它越来越成为一个现代企业。但这不是一步能做到的。中国的经理人文化、法律法制意识的培养都需要时间。我们现在不是没有做得好的企业,比如万科,它第一大股东是华润,你可以说它是个国企,但是它的股权是相当分散的,经理人集团掌控大局,有长远意识和眼光。这说明中国走这条道路也是可以的。我反对极端化的要求一步搞成,认为国企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了,要把它们打掉,全部私有化。而私有化的结果就是到私人家族中,到那个时候不管怎么公平,都是假的。老百姓即使分到几百股,也无济于事。 土地改革要让城市化主体归位 改革土地财政,关键是中央政府有没有决心。 《中国经营报》:你提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上应该最终把现在地方政府、开发商以及城郊农民获得的巨大利益转移到最需要变成市民的农民工群体身上,目前来看,这其中的关键障碍是什么? 华生:我强调土地制度的改革,因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两个要素,第一是国土,第二是人民。而土地又是涉及每个人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财富分配形式。现在看来,太多的人穷是因为没有房,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主要困难就是没有房,很多人富也是因为拥有多套住房和土地。而房子涨价,是因为房子下面的地价涨了,所以土地问题是一个关键。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就是从土地问题上突破的,土地问题突破了,联产承包制取得成功了,大家对改革的信心有了,保守的力量就让位了。如果土地问题没解决,吃饭问题没解决好,80年代的城市改革根本搞不起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矛盾,贫富两极分化,可以说有一多半都是土地带来的,现在的社会事件有一半以上也是因为土地纠纷导致的,贪腐相当大的一块也是跟土地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把土地的概念再宽泛一点,包括矿藏可以说都是土地资源。因此,土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政治的焦点,未来的改革必须从土地制度入手。 《中国经营报》:那么,在土地制度改革的具体路径上,你似乎不太认可重庆做的“地票”交易模式,你也一直反对小产权房的合法化。但现有土地制度的很多纠结点似乎很难解开? 华生:我觉得第一个是要先解决方向问题。我认为,这些年来,我们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上是有偏差的。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农民变成市民,也包括中小城镇的居民到大中城市来。全球的城市化都是这么一个过程。所谓外来人口,包括两个部分,主要部分是农民工及其家属,另外是外地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移民来的人口。这两部分人是中国城市化的主体。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讨论,包括在研究土地问题时,基本上把这个主体甩到一边了,没有人讲他们的事情,好像我们解决土地跟他们没关系。但实际上,如果农民工不进城,如果不是因为大量外地人口涌到大城市来,就不需要征地,土地也不会持续升值。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现在我们把城市化的主体甩掉了来研究问题,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政策偏差。 比如我们为城郊农民争取越来越大的利益,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城市化的主体,而这样做导致的结果是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真正的城市化主体要进入城市更困难了。再比如小产权房的问题,城中村农民的房子是小产权房的时候,他租给农民工住,如果直接将这个房子变成大产权房了,他就可能把农民工赶走了。因为,房子值钱了,卖了以后拿到银行去储蓄,利息都比原来的房租高很多倍。 所以,我说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要解决方向问题,即回到维护保证城市化真正主体的方向上来。 《中国经营报》:你在微博上说过,要抛开现在房地产开发模式,房地分开,进而把现在捆绑在房地产上面的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共同体拆开,但在现有土地还是垄断在政府手中的情况下,这个可行吗?并且,现在地方财政似乎真的非常紧张,地方政府怎么会主动让利呢? 华生:你要看到,地方政府跟企业一样,钱永远是不够的。我们看到,卖地最多的地方,比如北京、杭州等等,都可说是最有钱的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跟企业家一样,越有钱野心越大,越觉得钱还是不够。所以钱够不够永远是相对的,没有土地财政的时候,地方政府还不是照样过日子?所以说,地方财政困难目前来看是带有虚假性的,北京、广州、杭州这些卖地最多的地方,是因为穷得过不下去了吗?显然不是。财政就应该是政府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西方的地方政府就是这样,首先算算自己有多少钱,然后去办事。而我们的地方政府是,要办事就想办法在政策上开口子,看到土地可以卖钱,就在土地上做文章。 所以未来要改革土地财政,关键是中央政府有没有这个决心。我认为,这个决心不是不可以下的。我举一个例子,当年部队、武警还有执法机关经商,其中的利益是惊人的,当危及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时候,中央下决心不就解决了吗?关键是这件事情利害关系有多大。现在看来,如果按照土地财政的路子搞下去,甩掉城市化的主体,政府靠倒卖土地过日子,与地产商成了利益共同体,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国家的根基都会动摇。是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还是要政府不该得的土地收益,这个账很容易算。而且,现在通过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赚到的钱越来越少了,因为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下,拆迁补偿越来越高,加上基础设施建设用掉一大块,真正净落到地方政府的钱只能越来越少,而地方政府还要背负一个卖地的恶名,累积巨大的民意压力,得不偿失。跳出来看,通过卖地获取收入的政府,除了香港特区,全世界没有这么做的,它不是一条正路,而我们恰恰学了那个最不好的。况且香港卖的全是公地,并不需要靠征地来再去卖地,所以也就没有我们这些矛盾。 分配改革是场硬仗 等茅台酒价格下降一半,收入分配就成功了。 《中国经营报》:你也曾谈到,分配改革必须放在土地制度改革之后来,这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华生:首先,土地制度改革本身就是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什么把收入分配放在后面,因为土地改革难度很大,但是好处也很明显,它能够解决我们城市化的主体问题,会带来内需,带来经济增长,好处一大堆。直接的收入分配改革难度很大,但好处不是很明显,得罪的全是强势群体,或有话语权的精英,受益者则是分散的弱势群体,所以这样难的改革要摆在后一步,否则可能还没干成呢,改革者自己就牺牲了。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提到,等茅台酒价格下降一半,收入分配改革就成功了。是不是说这项改革的关键还是在政府这块? 华生:对,应当说从政府到社会改起来都不容易。收入分配改革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的隐性收入猖獗到这个地步,因此这项改革的触动面会非常巨大,涉及我们整个财政税收制度,从它的制度设计到监管体制都要做根本性的变革,否则什么也改变不了,分配不公现状很难改变。 《中国经营报》:现在看来,年底前一个新的收入分配方案就要出台,你对其作用并不看好? 华生:出个方案并不难,但把一些原则性的提法归到一起来形成文件,也许更全面一些了,但我不认为会解决多少问题。因为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场硬仗,现在大家其实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比如现在都说要动垄断行业的利益。媒体属于意识形态,可说是最垄断的行业,动你们媒体各位从业人员或你们领导的收入就能解决贫富差距?你自己想一想就会明白这很可笑。这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简单。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认为现在各项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很难推进,就是因为阶层的利益固化,甚至出现了权贵化,但你似乎不认可权贵资本主义的判断? 华生:要看到,我们国家现在所谓的权贵不是卡扎菲家族,也不是苏哈托家族。现在的高官阶层,在卸任后根本不可能把国库背回家去,但其中很多在任内确实得到了不少好处,但跟他们曾经管理的资源来说是九牛一毛,远远称不上权贵。包括大型国企的领导人,他们到点也要退休回家。他们其中有人在任内可能捞了一点,但是相对于他们曾经掌控的超大型国企,这些人在任期捞的全加上,一般也远远抵不上市场化的经理人收入,哪里能称为权贵。这说明,这些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阶层是非常飘忽的,是不稳定的,会有新老更替带来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会带来不稳定性,会导致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是有权贵资本的问题,但你肯定不能说中国的主要资产已落入那种固化的权贵家族。 《中国经营报》:你对政治改革的起点设计,也是先从党内民主开始谈的,强调机制设计、投票程序,而不是理念上的? 华生: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程序。中国人喜欢做是非判断,实际上西方民主主要讲程序对不对,程序对了以后,最后就是选出一个烂人,大家也得认。我们的问题是,可能口号理想都非常好,有时可能选的人也不错,但就是没有程序保证。就是好人变坏了,他在台上你也没办法去制约他。我强调党内民主,并不是说我完全把希望放在这个上面。因为我同时强调了人民代表的选举跟参与机制的保证,跟上一个问题一样,政治改革的推进也要内外配合。但是讲党内民主,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更主动,没有任何可以推诿的理由。因为党内不存在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也不存在民主素质问题,因为按照定义都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从党内民主开始推进,可以使得那些不愿意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和阵地,让他们无路可退。 《中国经营报》:中共十八大马上就要召开了,下一代领导人其实跟您是同一代人,经历过文革动乱,又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你怎么评价这一代人? 华生:我对这一代有信心。我这样说,不是看个人的素质,个人素质有偶然性,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主流的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这代人,如果我们对这代人没有信心,其实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那我们还说什么,只能指望子孙后代了。同样,我们对这一代有信心的时候,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就像鲁迅说的,官员跟国民是同构的。具体说来,很快走上领导层的这一代,也就是“老三届”这一代,大都有从农村工厂考到大学的经历,接受的知识信息都是一样的。这一代的确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了解过去的旧体制,且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又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所以相对来说,在社会里的根扎得比较深,更加求实,而且又不乏对新事物的追求,这是这一代的主流。 而且不光我们50后60后这一代,后面70、80、90后都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要求跟我们又不一样了,他们要求更往前走,也是未来的推动力量。也就是新的领导层既要承上启下,又要面对新一代的诉求,所以我认为未来是很有希望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