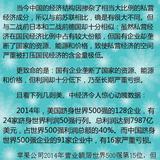10月20日,台湾诗人许悔之在广州方所作了一次题为“在想像的彼岸—我的诗生活 ”的诗歌讲座。一个多小时的讲座,诗人朗诵并阐释了自己从事诗歌创作30年的作品,从17岁写就的情诗《绝版》,到28岁为父亲写就的诗歌《跳蚤听法》,以及创办公司缘由的诗歌《有鹿哀愁》—十多首诗歌,十多张照片,串起了一位诗人在写作生涯中的成长历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到1994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地平线诗社”,许悔之曾多次获得过台湾文学奖与诗人奖。2002年开始,他担任《联合文学》总编辑。许悔之说话风趣,亲切中处处流露出感性的一面。谈到诗作,他常用佛教义理阐释;谈到人生,又用诗歌讲述出诗意盎然的一面:“写诗生涯最可贵的是心灵有一个没有界限的边界,可以一直跨越。” “所有美好的情谊,都是诗的根源。”朗诵会的开篇,许悔之展示了许多他收藏的友人们的书信、照片。“加州以晴朗温和的气候迎接我,经过两天时间的整顿,我又坐在书桌前,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祝你一切顺利。”许悔之以柔和的语气,念出散文家、翻译家林文月在多年前从加州寄给他的信。发黄的信纸,优雅的字迹,许悔之珍藏至今。接着他又掏出一张明信片,是今年7月份作家蒋勋从日本寄给他的卡片。“深峡幽谷,深潭极静,水面如镜,映照天光云影,也映照走进水边的自己,当然自己也是倒影。悔之一笑。蒋勋。”让许悔之觉得这张明信片简直就是魏晋时代的手帖。讲座中,许悔之强调了诗作《有鹿哀愁》。在许悔之看来,写作《有鹿哀愁》是人生里最庄子的一次体验。1998年,许悔之随旅行团到爱尔兰旅行。90年代的爱尔兰仍保有传统、质朴的一面。在近乎荒凉的山谷中,许悔之跟随导游一行人四处行走,导游冗长的有关爱尔兰历史的解说使许悔之的神思游离在团队之外。他随意眺望,突然一只麋鹿跃入了他的眼帘。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那只鹿也望着他。那种眼神震撼了他,“仿佛对我说出亘古久远以来的话”。一刹间,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只鹿,那只鹿就是他自己。“那是一个鹿与我都同时泯灭的时刻。”许悔之回到台湾后,多少次想把这只鹿对他讲的话诉诸笔端,但是不行。之的某一天,许悔之心境低落,决定翘班去看一场电影。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面对大屏幕上北野武的《花火》,他突然想起了旷野中的那只鹿。他掏出笔记本,将想说的写了下来。 许悔之任《联合文学》总编辑时,才30多岁。风华正茂,年轻英俊,亦有当年“台湾文坛美男子”的称呼。“事业、生活、外界评价,似乎一帆风顺。但不知为何,那竟是我人生最困顿的时候。”谈到担任《联合文学》总编辑的那段岁月,许悔之如此回忆。在读者的再三追问下,许悔之首次吐露出缘由。

2003年冬,许悔之与交往十多年的文坛好友因故绝交—也是平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朋友宣布“绝交”。种种因缘际会,使他失去了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对他来说,内心始终无法认同接受。“为什么人世间没有一直可以依赖的关系,永恒的关系呢?”加之其他各种烦闷交加,许悔之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念化工专业的他,用化学专业知识将这一切准备得很充分。 时值六天五夜的假期,许悔之准备好一切之后,开始抄写经文。他觉得在生命结束之前需要做点什么,于是没日没夜地用蝇头小楷抄写《法华经》。一位朋友见他如此劳累,便削了些水果送上来。“在走之前,我得感谢他。”于是,许悔之问这位朋友有什么可以帮忙?朋友说,不如注解一本白话文的《心经》送给他。当许悔之开始一字一句地为朋友注释经文的时候,郁积的心结慢慢解开。几天后,《心经》注释好了,许悔之整理好后送给朋友,自己也随之走出困顿—就这样因为一盘水果,许悔之走出了人生的最低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