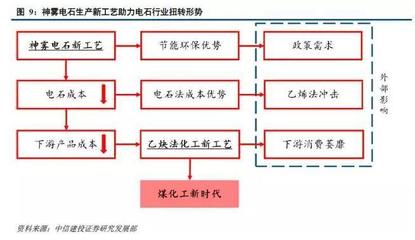聊天中,“新单位”诞生 从创建的第一天开始,陈叙就在讲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她和她的另两位合伙人:刘妍和阿角。

刘妍和阿角都是陕西人,却相识于荷兰鹿特丹举办的一次电子艺术节。那时候,刘妍在荷兰做艺术管理,阿角是一名有IT技术背景的策展人,从此,这两个老乡一直保持着联系。 2008年,刘妍回国,定居上海,邀请阿角联合经营“三术沙龙”——艺术、技术、学术,以不同专业背景的创意人士和大学生为对象,鼓励跨界交流。 陈叙和刘妍的交集则是在一次于北京举办的创意产业联盟的论坛上。在英国时,陈叙学的是创意产业,毕业后曾经跟随《创意经济》的作者约翰·霍金斯一起工作,一直对国内的创意生态非常关注。论坛上,两个女人一见如故,更巧的是,她们居然住在上海的同一个小区。 “联合办公室的点子可以算是在我家客厅和她家书房产生的。”陈叙说,认识刘妍后,她们先是通过网络交流。刘妍会谈及“三术沙龙”的困境。因为没有固定的场地,每次活动都像打游击,有时刚刚交钱预定了一个画廊,国际交流团队的来华时间又变了。 而陈叙会说,她很想经营一家本土的创意产业空间,正在寻找合适的项目。后来,她们干脆面对面地聊,“要么我去她家,要么她来我家,反正只隔着一条路。” 聊着聊着,便聊到了在美国迅速蔓延的一种新型的工作方式——co-working(联合办公)。表面上,是一群自由职业者不愿忍受长期孤独的工作状态,共同分享亦分担一个办公空间,本质上,却强调共处于这个空间的人相处交流合作,形成一个志同道合且从中能够产生新价值的实体社区。 较早成立并发展良好的例子有位于旧金山的Citizen Space,费城的Indyhall和纽约的New Work City。 那时,他们为这个计划中的空间起过很多名字。刘妍感慨,刚回国那几年,为了孩子,她当了五年的全职太太,深受没单位的苦,这个地方就叫“新单位”吧,让所有没单位的创业者都感受到有单位的归属感。 “新单位”再“创新” 和所有创业者一样,定位于为创业者提供新型空间的“新单位”,初期的故事也颇为不易。它的第一个地方位于长宁区映象创意工厂,那是一片由国营塑料厂的老厂房改造而成的loft园区。 通过朋友介绍,陈叙租下了一位摄影师的2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简单地装修后,就开始找人入驻。他们用了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开沙龙,希望园区内其他创意机构的成员来参加,大家交流心得。结果,发出了一叠邀请函,却只有隔壁一家创意公司露面。 “我们是不是高估了他人分享的意愿?”阿角也开始反思。在国外,联合办公室往往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空间,但人们之间的社交很积极主动。可在中国,把两三个陌生人放在一个房间内办公,他们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 “新单位”应该扎到更有分享欲求的环境中,或者自己先搭建出这样的社区,把实用的信息推送给有信息需求的人,让分享、互动意愿强烈的群体有处可循,主动上门。 这两步是同时迈出的。陈叙又开始找地方。这一次,他们定了三条标准:第一,不超过300平方米的空间;第二,交通便利;第三,周边环境较好。于是,就有了现在“新单位”的大本营——一幢位于旧上海法租界中心地带6层楼的老房子。 与创意园区相比,这里更加贴合生活的节奏,多了份城市的烟火味。 同时,刘妍也着力开始营造社区氛围。“新单位”有意把一楼设计成咖啡馆的模样。平时,偶尔会有路人进来喝杯咖啡;周六、周日则会在这里办些有关设计、网络、生活创意方面的沙龙。 两个女孩子承包了这里的咖啡供应,价格与一般的咖啡馆相当,如果搞活动,她们则担任入场接待和饮料服务。 前台是一位瘦弱干净的男孩,除了负责招呼来客,帮客户收发快递、订外卖之外,还负责客户之间的联络,把每个入驻的“新同事”的基本情况写在黑板上——做什么项目,到了哪个阶段,需要什么帮助…… 陈叙说,为了把场子炒热,她和另两位合伙人还利用自己的人脉组织了环保、设计、编程等项目,吸引有兴趣的人来加入。 未来的“新顾问” 现阶段,“新单位”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工作位出租。二至六层共有18张独立的办公桌和4个会议室。大体上,他们分为椅子会员和桌子会员。 椅子会员即流动会员,只能周一至周五过来,来了之后哪有空位就坐哪,如果楼上的办公区没有位置了,就只能坐一楼大厅。桌子会员即固定会员,不管来不来,都会为其保留一个位置。 椅子会员的租金为每月500元,桌子会员为每月2500元。现有的会员都可以免费使用会议室,但如果要邀请其他人来一场“头脑风暴”,则需要支付每人每小时15元的会议设施使用费。 如今,上海大部分创意园区的租金价格大约是每天每平方米3元—5元,以70平方米起租面积计算,租户每月需要支付至少6000元。单个自由职业者和创业者通常用不了这么大面积。相比之下,“新单位”的确颇有吸引力。 而对于“新单位”而言,这一价格恰好是收支平衡。 至于“新单位”未来的故事,不久即将上演的篇章叫“新顾问”。“我接触了很多老外,他们都看中了上海潜在的创意产业机遇和某些可能性,却不怎么了解这座城市的产业政策、商业成本等细节,要么毫无方向跑来抓瞎,要么只能在老外圈子里打听消息。”刘妍认为,这就是“新单位”的新机会。 “新单位”的三位合伙人都从事过创意产业的经营管理,亲力亲为过每个环节和步骤。三年来,通过入驻体验过“新单位”服务的超过200人,通过网络关注“新单位”的有8000人—10000人,他们几乎都是与创意产业有关的鲜活的案例。“新单位”计划将他们统统纳入自己的顾问团。 每个“新单位”成员都可以成为“新顾问”,每个月贡献2小时—4小时,作为顾问或者导师专门为“新单位”社区服务。比如,介绍项目、客户资源或者是提供商业战略、技术咨询和指导,用以解决上述老外的需求或者其他正被某个环节困扰的人。接受咨询的费用打包在办公空间租金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