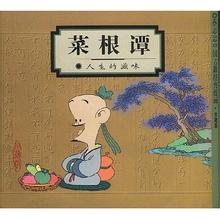○持身涉世,不可随境而迁。须是大火流金而清风穆然,严霜杀物而和气蔼然,阴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涛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内的真人品。
○作人只是一味率真,踪迹虽隐还显。
○贫贱骄人,虽涉虚骄,还有几分使气;英雄欺世,纵似挥霍,全无半点真心。
○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贯。若伪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对人则面目可憎,独居则形影自愧。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优人傅粉调殊,效妍丑于毫端,俄而歌残场罢,妍五何存?
○逸态闲情,惟期自尚,何事外修边幅?清标傲骨,不愿人怜,无劳多买胭脂。
○贫家净扫地,贫女净梳头,景色虽不艳丽,气度自是风雅。士君子当穷愁寥落,奈何辄自废驰哉?
以上这些引自《菜根谭》的语句,似诗,似楹联,也似慷慨陈词……所论及的都是做人的关键——人品,还附带地提到了为文之道。
按照洪应明的认识,成功的文章,不是通过堆砌奇文异字而取得的,而是通过内容的充实和字句的协调来达到的,说到底,就是各方面显得恰到好处,整篇文章有一种浑然一体的整体感。
要达到这种目标,当然要通过具体的写作来实现,这又落实在写作中的各个方面上,如不乱用比喻,避免堆砌词藻等等。
仅就文章中的形容词运用来看,从中国历史上众多的著名文学家到现代的文学大家,典型如老舍,并不主张在文章中运用过多的华丽的形容词,而是提倡一种天然清新而又自然贴切的文风,以免使文章失去了淳朴的魅力,给人以一种华而不实、肤浅卖弄之感,也避免使文章成为形容词的汇编,做到不因词害意,保证文章有充实的内容。
这并不是说为文时就不须讲究艺术的技巧,而是主张我们为文时,不必挖空心思地追求那些多余的文字矫饰,在平淡的文风中追求成熟而又绚丽的效果。
为文如此,为人就更是如此。
春秋时代,越国有一名叫西施的绝色美女,她有心病,在村里总是皱着眉头。
西施的邻里中,有一名叫东施的丑女,每每见到西施的这副让人怜爱的模样,觉得很美。有样学样,她在村里,也学着模仿西施的那种手捧胸口、皱着眉头的模样。为此,村里人见了她,富人是关上了大门,穷人则是带着妻子儿女避开,谁见到她,都是唯恐避之不及。
东施所知道的,仅是皱着眉头的西施的确美,却不知道西施为何即使是皱着眉头,也是美的。
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东施效颦”。
它看似简单,但从庄子经黄庭坚而至今,已被中国人传诵了数千年,可见它包含有深刻而又冷峻的智慧哲理。它所论及的是一个人的形貌,直接地说明了当东施盲目地去模仿西施的形貌动作时,她的作为只会增加她形貌上的丑陋度,使她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事实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东施也不例外,只不过她因一味的模仿而失去了本真,结果是适得其反。
现代人明白了这点,所以,即使是相貌生得有些对不起各位看官,那么,一如流行歌词所吟唱——“我很丑,但我很温柔”,丑是客观,温柔是自然本色,丑加温柔,也是可爱。
形貌尚且如此,讲到人的品质、品格与品性行为,就更是如此。
结合每个活生生的人来论人品,人品就有好与坏、高洁与卑劣、可信与不可信之分,而这些,都通过每个人的各自个性、情趣爱好、行为追求和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体现出来。
在人品问题上,洪应明像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思想家一样,推崇的是本然人品,也就是率真、纯真、本真的人品。
本然人品,人品本然,是不违反个人的自然本性,不被各种外在规则所规定,也不会被各种外在的功利目标所扭曲的。
本然人品,人品本然,是发自内心而又顺其自然地表现出来的,不是矫揉造作的。
论人品的本然与本真,可贵之处也就在此。
所以,是李逵,就不用如林黛玉般地吟诗焚稿、呕气吐血。是林妹妹式的人物,也不必似李大哥那样去挥舞大板斧,为劫富济贫而冲锋陷阵、打家劫舍。
为人至此,那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溪”——“踪迹虽隐还显”,类似诸葛亮那种藏龙卧虎的人中豪杰,就是如此。
为人至此,就能泰山崩于眼前而不眨,就能显出中流砒柱的英雄本色,关于这点,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莫不如此。
至于洪应明所言的“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贯”句,涉及的则是三则故事。
“霜可飞”:道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忠臣邹衍因冤下狱,相传他曾仰天大哭,虽时值盛夏的六月,然而上苍受此感应,竟然六月飞霜,以证邹衍的确是受到了冤屈。元朝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在其悲剧名作《窦娥冤》中,讲述了含冤被判处极刑的窦娥在临刑前,对天发下三桩誓愿,以证明她的确是冤枉,三者之中其一就是引证“飞霜六月因邹衍”的故事,立誓在三伏天时,让天降三尺瑞雪。
“城可陨”:讲的是秦始皇时代,有一名叫孟姜的女子,因思念被征配去修长城的丈夫,千里迢迢地去探夫。她到了长城边,才知道丈夫已因劳累过度而死去,悲忿交加的她,在长城城墙下放声恸哭,她那哭的能量是如此充沛,瞬间即使长城崩塌了一大片。
“金石可贯”:讲的是周朝有一名叫雄渠的射箭能手,一天傍晚,他走在山路上,猛见有一只虎伏在路旁,他马上箭搭弓上,聚精会神,用尽全身气力把箭射出,箭射中了那老虎。但见那老虎既不叫喊,也不翻跳,他心中不免怀疑,走近一看,才知那“老虎”原只是一块石头。由于他射箭时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所以射中石头的箭,已深深没入石头之中,谁去拔都拔不出来。西汉时,著名将军李广也曾有与此相似的经历。
在这三则故事中,前两则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传奇故事,虽涉神怪灵异,却盛赞了人的真挚情感与精神;后一则为史实故事,它阐释了当人能集中精神,气贯长虹之时,就可以创造出平时所难以创造乃至想象的奇迹,也就是“精诚所至,金石可贯”。
可见,人之所以成人,建树起本然的、本真的人品,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否则,一个人倘若因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时时处处隐匿起自己的真面目,靠假面具来装扮自己,结果必是糟蹋了自己的个性,扭曲了自己的性情,从言谈到行为都充满了虚伪的成份和矫揉作态的举止,那么,这种人就只可配称为徒具形骸的伪妄之人,无异于行尸走肉,只会给人留下虚伪可憎的印象,缺乏人格的力量。
当这种人到回首平生往事时,会发现他们最缺失的正是自我的本来面目。所以,头脑中只会留有形影孤单、自怜自愧的痛苦,摆脱不了因虚伪而引致的心理折磨。
显然,这种人不会获得幸福,其人生只可算是失败的人生。
因为他们的一生仅是在演戏,也许他们表演得很美也很得体,但并不能使自己信服,不能蒙蔽眼睛雪亮的人。
这,一如诗人那一针见血的揭示:
请不要相信我的美丽
也不要相信我的爱情在涂满了油彩的面容之下我有的是颗戏子的心(席慕容:《戏子》)退一步说,假如当我们世故到也戴起面具,写文章也到了需要修饰之时,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此而损害了自己的本然人品和文章的朴实。原因在于,本然人品与优秀文章都是容不得虚伪与矫饰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十分强调此点,从要求人保持天然的“本色”、“本来面目”乃至“君子坦荡荡”等等说法,均表明了类似的内容。
借用一个流行词,保持本然,也就是:不“作秀(骚)!”
所以,人活世上,《菜根谭》更推崇的,是一种能保持清标傲骨而又有逸态闲情的人生,是一种可以面对自我、不修边幅、素面朝天的生活。对于清贫之家,洁净在于扫地;对于清贫家之女儿,洁净在于梳头,景色虽不艳丽,而气度同样落落大方,自有风雅。如此,士君子即使是穷愁寥落,又岂会自惭形秽、自怨自艾?
洪应明是在论为文、为人与人品,事实上,举一反三,看世间事物,多如此。
明朝刘元卿曾记录过一个猫如何被某些人形容成“鼠猫”的故事,形容猫的英武,却要用猫爪下的猎物来形容,这正是某些擅于歪曲对事物本性的认识的人所经常犯的错误。此处引用,唯一要明确的是,这个故事绝不是写给猫看的。
这个故事所说的是:
曾有一名叫齐奄的人,十分看重自己所养的一只猫,逢人便夸耀说;“此猫名叫‘虎猫’”。
甲人听后,就给他出主意;“老虎虽算凶猛,但绝没有龙的神奇灵异,请你把它更名叫‘龙猫’吧。”
接着,乙人听后,更进一步进言说:“龙,是比老虎神奇,但龙要飞腾上天,必须依靠浮云衬托,可见云要比龙要更高一等,因此,还是改名为‘云猫’为好。”
但丙人却不以为然,说道:“云雾虽能遮天盖日,但只要风一刮来,云雾很快就被吹散了,看来是风比云厉害,你的猫,还是叫‘风猫’为好。”
而丁人对此论却更不以为然,批驳道:“大风虽能猛烈地刮,但只要用墙来作屏障,就足以阻挡狂风暴风了。风怎能与墙相提并论呢?可见,这个猫还是叫‘墙猫’才合适呢。”
最后一位说客,则另有一说:“各位所讲的都有一定道理。依我看来,墙虽坚固,但只要老鼠在墙上打洞,这墙就会倾塌下来。可见,墙又怎么比得上老鼠厉害?如此看来,此猫还是得改名,窃以为,叫‘鼠猫’最好。”
他们这番谍喋不休的争论传出后,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就嗤笑他们道:“嘻嘻!猫本来就是捕鼠的,猫就是猫。为什么要乱给它起名安号来形容,使它失掉猫的本来真实的面目呢?”
是的,猫如此,人呢?
再,人论猫如此,人论人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