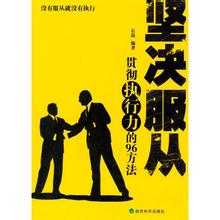
对于大多数企业领导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没有学会执行,而且是没有人向他们正确解释这一点。“一年前,霍尼韦尔前CEO拉里·博西迪和资深顾问拉姆·查兰在《执行》一书中这样说,在中国,《执行》被广泛阅读和讨论。一年后,现在一家国内商学院工作的国外MBA回忆说,她最初被人批评“没有执行力”时很纳闷,后来才隐约明白这种批评背后的意思其实是“不够听话”。
在中国,每一个曾经流行的管理观念都被符号化,或者被简单化为一个很偏狭的含义,或者被泛化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东西。对于“执行”,二者兼而有之。在一段时间里,所有管理问题都被看成执行问题。
执行就是“没有任何借口”式的服从,这恐怕是一个管理理念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曲解。“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知名军事理论专家洪兵说,他是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他认为,执行在军事上就是充分领会作战意图,把事情做对、做出结果。
执行变成服从,一方面可能是自上而下的压力所产生的结果,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它也可能是自下而上产生的。VOLVO卡车中国总裁吴瑜章曾经在公司里遇到这样的情形,有的员工做事时说“这件事这么做是吴瑜章说的”,从而把事情的责任推至上层以逃避责任。
作为一家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吴瑜章认为中西方对执行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一是以“人”为依据,一是以“制度与程序”为依据。他在公司里推行所谓“去吴瑜章化”的做法,即不允许说某某事是他说让做的、他说这样做的,而应是这件事情程序上应该怎样做。吴说,“在执行的时候考虑的只应是原则与程序,不应该有其他的内容。”“(做事)按照管理的程序来,涉及到管理规章的问题,没有好坏、松紧之说,纯粹就是一个执行程序的问题。”
管理的探讨常常被引向更深层次的文化差异讨论,这些差异可能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做事的行为。譬如,中国人设定的人性前提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在设定制度与程序上往往很宽泛;西方的文化传统是完全相反的假设,因而制定严格的制度。在遇到问题时,西方人喜欢对抗,并不掩饰自己;而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奉行的是所谓柔或打太极的道家哲学。
“文化差异都可能影响我们对执行的理解。”方竹说,他现任中国网通集团采购与物流中心副总经理。他举例道,西方采用的是“数字化管理”,譬如麦当劳有多少道程序都是规定很严格的:消毒什么位置、消毒几遍、薯条炸完以后多少分钟没卖掉就必须倒掉,有一整套的规章体系。中国文化讲求“度”,但是“度”这个概念很难量化。
北京大学BiMBA美方院长杨壮教授认为,“文化和组织结构是执行的载体。”他举郭士纳执掌IBM之初所做的头两件事就是改变公司文化和组织结构,郭士纳认为在企业里面就要进行严格的绩效评估,完成了奖励,完不成惩罚。“建立一种向上的文化,在严格的制度结构下面,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杨壮说,“在制度下,人的反应应该是一样的,这样就不会产生执行的差异。”
因此,虽然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说执行就是要建立“执行文化”,但我们首先要做的却是先是强化制度,因为他们所指的是在西方大型跨国公司已有制度基础上的“文化”。
在《执行》中他们所举的案例都是诸如通用电气、霍尼韦尔、联合信号等有着非常严格的制度的大型跨国公司。2004年6月韦尔奇在中国演讲时,当被问到GE有多少名战略规划人员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一个也没有。”这是因为从1970年代开始推行战略规划到现在,战略规划已经成为GE员工的一项基本能力,为了打破官僚性,他才强调总部不需要专门的战略规划人员。这并不适应中国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
方竹结合网通重组过程实际情况分析一个有着执行文化的机构的组建过程,网通集团采购与物流中心是网通重组后由网通集团内抽调人员新组建的部门。方竹介绍说,这个部门组建的过程中,首先强调价值观、理念的统一;第二纪律一定要严明,很多人以前是“总经理”,在新的公司里面要明确自己的职责;第三是明确任务的目标:什么时间完成,然后是一系列的考核,不仅仅凭印象就定一些事情。
设计了好的机制,才有执行,反馈机制是将人员和战略结合起来的执行机制。吴瑜章说,“执行的末梢就是信息反馈,员工应该而且必须把在一线了解到的信息反馈给企业的指挥官。”他特别欣赏海尔的交叉反馈方式,海尔的每个员工都有一个信息反馈的功能,员工之间对同一个信息进行交叉反馈,企业根据这些信息交叉监督。比如说三个人说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个说的与其他的两个不一样,马上就警示可能系统哪里出了问题,当即反馈给领导者重新决策。
领导者是有效执行的最重要的因素,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的研究发现,领导者应遵循这样七条基本行为:了解你的企业和你的员工;坚持以事实为基础;确立明确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先后顺序;跟进;对执行者进行奖励;提高员工能力和素质;了解你自己。在有了制度之后,执行的要点在于此,制度的建立也需要领导者来推动,在执行的过程中也需要他们的推动以进行必要的改动。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