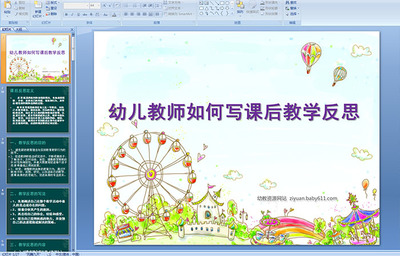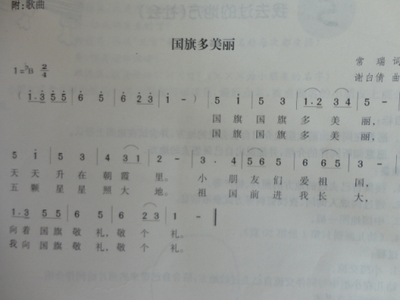美国西海岸,夏季日脚长,到了七点三刻,天还没黑下来的意思。太阳早已沉没,余晖也挥霍尽了,仅存的光明,被老天爷省俭地用着。我在街上,一边散步一边和住在休斯敦市郊双湖畔的朋友通电话。他那边已是晚间近10点。我好奇地问,“双湖”有没有渔火?他笑了,因为我的问题太天真,告诉我,不过是小不点的人工湖,也许没广州流花湖大,不乏在岸边垂钓的,偶尔有洋人划小艇或者独木舟,都是用卡车拖来的,玩完了,便抬到车上运走。 他问我,此刻旧金山的街道热闹不。我说我这个滨海居民区,总是冷清清的,除非有电车隆隆开过。我每天在街上溜达,也常感奇怪,为什么如此阒寂?今天是星期天,也过了下班时间,尤其寂静,也难怪,这个周末,连下星期一的国殇日,假期共三天,许多人趁汽油降价,驾车远游去了。但不管哪天,居民区这个时刻的基调是冷。暑气断乎没有,外出乘凉、戏水更没有。我脚下的,是遍布酒吧、餐馆、足浴店、咖啡馆、柔道馆和芭蕾舞学校的他拉威尔大街,从窗户和大门透出晕黄灯光的所在看进去,就餐喝酒的客人并不少,可是,我在街上,目光所及,只有零星的遛狗者、散步者和回家的人,还有,没开灯的汽车。

通话时,我告诉友人一新奇发现:近来在这一带散步,不下十次看到两位中年中国女子并肩而行,衣着常常变换,但颜色和式样大致相同,昨天是红色短大衣,今天是长长的白羽绒服。和我擦肩而过时,听到她们说普通话。她们只局限在一个街区内的一段人行道,来回多次,一路热烈交谈。我揣测,她们可能是新加入某诗社的诗人,不然,是刚刚开始或者结束一段婚姻的同病相怜者。看多了,又猜她们是一家“健康中心”的从业员,这“中心”没有中文招牌,只在玻璃门上标出英文名字,没有具体内容,天晓得是如何教人“健康”的?如果我的好奇心更加丰沛一些,当推门进去,问问在电脑屏幕前坐着的女孩,请她介绍“健康”项目,可是不想让单纯的散步无端染色。我对着手机说话时,两位散步者一起推开“健康中心”的门,瞄了瞄,离开了,又是一路交谈一路溜达。我大乐,向友人揭开谜底:是一家按摩店,散步者是技师,客人没来,她们便以散步解闷,怕客人打电话或进门,不敢走远,每隔十来分钟和接待员打个照面。为了终于看到寂静街道的生动一面,我高兴起来。 为了不影响友人就寝,我挂了手机,往回走。暮色沉沉而降,林荫道带上黑影。前天被大风刮倒的花旗松,被锯成许多段,搬走了。花旗松站了上百年的地方,留下一角格外敞亮的天空,那是死亡带来的空白。 到家之前,隔街看到,贴邻的门前,一个白人斜靠电线杆,埋头读一本书。这个时刻,天色已暗,除非视力极好,小字难以看清。可是他行。我知道他在读什么。今天早上,我外出买报时,看到电线杆下的纸箱子,里头放着十来本书,多半是科幻小说,也有一些心理学方面的,我逐本翻了翻,放回箱内,掉过头对好施舍的印度裔邻居,在心里说,谢谢你,可惜不对口味。刚才我又路过箱子,看到书已减少到一本,于是,进行第二次推测:这位好学之士刚好路过,出于好奇,捡起箱内的书,一翻,被吸引住,坐下来,读个天昏地暗。他的上方,有黄得叫人想起咖哩饭的灯光,那是书的前主人的餐厅透出的。我定神看汉子手拿的书,书脊黑白各半,噢,对了,就是那本《被切割的人生》,我记得清楚,是刚才翻得仔细的缘故,作者乃华盛顿邮报记者俄尔萨?瓦里苏,由CNN主播吴露夫品题,内容是三位名女人的访谈录。 在清冷的街头,在离下一棵参天大树不远的人行道上,就着黯淡下来的光线读书的,是谁?流浪汉吗?也许是,否则,他该把书带回家,在客厅从容地读;不过,我还是把他当做书呆子吧!伟大的呆子,为了爱书而在冷风里,靠着并无暖意的木杆,头上的电线,虽曾站过的鹧鸪,以凄恻的“行不得也哥哥”引发我古典的乡愁,但此刻连海鸟也不来栖息。我非要把他定性为“妇女问题专家”不可了,否则,对不起那本书。在天色全暗之前,街灯亮了。橙黄的光慷慨地铺在读书人伸进人行道的腿上,街灯终于成了他的台灯或床头灯。 我被感动着,生怕扰乱了读书人,不敢迈开大步。门旁的山茶到花信的末端,凋谢的和盛开的密匝匝地覆盖了树叶。暗红的花,在街灯下,有如壁炉里半烬的松柴。我那在远方双湖畔忙于画画和作诗的朋友,该已在梦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