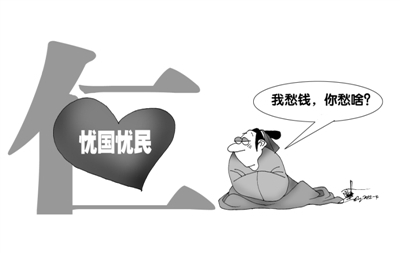迥异于华为、中兴通讯一城一池逐步推进的方式,TCL则是以跳跃式的并购匆忙进入全球的大舞台,如何在竞争中获得对国际市场的认知对TCL来说才刚刚开始。 1月12日,深圳威尼斯酒店。TCL集团第一次如此奢华而大规模地宴请“国际化”后的第一拨海外客人———150名印度经销商,深圳只是这群印度人的第一站。据说,在TCL安排的日程中,还有国内其它几个大城市的旅游。
TCL今后将会把这样的行程安排当成日常的作业,让更多的老外认识:这是中国,这是中国的TCL。这种做法有点像深圳另一家同样行走在国际化征途中的公司———华为,为了获得海外运营商的迅速认同,华为多年来采用的一种快速而有效的做法就是邀请客户到中国旅游。但不同的是,在思科一案后,华为这方面的公关成本已经开始大大降低,“一个让思科畏惧的华为”比任何表述都更能建立客户的信任度。
如何在全球产业链条内成就为一个成功的调度者?如何把全球的资源调配到最佳?迥异于华为、中兴通讯一城一池逐步推进的方式,TCL则是以跳跃式的并购匆忙进入全球的大舞台,如何在竞争中获得对国际市场的认知对TCL来说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华为、中兴海外市场的拓展来自于长达十年日积月累,TCL截获汤姆逊、阿尔卡特等传统欧洲品牌几乎只在一夜之间,由此带来的最大差异是:华为、中兴在全球各地区拥有用时间和人力累积起来的分公司或者办事处,并且这些海外机构与国内母体之间早已水乳交融,而TCL从汤姆逊、阿尔卡特身上接手的全球生产、研发机构仍然只是散落各地的棋子。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国际化路径,前者缓慢推进但动作稳健,后者动作神速但注定要险象环生。
国际化暴露的组织危机国际化对TCL的最大考验是什么?
按照1+1=2的理想公式,TCL-汤姆逊公司成立后,其全球彩电销量据称可以达到1800万台,而目前全球彩电冠军三星的业绩是1300万台;吃下阿尔卡特手机的全球业务后,TCL手机的生产规模也已进入了全球前五名。一副转瞬间从小孩长成大人的皮肉,如何才能迅速拥有与之相匹配的骨骼?
TCL—汤姆逊合资公司TTE首席财务官Vincent Yan曾在合资公司成立多个月后对海外媒体表示:“合资公司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正式运营之后,我们发现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要远远超过预想。”
诸如中法双方的工作人员语言不通、公司奖励机制难产以及欧洲工厂运营支出过高等等细节问题开始纠缠TCL管理层的神经。据当时的外电说,对海外市场操作经验的空白甚至让这些进驻法国的中国人一时间不知所措,“中国方面的管理人员对于美国零售商的强劲需求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同后者直接开展过合作”。
也许语言并不是最有挑战性的难题,更富想象的问题在于,TCL同汤姆逊的合作并不是习惯中的西方企业为成本控制所需,将生产等业务转移到中国,事实上,TCL几乎合并了汤姆逊位于全球的电视生产业务,其中包括在中国、法国、墨西哥、波兰、泰国以及越南的工厂及研发部门。
这可能是对TCL2001年完成改制后的又一次组织架构的考验。如何让TCL的血液以最快的速度渗透到全球各地的枝叶中?
在去年6月李东生宣布的大规模人才招聘中,TCL似乎在力图转变这种供血不足的局面。TCL宣布在全球招聘人才,其中高级职位占到了近40%,研发型人才占到了近70%,TCL汤姆逊项目和移动通信的人才需求占60%。但是正如TCL集团副总裁、TTE公司CEO赵忠尧当时所说,全国这么多外资企业以及大型国内企业,其中有多少适合TCL集团招聘要求的人才,他数都数得过来。
而仅仅是解决人就足够了吗?
有国外媒体评论说,在同汤姆逊合作之前,TCL是中国最早进行产权改制的国内大企业之一。因此该公司同汤姆逊,以及另外两家国外企业———法国的阿尔卡特以及日本东芝公司之间的合作是否成功,对于中国国企改制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TTE大获成功,中国政府就有可能对更多国企进行改制,如果失败情况将会截然相反。在海外人士看来,TCL当时的国企业改制只能解决了劳动力在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问题,而距离国际化后的公司治理还有多远距离仍是一个未知数。
1995年,TCL开始已经小范围地实施国企改制,1996年底与惠州市政府签订资产授权经营协议之后,在政府直接推动下,TCL员工持股计划开始大规模实施。协议的基本内容是,集团到1996年底资产全部划归市政府,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能低于10%,如果增长超过10%,管理层和骨干员工可获得一定比例奖励,并按净资产购买公司股份。与此同时,TCL鼓励员工用现金购买公司股份,当时有超过2000名员工出资1.6亿元参股。

通过与政府协议的授权经营,至2001年,TCL吸纳包括飞利浦、东芝等在内的五家海外战略投资者以及TCL公司管理层持股,使当时的TCL管理层持股达到25%。
通过那一次改制,TCL快速地刺激了属下干将的积极性,同时也在TCL内部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富豪俱乐部。至2004年初TCL集团整体上市时,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TCL集团中的股份已减持至25.22%、TCL集团工会持有9.10%、社会公众股38.45%,而李东生及其属下爱将袁信成、杨伟强、万明坚则分别持有数额不等的股票,当时有人根据他们的持股数计算,各高管身家均在几千万到上十亿元不等。
当长虹、海信仍在试图越过管理收购的樊篱时,TCL已经充分享受到了股权激励的妙处。虽然吴士宏在IT低潮中失利让TCL赔出去一个多亿,但是万明坚在此后的几年中也实实在在地为TCL赚进了十几亿元的净利润。
如果说改制后的灵活的组织架构赋予了TCL灵活的机制,并使TCL从一个生产电话机的公司演进为彩电、手机、电脑三大主业共进的集团化运作的话,当时的机制也同时衍生了至今仍挥之不去的另一种隐性的特质:分而治之。
从分治到集权早在90年代中期以后,彩电业在TCL集团始得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势,良好的股权激励政策,集团的放权,让袁信成、胡秋生一批干将快速与彩电业同时崛起;同样方式后来还诞生了主管PC业务的吴士宏、杨伟强,以及手机业的狂人万明坚。
但是几度轮转,在以成败论英雄的潜意识主导下,TCL施行的是一种分而治之的体系,各大事业部原则上统领于集团,但在行销体系、财务结算甚至公关策略上都独立运转,仅从手机业的快速崛起看,TCL管理上的独立性让不同的产业分支获得了最大的个性发挥。
这种特质从各大事业部举行的产品发布会或经销商会风格上就能窥斑见豹:彩电及电脑产品部的发布会大都讲究时尚与温情,只传达品牌的理念,不涉及竞争对手;而通讯产品则显然要直接得多,常有预先设计的拳击赛表演,以TCL胜出的结局,预示对手的挫败,万明坚也时常为诸如此类的活动冠上“英雄天下”之名。内敛与狂放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实际上正是来源于各路诸侯风格的迥异。
无论如何,尽管路数不尽相同,但是TCL的彩电、手机两块主业却实实在在地分别冲进了国内企业的领军之列。
但是同样的模式能否成就TCL的跨国梦想?过往的TCL各路诸侯还能一如既往地所向披靡吗?
有意味地是,在汤姆逊、阿尔卡特两起重大并购案中,担纲主演的并非TCL原本两块主业上的元老们,而是另两位有海归背景的人物---郭爱平和严勇。刚刚接替万明坚出任香港上市公司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2618.HK)董事总经理的郭爱平为2001年后加盟TCL,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工程技术经济系统学博士学位,曾经任职于声名显赫的IBM、安达信等公司。
TCL内部有一种说法认为,业绩下滑、功高盖主确实是导致万明坚下课的原因,但万个人的性格特质对于TCL国际化路程的确存在相当大冲突:万明坚是TCL诸侯文化表现的极致,他在移动公司无所不在的影响使TCL手机业务难以获得更为开放的理念,更多熟悉国际化运作的人才、开放的意识无法在既有体系上获得实现。
而万明坚的离开显然更能成全TCL的国际化人才之梦———万的离职,郭爱平的上任或许正是TCL移动公司两个时代的交接。
相似的一幕也曾经发生在去年TTE合资公司成立之前,原计划的合资公司CEO被临时换上了赵忠尧,尽管具体原因外人难以知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TCL的一拨“老人”正在TCL的国际化征途之初快速地隐退。
与郭爱平在手机业务上的崛起相呼应,另一位海派人物严勇已于去年3月在任命为TCL集团副总裁后,又被任命为香港上市公司TCL国际的执行总经理。
“TCL正在收权。”TCL内部人士说,去年以来TCL已经着手将各个分公司的市场宣传、人事、财务等权力收回到集团的掌控之下。对于正在抱团出海的TCL而言,分散的组织架构势必在大大削弱争夺更大市场的力量,而历史上曾经成就了TCL辉煌的分权治之的模式,正在时间的冲涮下再次回归到集权时代,而人事的快速变迁恰恰是TCL从分治到集权的最大表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