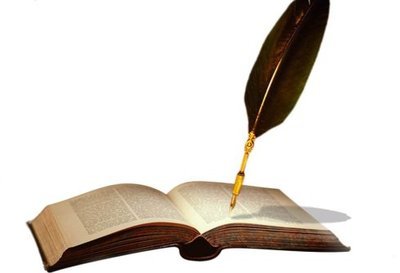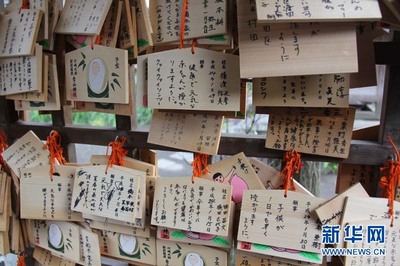从偶像崇拜透视青年文化消费
余开亮
内容提要: 青春偶像作为青年文化的代言形象及年青一代的崇拜对象, 自身有着很多值得探讨的特征。文章从形象包装、明星轶闻、偶像崇拜以及青春舞台四个维度对偶像形象进行了描摹, 并试图通过青春偶像来透视青年文化的形式、内容、消费心理以及功能等诸多特征。
一、形象包装与青年文化形式法则酷(cool) 曾被评为十大恶俗流行语之一, 但正因其恶俗, 才显其格调。(《恶俗》与《格调》皆为标明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情趣的两本书), 也才恰如其分地描摹了青春偶像的形象特征与青年文化的形式法则。
青春偶像是酷潮流的形象代言人。在青春偶像酷形象包装中蕴涵着偶像与其追逐者(主流为青少年) 之间的良性互动。正因为青少年一代对酷的时尚消费, 才有了明星的争相扮酷, 也正因为有了明星们的酷装扮, 才引导了酷文化消费的时尚潮流。所以酷本质上是商业时明星制造的一种形象包装, 是商业竞争对商品(明星在消费性上是一种商品) 外观进行的刻意设计, 是为了更好地吸引消费者的一种市场策略。而在市场循环机制较为健全的现代社会中, 青春偶像的形象包装与青少年的消费心理达到了良好的契合。酷是一种反叛, 它切合了年青一代对家长、老师与社会的逆反心理。因而, 《古惑仔》里郑伊健饰演的铜锣湾黑社会老大陈浩南--酷!《还珠格格》里赵薇演的小燕子--酷! 怒泼记者、我行我素的谢庭锋--酷! 酷是一种个性, 它满足了青少年彰显个性的心理需求。高仓健的孤傲、迪克牛仔的沧桑是酷, 姜育恒的忧郁、张宇的苦情也是酷。酷是一种装扮时尚, 它迎合了年青一代从众的文化消费心理。王菲万辫如帘、色彩飞扬的发型是酷, 安室奈美惠的寸底“松糕鞋” 也是酷;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更何况正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年青一代。各种类型的帅哥靓妹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 使他们产生一种遥远的亲和感与情感依恋。而明星也刻意迎合消费者的这种浪漫幻想。荧屏里的频频曝光, 舞台上的款款亮相, 写真集的青春展现甚至挑逗性表演都旨在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注意力。明星们的这种视觉形象极大限度地调动了年青人的潜意识, 刺激了他们的消费欲望, 使整个商业巨轮越旋越快。正由于明星是市场机制包装而出的完美化商品, 是按照一定类型予以生产的, 就不可能永远满足青年的消费品位。因而明星的更新换代速度是非常快的, 文化工业会不断地推出新人来供人们消费。所以, 明星前赴后继, 时尚勇往直前! 形象消费是青年文化消费的主要方式, 偶像明星作为青年文化的代言形象, 其酷包装的背后折射出了青年文化本身的形式法则。青年文化外在形式与明星形象包装如出一辙, 它也以抢眼的色彩(图像化法则) 与诱人的线条(欲望化法则) 营造了满足青年心理的消费文本。人类已经进入一个读图的时代, 各种商品都通过感官的冲击来满足人类消费的需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各类文化的平面化已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潮流, 在铺天盖地的图像面前, 消费者会更加拒绝思考。电视散文、M TV 、泛滥的街头广告、形式花哨的书籍、图片化的杂志、套红的报纸以及搞笑与煽情结合的影视剧等都象快餐一样满足着人的即时饕餮。与偶像明星的性感包装一样, 青年文化也对欲望化叙事法则运用得恰到好处。这类文化商品强化观赏的效果, 给年青群体提供了一幅感性满足的全景图画。流行歌曲的情爱追逐、各种刊物的明星剧照、影视节目若隐若现的床上镜头以及小说叙事的性爱描写等都对欲望化场景进行了强有力的表达。在这里, 青年文化商品的批量生产与消费者“过把瘾就扔” 的心态造就了市场价值规律的完美运作, 青年文化的经营也因此而如火如荼。
二、明星轶闻与青年文化内容属性
随着中国娱乐业的发展, 娱乐新闻成为各大报刊杂志网络站点吸引读者的极大卖点, 各种有关偶像明星的趣闻轶事充斥报端, 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偶像明星作为商业时代的新神与青少年生活的幻觉符号, 他们必定是众多眼光的聚焦点。但偶像明星又是现实存在的人, 他们象普通人一样每天都面对着世事纷扰。这样, 有关明星们的各种生活轶闻也就引起了青少年的极大关注。青少年对偶像明星的日常关注一方面满足了自身潜意识的窥淫癖心理, 另一方面也在这种可感知的偶像行为中分享了崇拜对象散发的微弱光芒(这种光芒可以使青年人感受到新神的沐浴而获得某种依托) 。年青人对偶像明星生活轶事的市场需求必将形成强大的“星闻” 效应, 这种“ 星闻” 效应借助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也就促成了娱乐报道的繁荣。明星成为不折不扣的商品, 他的任何属性都被拿到市场上进行了贩卖。因此, 明星的各类外在特征、性格爱好以及婚变、绯闻等情况都成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素材。明星的自传也几乎成为新时代的圣经。偶像明星所居所到之处总有大量娱记相伴而行, 而“狗仔队” 对明星则形影不离。一些娱记会极尽添油加醋之能事, 或盲目夸大其辞或无中生有地制造许多偶像明星的绯闻轶事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一些以报道娱乐业界动态为顶梁柱的报刊杂志、网站、卫视台、广播台等新闻媒体也借助其强大的“探密” 娱记而使经济效益扶摇直上。明星轶闻的轰动效应充分暴露了青少年猎奇的心理, 只不过这种猎奇心理仅局限在自己所关注的偶像明星身上。而整个青年文化产品的内容构成则把这种潜意识的窥淫癖发挥到了极至。以1990 年“ 毛泽东热” 为发端, 各种领袖传奇、高层政界斗争、文革秘史等书籍(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共和国风云实录》、《中南海珍闻录》、《文革冤案与大平反》等) 对中国当代史进行了“政治揭密”。以阿来的《尘埃落定》为最成功代表的文学样式或真或伪地展示了中国民俗风情(如《妻妾成群》、《爸爸爸》、《怀念狼》等) 。以贾平凹《废都》为典范的注重性爱描写的小说极大满足了人的窥淫癖(如《白鹿原》、《上海宝贝》等) 。而以张艺谋为领头人的东方情调(对国外而言) 或异域情调(对国内而言) 电影则在视觉效果上再现了民族传统的某些仪式与地域特色(如《红高粱》里的“ 颠轿” 与“ 酒誓” 仪式、《菊豆》里的杨家染坊、《洗澡》里陕北姑娘“ 洗澡出嫁” 与西藏“ 朝拜圣湖” 仪式) 。这些文本内容都恰当地迎合了年青一代的猎奇心态, 实现了艺术与市场不露斧斫的结合(在商业化时代里, 很多知识分子也实现了市场转型。就受众来说, 他们的作品与其他消费品并无二致。这有点象罗兰8226;巴尔特所做的那样: 把写作比作勾引, 把阅读比作色欲) 。至于其他一些关于艳情凶杀、色情乱伦、奇闻怪志等的各类体裁作品、泳装Show 、选美比赛等则更是直露地去迎合人的猎奇心理。对一个封闭保守的国度而言, 所罗门魔瓶一经打开, 潜意识暗流就会汹涌而出。在商业利润驱动下, 迎合潜意识的文化产品无疑会以强大的生命力活跃在市场上。三、偶像崇拜与青年文化消费的虚拟性心理
偶像崇拜是个心理学命题, 指个人对幻想中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与情感依恋, 但这种幻想被过分的强化或理想化。其中影视歌红星占据了青年偶像崇拜的主导位置。偶像崇拜导致了对偶像的过分认同与依恋, 由此而生的过于理想化或浪漫化的遥亲感会使追逐者对其偶像想入非非, 做出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浪漫幻想是偶像崇拜最直接的心理反应。它突出表现在对偶像对象的迷恋中充满了情爱甚至性爱的幻想。我们能从追星族对其青春偶像的狂热举动中可窥一斑。成龙在日本的一次演唱会上, 被日本影迷索取纪念物, 在狂热的fans 举动中, 成龙被“剥夺” 得只剩一条三角裤。在黎明北京下榻的酒店前, 总会有成批的歌迷与影迷在耐心等待, 黎明一出现就会有勇气可嘉的女fan 突破重围去一亲“ 芳泽”。在众多的追星族心里, 自己的偶像不但是个绝对英雄, 而且也是自己情感的一种依靠, 他Π她已经成为幻想中的情人。正因如此, 某个著名歌星或影星宣布自己结婚时, 就会使某些歌迷或影迷痛不欲生, 甚至意欲自杀。除浪漫幻想之外, 满足虚荣也是偶像崇拜的一大动力。对很多青少年来说, 亲眼见过某某明星或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各类明星档案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是“另类” 的标志之一。所以这些人会不惜代价地参加事关自己偶像的演唱会、新闻发布会、歌迷会等活动以及购买自己偶像的影碟、CD 、卡带与剧照等物品。这些都是追星族向其同伴炫耀的资本。无论偶像崇拜是出于浪漫幻想还是满足虚荣心, 其共同点都是实现情感的虚拟性满足。偶像作为一个幻觉符号、一个“镜像” 使其追逐者在想象中确证自己。追星一族也正是在这种对自己青春偶像的幻觉里完成着一次次情感虚拟的体验。而这一情感体验过程正是青年文化消费的重要特征。偶像崇拜的虚拟性情感满足了实际上在某种程度填补了神灵缺席下青年对意义的需要, 它给“ 飘一代” 的青年人群带来了些许慰藉。正如约翰8226;列侬说的, 他比上帝还有名。在神灵退位历史权威走下神坛的新时期里, 偶像明星是一种神灵的代用品。它完成着对青年人日常生活的解释, 给年青群体铺设了一条世俗化的朝圣之旅。但是在商业时代里, 偶像崇拜是脆弱不堪的, 它只是文化市场循环机制下的一个环节。青年对偶像的迷恋只能是浅层次碎片式的精神满足, 是一种意义寄托的当代戏拟。然而这种商业制造式的虚拟性情感满足正体现了青年文化消费的意义所在。营造一个虚拟氛围让大众情感得以释放是青年文化的重要促销手段。消费文本的或快乐或悲伤、或深情或搞笑的因子都是经由生产程序制造出来, 迎合着脆弱而多愁善感的现代都市人。而人们也正在这种“制造程序” 里进行着虚拟性消费, 体验着情感的虚拟历程。人们可以在爱情歌曲中品尝爱情的五味果, 可以在卡拉O K 演唱中寻找表演的感觉, 在武侠小说、影视里体验身怀绝技、浪迹江湖的侠客情怀, 在游戏机前感受指挥官的纵横捭合、运筹帷幄的雄才伟略, 在数字电影的电脑合成特技中经历着“超现实” 的眩晕。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虚拟生存更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网络聊天里的谈情说爱、电脑门诊的求医问药还是电子商务的普及运用, 都使商品消费进入了一个虚拟时代。青年文化正是通过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消费品满足消费者的这种虚拟性情感消费。它充分利用了形象魅力崇拜能暂时满足青年情感慰藉的消费意义, 制造出了迎合青年消费心理的各类商品。年青一代也正是在这种平面化图像化的文化产品消费嬉戏中, 或者暂时忘却了对意义的追寻, 或者瞥见了意义的瞬间惊鸿。四、青春舞台与青年文化的娱乐功能
舞台是青春偶像与大众交往的主要场所, 它延续了中国古代“ 台” 的部分功能, 成为现代新神的布道场和祭祀坛。只是这种布道和祭祀的内容、形式、心态与古代截然不同, 在青春舞台上, 古代灵台祭祀的神秘庄重已荡然无存, 娱乐性成为其绝对功能。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大型演唱会上, 随着明星们的陆续出场, 中国最高学府的那些年轻人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 随着音乐的节奏左右摇摆。摄影镜头所到之处看到的是莘莘学子的各种痴迷状, 其中还伴随着女生兴奋的高声尖叫。在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 的演播现场, 小学生高举着“ ×× 我爱你, 就象老鼠爱大米” 的横幅标语在镜头前欢快地摇晃不已。这就是偶像明星的魅力。可以穿透学识与年龄的界限, 直达人性深处, 让人放浪形骸, 实现精神的极大宣泄与愉悦。疯狂无忌的明星表演、铿锵有力的音乐节奏、调侃戏谑的说白、绚烂刺目的灯光效果在青春舞台上汇集一起, 可以极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游戏本能, 使人暂时忘记生活中的烦恼与不适, 达到身心的极大放松。正如崔健唱的“ 我们有了机会Π就要表现我们的欲望Π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青春舞台的娱乐功能给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宣泄渠道, 维护了人的身心世界的平衡。这种娱乐减压功能也是青年文化的主要功用。在日益图像化与平面化的文化产品面前, 嬉戏娱乐成为青年文化消费的主要功能所在。许多青年文化产品的制造仅是为了满足人的身心娱乐与减压要求。我们可以从受到人们极大欢迎的一些纯粹搞笑的文化产品里看出这一点。流行的都市笑话、火爆的贺岁电影、戏说的历史剧、喜闻乐见的相声小品、令人捧腹的漫画等都由于其独有的搞笑噱头而令人瞩目。其中, 香港影星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把青年文化的娱乐功能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凭借其对搞笑噱头的恰当运用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大学生们更是对他的电影推崇备至。周星驰电影里的经典对白已经成为当代很多大学生的口头禅。一部《大话西游》就几乎影响着这一代大学生, 成为学子们百看不厌的经典之作。看看水木清华BBS 上的有关周星驰的讨论以及《大话西游宝典》的热销情况就可见一斑。而青年人也正在对这种文本的不断消费中, 维持着身心的平衡, 保持着快乐的心境。参考文献:
岳晓东:《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异同分析》,《青年研究》, 1999 年第7 期。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 作家出版社, 1996 年。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邮编: 100872)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