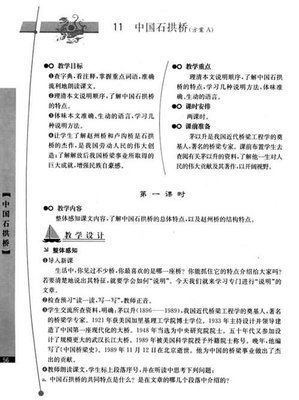高科技垃圾引发的话题
2002年2月25日,美国西海岸的两个环保组织——总部设在西雅图的巴塞尔行动网络[Basel Action Network (BAN)]和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 (SVTC)]发表了其联合撰写的长篇报告《输出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垃圾》(Exporting Harm:The High-Tech Trashing of Asia)。这篇被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路透社(Reuters)等世界各大通讯社所以及BBC、CNN、ABC等所摘录报道的50多页的报告用大量的图片、录象以及实地取样化验分析数据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正在向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转移高科技垃圾,并在当地造成难以逆转的环境生态灾难。
题图:贵屿镇电子垃圾堆上玩耍的儿童(图片来源:BAN)报告详细介绍了电子垃圾重灾区广东潮阳贵屿镇(China: The Story of Guiyu)的情况。始于95年的这项产业,使贵屿镇雇佣了十几万来自安徽、湖南等地的民工,每年处理逾百万吨来自美国、日本、南韩等地的电子垃圾。由于处理手段极为原始,只能通过焚烧、破碎、倾倒、浓酸(王水)提取贵重金属、废液直接排放等方法处理,造成了非同寻常的生态恶果。对河岸沉积物的抽样化验显示,对生物体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钡的浓度10倍于EPA(美国环保署)认定土壤污染危险临界值,锡为152倍,铬1338倍,铅为危险污染标准的212倍,而水中的污染物超过饮用水标准达数千倍。由于地下水源污染的不可逆转,贵屿镇现在不得不从30公里以外的地区买水饮用;大比例的呼吸道疾病,大面积的肺炎流行,各种癌症及不明病症频发;甚至一部分从事废品拆解的女工分娩时羊水呈墨绿色,降生的婴儿皮肤漆黑一团并很快夭折。许多因垃圾处理富起来的贵屿人纷纷迁离贵屿。
更为糟糕的是,贵屿现象正在扩散,就近而言,每天有上千吨的废旧电脑发送到清远市的龙塘镇,这里正在形成新的贵屿;远的已至湖南以及其他一些内陆不明地区。
就在BAN与SVTC报告发表的同一天,《电脑报》刊登了对浙江台州地区电子垃圾的暗访报道。作为走私进口电子垃圾大规模拆解处理及集散地,台州的问题同样是触目惊心。至此,中国高科技垃圾重灾区才渐渐浮出水面。
贵屿镇就是借助于这样的工具从30公里以外的地方买水(图片来源:BAN)贵屿镇随处可见的电子垃圾处理手工作坊(图片来源:BAN)2002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重申我国将采取三大措施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越境转移,禁止进口污染环境的电子垃圾。此前,国家环保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曾联合发文,明确规定自2000年4月1号起,禁止进口废电视机及显像管、废计算机、废显示器及显示管、废复印机、废摄(录)像机、废家用电话机等十一类废电器。然而由于监控不力、地方保护等众多原因,仍然有大量的电子垃圾通过夹带走私或者直接走私源源不断的流入我国,只不过由原来的公开变为半公开及隐蔽的行为,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大大小小的港口为这一走私提供了便利。据BAN与SVTC报告引用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研究结果估计,2002年美国约有1275万台电脑报废,其中80%也就是近千万台的电脑垃圾流入亚洲,而大部将进入中国大陆。
电子垃圾的一片谴责声中,我们对自己产出的高科技垃圾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每年电脑新增销量上千万台,未来5至10年的年增量更被业内人士估计为25%左右,当前旧电脑的淘汰量每年估计为500万台以上,并且随着液晶显示器的出现并逐渐成为市场主流,传统球面显示器电脑的淘汰速度将会加快;据最新统计我国电视的保有量已近3亿,以及天文数字的其他家电也逐渐进入更新报废期。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国自己每年产出的高科技电子垃圾也将成为巨量数字。
对浙江台州的调查我们已经已经发现了大量来自国内的电子垃圾(譬如福州大学淘汰的计算机)。所以仅仅靠堵塞渠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电子垃圾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留给我们的只有理智的面对而不是逃避。为什么电子垃圾流向中国等亚洲国家而不是其它?
美国向中国等亚洲国家大量输出高科技垃圾,除了美国没有在限制发达国家将有害物质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巴塞尔公约”签字(美国由来已久的自私本性)外,据BAN与SVTC报告分析,亚洲国家低廉的工资、普遍缺乏环保标准以及相应的有效法律体系保障是两个重要的原因。电子垃圾真的是遭人唾弃的废物吗?
在这里我们必须纠正由于某些媒体对电子垃圾造成严重恶果的报道给公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不经意间,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电子垃圾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不正确的处理方式,或者说人为的原因,电子垃圾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人祸而不是其他。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电子垃圾而言,只有显示器和线路板,回收处置需要较高的工艺,回收不当将造成环境污染。以废计算机为例,由于铜、铝、钢铁、塑料等占其的90%,如果是以手工方式拆解和分拣,不涉及化学过程,不仅不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有相当高的资源回收率。笔者认为,真正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电子垃圾处理问题,不是技术,不是投资,除了国家严格的环保要求标准之外,作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让企业难以承受的居高不下的人工成本才是根本原因。
我国是自然资源人均占有极度匮乏的大国,然而却具有源源不断的巨量优质低价劳工储备,这一切给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财富化提供了巨大的需求与条件。在对洋电子垃圾的一片喊打声中,在国家自上而下对洋电子垃圾的封堵之下,我们是否冷静审视,寻找对于尚处雏形的我国环保产业而言所蕴藏的巨大机会?不仅是对电子垃圾,在对整个垃圾处理产业审视之后,我们不无遗憾的发现,我们在此有着太多的误区,我们正在做着许多错误的事情而不自知。因而我们必须了解外面的世界,进而反思我们的行为。
垃圾电厂与二恶英困局
实际上,据国家环保总局的数字,我国固体废物的环境污染,最大的还是生活垃圾和工业废物。目前,生活垃圾年产量约为1.2亿吨,工业固体废物8亿吨,其中化学品等危险废物近1000万吨。由于缺乏有效处理,我国历年的垃圾存量已超过60亿吨,全国660多个城市中有2/3处于垃圾包围之中,用垃圾围城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由于传统的填埋与堆肥处理方式有极大的缺陷,众多的城市不得不纷纷寻求新的解决办法。
日本东京MINATO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这些新办法中,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垃圾焚烧发电。自1992年深圳建成我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以来,已有上海浦东、宁波枫林、温州东庄等多座垃圾电厂在中国建成运营,另外北京、广州、杭州、天津等十余座大城市的垃圾电厂建设也相继开工,几十个中小城市的垃圾电厂处于拟建或项目前期运做,另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垃圾电厂纳入议事日程。
丹麦哥本哈根垃圾焚烧工厂我国政府出台的相关优惠政策客观上也为“垃圾发电”推波助澜。如在税收方面,于2001年1月出台了对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生产的电力实行“即征即退”的增值税政策;在融资方面,要求银行优先安排大型垃圾发电厂项目的建设贷款,国家给予2%的财政贴息;另外,在电力调度上保证垃圾发电厂满负荷发电,并给予优惠的售电价格;各地方政府也分别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
媒体也不甘落后。大量有关兴建垃圾电厂的新闻报道与评论说明文章见诸报端,有人引用国家计委的统计数字兴奋的推算,我国即使只有20%~30%的垃圾用来焚烧发电,所造就的设备需求就达几百亿人民币。确实,垃圾电厂的投资动辄上亿元:上海浦东垃圾焚烧电厂投资6.7亿,宁波枫林一期投资就达4亿元,天津垃圾电厂投资5.7亿。由于纸上测算的巨大社会与经济效益,由于环保及其衍生出来的种种巨大压力,几乎在一夜之间,垃圾焚烧电厂及其相关产业成为我国新的投资热点。

维也纳施比特劳垃圾焚烧站
然而我们不能不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85年美国就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我们的近邻日本1998年末永久或短暂关闭了2000多座工业废物焚化炉,到2000年7月,全日本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即使是垃圾问题极为严重的贫穷的菲律宾,也颁布了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禁令。
导致各国政府纷纷立法关闭及禁建垃圾焚烧设施的直接原因是人们发现在垃圾的焚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其中最为危险的当属被国际组织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中毒性最强的二恶(DIOXINs,DXNs)。二恶英主要是由垃圾中的塑料制品焚烧产生,它不仅具有强致癌性,而且具有极强的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其对人类的远期危害远比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严重。这种比氰化钾毒性还要大1千多倍的化合物由于化学结构稳定,亲脂性高,又不能生物降解,因而具有很高的环境滞留性。无论存在于空气、水还是土壤中,它都能强烈地吸附于颗粒上,借助于水生和陆生食物链不断富集而最终危害人类。
二恶英对人类的大规模伤害首始越战。由于美军在越南丛林大量使用含较高浓度二恶英的落叶型除草剂,造成大批人员中毒,其远期致癌性及致畸性给参战双方特别是越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二恶英污染对经济的打击也是致命的,1999年源自比利时后波及荷兰、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的二恶英食品污染引发全球性食品恐慌,使这些国家的相关产业招致巨额经济损失,并且直接导致在比利时执政40多年的荷语基督徒人民党与法语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倒台。在我国,1997年香港环保署因深圳海湾产的蚝(牡蛎)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而全面禁止进口,导致养殖者上亿元人民币的直接经济损失。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由于有机物(厨余垃圾、果皮及剩饭菜等)含量较高,含水量较大而热值较低,在焚烧过程中难以达到理想高温;并且由于内含大量废弃塑料包装袋及一次性餐盒等塑料制品,在垃圾的焚烧过程中更易产生二恶英。然而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国内媒体的众多报道回避了这个问题。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纸是包不住火的。2001年5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各国全权代表会议上经投票有九十一个国家(包含我国)赞成,《POPs公约》(后更名为“斯德哥尔摩公约”)获得了通过。公约确定了各国必须立即加以控制和治理以二恶英类为代表的十二项在环境中具有高残留性、高生物浓缩性和高生物毒性的物质,即POPs物质(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残留性有机污染物质)。公约在九十天后(2001年8月23日)自动生效,进入实施阶段。这意味着我国必须通过立法实现对包含二恶英在内的POPs物质污染防治的承诺。
实际上,自2000年6月1日起,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就已经开始在我国实施。标准中特别规定了二恶英的排放限值,要求向大气中排放的每立方米烟气二恶英类不得超过1.0纳克(即1.0个毒性当量,欧洲、北美和日本限值为0.1纳克/立方米)。
然而,由于检测技术的制约,二恶英排放这一限值只能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试行,其它地区自2003年6月1日起执行。作为世界精尖技术,二恶英检测难度较大,检测费用较高,一个样品的分析测试就需花费近万元人民币;再加之我国能够检测二恶英的实验室极少,由于投资较大及技术要求较高,目前仅有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由德国援助的二恶英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自己建设的符合国际标准要求的二恶英研究实验室能够检测。北大二恶英研究实验中心的项目负责人陈左生博士这样形容二恶英样品前处理(提取、分离、浓缩、精制)的工作量,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50米×25米×2米)装满大米,从中挑捡出一颗带色的大米。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虽然国家制订了相应标准,然而由于目前技术条件的限制,对建成以及即将建成的垃圾电厂进行有效的监测实不可能,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些标准不得不形同虚设。
在这种情形下,国内众多的垃圾焚化设备提供商以及科研机构推出了据说是能够彻底消除二恶英的垃圾焚化技术与设备,更有媒体引用某些环保协会理事研究人员的话语,我国研制的垃圾焚烧炉因增加了二次燃烧,所以我国的垃圾炉不排二恶英。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们解决了困扰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的技术问题,笔者真的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成功还是我们的不幸。
在这些机构里面,中宜环能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它便与国内21个省的90多个城市达成城市垃圾处理初步意向,更因众多媒体争相报道的所谓的向韩国某著名企业出售“城市垃圾分类焚烧技术”获利超过2000万美元而名嘈一时,故事的主角吴桐也被众多媒体冠以身价10亿的“中国环保大王”“神童”而成为风云人物。不幸的是,随着吴桐学历与其环保专利造假的曝光,中宜环能的光环渐渐褪去,吴桐也不得不远走德国,一个垃圾神话就此结束。
由于国内在此领域尚缺权威专业的研究评估结论,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国外。2000年,由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美国国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的主要运做机构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主持研究完成的报告《废弃物焚化与公众健康》(Waste Incineration and Public Health)发表。这个300多页的报告用极为审慎的态度指出,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能够在垃圾焚化处理与人类疾病之间建立必然联系,是因为这些研究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因而期待更加深入的研究。通过训练有素的员工的合理操作,现代化焚化设施可以将对公众健康的影响降至最低。不能否认,由于过时的设计、人为操作错误以及设备故障等原因,仍会导致问题的发生。
然而,2001年3月,由英国埃可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位于英格兰西南德文郡首府)的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研究实验室(Greenpeace Research Laboratories)发表的名为《焚化炉与人类健康》(Incineration And Human Health)的长篇报告,通过对二恶英与焚化炉关系的专门研究,指出不管是老式焚化炉还是经过改良的新型焚化设施,依然是排放二恶英的主要源头。这份报告还纠正了许多传统的误解:虽然控制空气污染的科技经过改良,新型焚化设施通过烟气排放的二恶英及重金属数量已大为减低,然而在灰烬中的二恶英及重金属含量却相应提高,仍然造成环境污染;焚化并不能完全消除废物中的有毒物质,而只是改变了它们的形态,部分物质的毒性甚至较原来更高;所谓焚烧可减少废物的重量和体积,不过是针对灰烬而言,如果将焚化炉气体输出量加起来,总输出将超过废物原来的重量。
报告还通过对芬兰、西班牙、德国等欧盟国家在垃圾焚化设施附近的居民的监测研究,指出垃圾焚化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儿童及成人)患上癌症、呼吸系统病、心脏病、免疫系统失调、过敏症及先天畸型等病症。报告的结论是:“足够证据显示,焚化炉对环境造成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伤害,理应被全面取缔。”
就在我国签署《POPs公约》之前的2000年12月,第五届国际政府间协商委员会会议 (the Fifth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Meeting)达成的全球性协议文件中,焚化被列为二恶英的主要工业来源,并且要求新建或翻新的焚化炉均须采用现存的最佳技术(BAT);大会达成一致性共识:从长远考虑,废弃物焚化应被其它方式取代。
谈到BAT(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我们就必须提及由法、美、德、日、瑞士和瑞典共同参与开发的被称为第三代废物处理技术的热解气化 (Thermal Pyrolysis)技术。这种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流行起来的技术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焚烧,它结合了创新的高温分解技术和传统的高温供氧气化技术,在一个高温高压的封闭环境中,把废物完全转变成合成气和可回收的固体残留。清洁处理后的合成气有多方面用途:可以作为原料直接投入化工厂生产化肥,可作为燃料产生热量,也可经过高效燃气轮机发电机系统发电;固体残留是非常稳定、完全无毒的,而且100%可以再循环利用(生产建筑材料及金属合金),这样,就没有任何填埋的需求。由于不燃烧,就没有烟(二恶英)的排放,即使用合成气燃烧发电,人们所关注的二恶英排放也已经降到0.01纳克/立方米以下,尚不足最好的焚烧技术的十分之一。
热解气化技术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是能处理除核废料外所有类型的垃圾,而且不需要事先进行任何分类。这样对于我们前面提及的高科技垃圾,诸如废旧电器、电脑、电池、打印机硒鼓、墨盒此类,经前期拆解分拣回收后的残余危险部分,就有了安全的处理途径。
然而热解气化技术确实不便宜,其投资成本和最好的焚烧技术差不多,整套设备往往需要上亿的投资,尽管有专家测算,我国引进消化这种技术后,成本至少可以降低1/3。这样,在逻辑上我们就面对这样几个问题,我们是一步跨入世界最为先进的技术,还是沿袭发达国家的老路?中国电讯业直接与世界最新技术接轨导致的超速发展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那么,如果将这一技术在中国普及,高达几百乃至上千亿人民币的投资从何而来?
BOT陷阱与脱困
现代垃圾处理设施作为一种公益性投资,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政府实难承担如此巨额的投资行为。我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外资与民间资本等多重融资渠道。在目前世界已有的获取资本的多种手段中,BOT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模式。
所谓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是指政府出于财政或其他考虑,将特定公用基础设施的特许专营权通过契约授与承包商(一般为国际财团);承包商在特许期内负责项目设计、融资、建设和运营,并被允许向设施使用者收取适当的费用,由此回收项目投资、经营和维护成本并获得合理的回报;特许期结束后将项目所有权无偿移交政府。
BOT的概念由土耳其总理厄扎尔于1984年正式提出。由于有效的解决了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问题而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青睐,并逐渐完善成熟而成为国际流行的投资合作方式。著名的英法海底隧道、澳大利亚悉尼港口隧道、香港东区港九海底隧道等一批耗资巨大的项目,都是BOT这一方式的结晶。
(图片来源:王守清) 王守清博士:不要把赌注完全押在地方政府的承诺上,因为它可能与中央政府的原则相背离以笔者对当今国内及国际投资市场的认识,不是资金缺乏,相反,却是有大量的游资充斥。世界银行以及众多海外财团都曾有意于中国的环保投资。那么,是不是借助于BOT,就可以彻底解决困扰我们的垃圾处理投资问题?回顾一下BOT在中国所走过的历程,或许有助于我们清醒的认识。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BOT的尝试,然而真正较大规模的BOT运做还是90年代中期的事,并且很快的在1998年以后归于沉寂。第一波的BOT浪潮以外资为主体,项目主要集中于电力设施及部分水厂。然而由于众多问题的发生,导致能够在中国顺利运营的BOT项目屈指可数。
中方合作者的信用程度、政府法律条文的变更、项目审批的人为耽搁以至取消、项目运行过程中的腐败行为等是导致问题发生的主要根源,世界银行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王守清博士于98年主持的一项中国BOT项目的专项国际调查结果指出了这一点(见王守清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olitical Risks In China’s BOT Projects,中国BOT项目风险评估与控制)。这一切最终导致投资方的收益无法按约定兑现,因而被称之为BOT陷阱。
这里就涉及到政府的守信问题。然而笔者一直这样理解,信用从某种意义而言更是一种能力。当政府的守信成本过于高昂,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就会加大其守信的不确定性。
就垃圾处理而言,由于出于政绩或经济上的眼前利益考虑,我们往往忽视或有意回避了垃圾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营需要巨量资金支持这一现实。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垃圾的处理费用也大不相同,然而利用现代设施处理每吨垃圾的费用基本都在百元以上,试想,一个适用于中大城市日处理千吨垃圾的处理厂每年的营运费用就至少接近4000万。对于中国年产1.2亿吨垃圾的处理而言,就是过百亿的天文数字。
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已逐渐显现出来。由于运营费用严重不足,长江上游三峡库区利用国债资金近几年建成的十几个垃圾处理厂,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内江市的垃圾处理厂的机器已经锈迹斑斑。长江两岸的垃圾或明或暗的倾入长江。而在费用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大量新的垃圾处理厂还在规划建设之中。为确保三峡库区水质,国家用西部债券在四川投入98亿元,四川各大城市都要建设垃圾和污水处理厂。但国家只是对项目建设进行投入,运营费用由各地解决。由于四川的经济相对不发达,运营费用的收取已成为制约环保的瓶颈。
单靠财政难以支持。这一切预示着BOT项目的正常运营需要政府在垃圾处理费用收取、支付上作出可兑现的保证。
图片说明:因医疗垃圾回流社会,未经严格消毒再次使用,废弃一次性医疗用品已成了艾滋病传播的第四条途径。在我国很多地区,这些未经消毒的医疗垃圾被加工成食品袋、面盆、衣架等塑料制品出售。医疗垃圾的非法交易遍及全国,其货源主要来自医院和医疗垃圾焚化站。图为工商部门查获的一批非法回收医疗垃圾。图片来源: 《法制日报》吴煌 汪成明
2002年6月7日,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就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鼓励国内外资金包括私营企业资金投入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等多个方面做出了规定。早在此之前,全国已有70多个城市征收了生活垃圾处理费,但收缴率普遍偏低。比如,按征收标准,北京2001年应收缴垃圾处理费1.3亿元,实际只收取1000万元;天津应收2800万元,实际只收到500万元。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就是《通知》只是提及生活垃圾,这就不得不涉及到我国垃圾管理的条块分割问题。
从目前的现状看,我国城市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医疗垃圾、建筑垃圾,分别由环卫部门(局)、环保部门(局)、卫生部门(局)以及城管部门(城市管理委员会)分头负责管理,每个部门要成立自己的收集和处理系统。由于缺乏国家或地方立法,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收费标准与收费方式难以统一,不仅存在乱收费、重复收费、收费难的情况,还存在因财政预算不足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收费被政府部门占用、挪用的问题;并且,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垃圾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复杂化、混合化的趋势,这种多头管理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譬如我们前面提及的高科技电子垃圾,严格分析,就形成了各部门似乎都可以管,又似乎都管不着的尴尬境地。从垃圾处理的产业化角度,我们就必须考虑相关的效率以及效益,考虑处理范围的划分和有关部门的协调问题。很显然,这种多头管理加大了政府守信的难度。
按照国际惯例,在BOT投资项目中,我国政府部门一般应提供以下保证:土地及其它后勤保证,外汇汇兑保证,限制竞争保证以及经营期保证。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对政府保证作出了种种限制或禁止,其中以《担保法》的立法权威性最高,因而有学者认为政府已被排除了对BOT投资项目作出担保的全部可能性。然而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已有法律专家指出,BOT项目中政府保证并不等同于我国的《担保法》所称的“保证”,根据我国现存法律,我国政府在以BOT方式与项目投资者签订的特许权协议中,为该项目所给予的政府保证,实际上是一种为了在特许权期满后无偿收回项目设施所付出的代价,而非担保关系中为主合同的履行提供的商业信用。因此,BOT项目政府保证的性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担保,政府对BOT项目所作出的保证实际上是一种政府信用行为,而完全脱离了商法意义上的信用保证(刘力华、李科:《我国BOT投资方式的立法障碍》)。
虽然国内学者在此争论颇多,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一案应该结束无谓的争论。
另外,由于令出多门,在这些限制政府保证的不同国家部门的规定中,甚至出现了彼此相互矛盾之处。BOT投资方式的实施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的共同规范,而我国目前尚无职权明确的协调机构。当面临政府换届、领导人更替、政府对工程要求变更甚至主管官员不正当的要求等诸多情况时,信用保证的能否延续往往就会产生疑问。
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为这样一个主要问题: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关于BOT的法律。就我国垃圾处理而言,在其后还隐含着对相关政府部门职能的变更、机构的重组等一系列体制变革要求。
在经过一段沉寂之后,新一波的BOT浪潮已悄然而至。所不同的是,这一波的投资主体以国内的民营企业为主,主要投资在环保领域。譬如北京的桑德集团,在污水治理方面以BOT方式杀入的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国内外投资者以及学者政府的极大关注。由于我们前面分析的原因,这一波也基本重复着前一波的轨迹,面临极大的赢利难题;并且,由于民企实力使然,普遍缺乏大型BOT项目所要求的融资、技术与规范运做能力,因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尚难成为我国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然而极为重要的是,这一波浪潮将作为一面镜子,折射出我国政府的政策走向,从而左右国际资本以BOT方式在我国环保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程度。
由于缺乏BOT这一有效融资手段,而对环保基础设施已是燃眉需求,我国不得不通过巨额外贷与国债融资。在我们前面提及的西部债券中,我国把内地多个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捆绑以资产证券化为基础向美国发行的离岸债券(中国西部基础设施项目债券),由于涉及到国内多个项目业主和地方政府,在项目权益的法律、财务、风险以及资产权益的重组、限制和再拆分上同样异常复杂;并且由于在许多项目上运做的不如人意,隐含着极大的偿债危机。反观BOT项目,由于其所需资金由项目公司自筹,在经营上实行自负盈亏,国家最大程度地做到了风险规避,而不存在任何财政负担。
关于BOT项目的国家立法已是迫在眉睫。分析至此,对于我国的垃圾处理,方向似乎已经了然明确。然而沿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这条生产垃圾因而消灭垃圾的曲折弯路,我们是否感觉自己在垃圾面前只是被动的跟从?粗放型的经营模式,已使我们习惯了倚赖投资来拉动经济,而忽视了实体自身的精细运做同样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源自对以自然资源非补偿性掠夺式消耗为前提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人们重新认识到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西方国家首先提出了废物处理的4R理念:Reduce(源头减量)、Reuse (重复使用)、Recycle(循环再生)以及Recover(回收利用),并由此引发发达国家在工业设计、产品生产与消费等领域的一系列革命。我们注意到了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诸多变革:严格限制过度包装的法令;因环保而生的全新的设计理念,譬如便于回收时拆卸快速便捷,金属螺丝已被嵌入式外壳取代;由于防火涂料在回收利用时会产生毒素,外壳因而被金属板替代;为减少回收处理污染,原来电路板上用来焊接部件的铅质焊锡已被银或铜焊锡取代;强制性改换包装及包装物重复使用,譬如用于运输防震的泡沫塑料颗粒被水溶性的填充物所替代;根据废物“谁生产,谁付费”的原则,高科技产品生产厂家与用户都要支付一定的回收处理费用;从法律、税收等角度作出的种种倾斜与限制等等。众多的“绿色工业产品”因此诞生,并且越来越成为世界流行的趋势。
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这一切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垃圾问题,并对其长远发展趋势作出定性、定量的分析与预测。从总体长远说来,源头的减量以及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柔”性方式逐渐取代硬性的处理设施,似乎更合乎自然法则,从而达至永续经营。
(至本文截稿,笔者被邀请参与以及知情的几个大型垃圾焚化发电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前期运做之中。希望此文于国于民有助。)
《反思:中国垃圾问题》在2003年1月期《智囊财经报道》刊登后,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西方研究中国的权威基地机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通过专家小组评议将此文录入其实证研究文库——《中国研究文库》,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