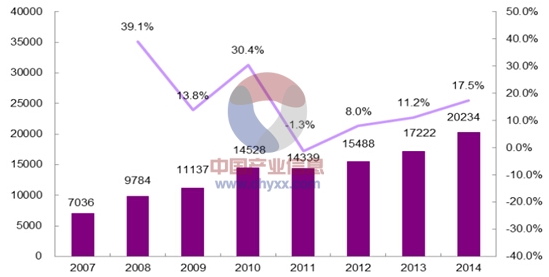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敌人,是教条主义和“左”的观念的话;那么在今天,一支更古老、更顽固也更加隐蔽的敌人,正蛰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千方百计地阻挠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它就是“小农经济范式”。作为古老民族文化的负遗产,它对我们每一位行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中国公民不宣而战。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战争不得不延续到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叫人悲哀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这场战争中,都还没有积极应战;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将来可能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学费,让WTO来教会我们如何被动地战胜它。
一
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创造、设计、丰富人的生活。因而,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公民之生活内容的丰富程度、消费链条的环节与长宽度、应对生活的自由程度等,就构成此时该国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为实现这一内容而组织起来的经济活动之组织形式、分配方式、行为模式乃至思维定式等,就成为相应的经济形式。经济内容中,生产力是根本要素;经济形式中,生产关系是核心内容。
经济内容决定经济形式并进而影响经济行为,行为又决定经济意识。意识、行为、形式、内容四者合力,又在社会文化层次上积淀成相应的经济活动范式。“经济范式”作为文化遗产,将置根于公民的社会文化心理之中,并最终影响公民的经济活动。

二
何为“小农经济范式”?小农范式=农Χ权Χ家。这是由旧中国数千年的宗族社会、集权国家和小农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的“农”即小农经济,是旧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内容(农、桑、林、盐、冶等)与经济形式(户井乡、租赋税等)的总和,成为小农范式的经济基础。这里的“权”即集权国家,此处主要指中央集权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它构成了小农范式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这里的“家”即封建宗族社会,它构成了小农范式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
“小农范式”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为“家”用“权”且采用的还是小“农”经济的行为模式。
三
权力社会中的国人对两种东西最感兴趣,一是“权”,一是“家”。此时的我们也一直生活在两种社会形态中,一是权的社会,一是家的社会。五千年来,都在争权夺利;五千年来,都没有走出家门。
先说“权”。“权”的核心内容是“支配”二字,往前再走上一步,就是“拥有”了。我不一定非得拥有某一件东西,只要我能够支配它,就算是拥有了对它的权力。权力通过“支配”而实现“拥有”。在支配权与所有权之间,支配权是核心。
“权”的对象渠道也有两个。一是对人格的支配,处长支配科长,科长支配科员;二是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如财富、荣誉、地位等。对人格的支配是为了最终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实现对社会财富的支配,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是权力的最终目的。
再说“家”。现实生活中的家庭,乃是由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经济单位。它与我们这儿所说的“家”有联系,更有差别。我们这儿所说的“家”专指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当然也包括家庭),如果只有两个人在争抢某一有限利益时,“家”的黑手也能将他们拆成两个利益集团。因而“家”与“自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四
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一个集权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权力经济。加上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因而,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权力社会形态。权力依然渗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主导着社会经济运转的方向,决定着人们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以至于过去国有企业的大小厂长、经理们,都在争抢相应的行政级别。
历史上的中国还一直是个“家”的国家,即宗族式的封建国家。历次改朝换代的战争,说到底都只是宗族之间的战争。获胜的宗族即刻把自己变为国家,历代的太庙便是明证。
“权”和“家”这两种怪物都还有一种可怕的能力——极强的“自组织能力”。像是有生命的物质一样,它们也都能自我组织、自我分裂、自我繁衍、自我扩张。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上无处不“权”,无处不“家”;人人爱“权”,人人爱“家”。
“权”是有层次大小的,“家”也是有层次大小的。各层次上的弄权者,为各层次上的家,争权夺利,熙熙攘攘。顷轧与内讧伴随着鲜血与泪水、裹挟着耻辱与罪恶,在古中国的大地上肆意横流。
五
历史上的中国也一直是个农业社会,它导致处于权力社会中的我们,即使是在看待“宇宙的无限”这样的哲学命题时,也带有小“农”的局限。在现代宇宙学看来,宇宙的无限是一种“生成着的无限”,从即使是有限的资源中也能生成出无限的结果来;而在小“农”哲学看来,宇宙的无限乃是一种“既定着的无限”,拿一个总少一个,只不过它是无限多、总也拿不完而已。
“小农范式”的哲学源于农业财富的生产方式。尽管造物生生不息、农业财富看上去也会无穷无尽,但由于地力、人力、物力的有限,农业财富又总是被限定在某个数量之内。人类知识的无限发展趋势,总是被限制于客体资源有限的尺度之内,最终的结果就是你潜移默化的接受了“既定着的无限”。“不患寡,而患不均”经常被写在农民起义军的大旗上,便是这一观点很好的注脚。
而现代经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生成着的无限”。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生物经济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更是将“生成着的无限”这一现代宇宙观发挥得淋漓尽致。现代生活内容的无限追求,又为现代经济的无限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动力。
六
“农”与“权”与“家”的结合,不仅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浸染了整个社会的肌体,更在于它们渗透到人性的内部。权力社会中,一个人在某个小“家”里可能是治人者(即主子),但在另一个更大的“家”里,却是治于人者(即奴才)。如果一个人,既不想做主子,又不想做奴才,那就只能被这样一个社会视为另类。长此以往,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就形成了主子、奴才和另类这三类人性的混合体。
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例,更是在促进这一人性的分裂与混合过程。只要假以条件,刘邦、朱元璋之类的市井无赖可以先是奴才、继而造反成为另类、最后当上皇帝而成为主子。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昔日的主子沦为奴才、而其内心深处又总是保留了一点另类情绪。我们不妨将这一现象称为人性的“权力疤痕”。
哪怕是山野村夫,其人性深处的“权力疤痕”也未能幸免,只要有人落进他的势力范围,他也会大玩特玩其“支配权”。其具体形式可能没有权贵们那样精致,但两者的心态绝对的是如出一辙。学者们称其为“穷人的腐败”。
在一个极端的权力社会中,只有三种人:主子、奴才和另类。但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他又极可能是这三种角色的混合体:只要假以条件,他就有可能选择其中的某一个角色充分表演一番;而一旦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也可以在这三种角色中任意转换。
七
庆幸的是,上述诸多可怕现象正在离我们远去,有的甚至是一去不复返了。而无庸讳言的是,残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小农范式”有可能是最为顽固的一部分。最后地清除它们,需要我们加倍的努力直至从我做起的勇气。这也是写作本文的原因。
别的不说,盛行于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小农范式”的典型表现。“地方”乃“家”作怪,“保护”乃“权”作怪,“主义”二字乃兆示其“毛病”之深之烈之顽固日久,追究到行为者的观念上,我们同样不难发现是小“农”在作怪。至于“某城是我家,环保靠大家”之类的口号,更是叫人哭笑不得。依照这样的口号行事,是否就意味着把垃圾送出某城之外,就万事大吉呢?
经济活动里的“小农范式”更是不胜枚举。制假贩假、行贿受贿、三角债、面对外商时的窝里斗,乃至企业内部的股东之间、劳资之间、部门之间、个人之间的相互算计,都或多或少地与“小农范式”有关。
八
根治的方法还是有的,就是以“法”制“权”,以“知”去“农”,以“国”疗“家”。合称“三大战役”。
第一战役是以“法”制“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迫使行政权力合理退出日常经济生活领域,真正割断权力与市场之间的纵横交错、变幻多端、千丝万缕的寻租渠道。培育健康、有序、高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建立健全系统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经济法律法规体系。
第二战役是以“知”去“农”,尽早确立迈向知识经济社会的战略目标。对于“知识经济”,我们一定要站在社会形态的高度上来认识它。知识经济现象,实质上是知识经济社会新一轮红日的一抹朝霞。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乃是从经济主要推动力的角度来划分的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三个社会形态。这对于工业经济尚欠发达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场极为严峻的挑战。
第三战役是以“国”疗“家”,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自由人的联合”。“国”乃公共领域,“家”乃利益集团。每一位中国人都不要再把整个社会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家”,然后又把自己归到其中一个个这样的“家”中。每一位中国人都要走出“家”门,都要把自己看成是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共和国公民。再以个人为单元,组成家庭、单位、社区、城市和乡镇、省区和国家。“国”立而“家”废。
九
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离不开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腾飞,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势不可挡。而这一目标与残存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小农范式”是格格不入的。倘若我们不能尽早战胜我们自身的缺点,我们少不了要走更多的弯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最后,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如果我们非得要让WTO来一次次地教育并迫使我们被动的战胜“小农范式”的话,那“学费”将是十分昂贵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