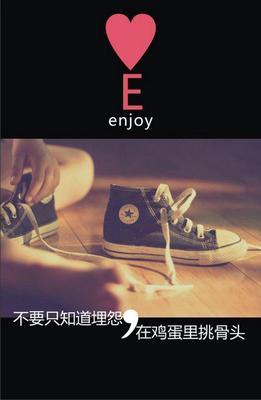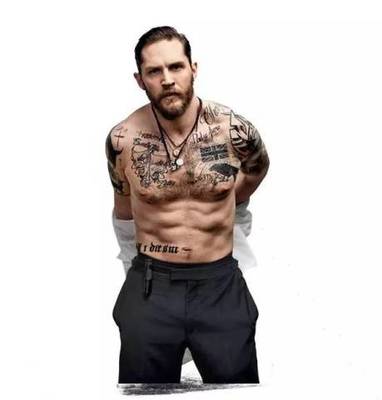如果能在以下两点上获取突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有所转变和提升。第一,靠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来引导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改变市场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的无效性
中国经济崛起的特殊性
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复杂情形在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兴起的时候世界全球化程度远远低于今天,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情况大不相同,且不用说中国目前的人口在世界中的比重比当年日本高多了。
美国1900年开始赶超英国的时候,美国受到欧洲很多影响,不少欧洲精英移民到了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来赶超英国的。
战败后的日本,其经济复兴有赖于相当深厚的制度积累、人力资源积累,加上美国对它的全力扶持,无论从物质援助还是经济制度建设上都给了日本很大的帮助,这些都和今天的中国不同。
再看一下韩国、台湾地区还有新加坡,它们相对而言都是小国家(地区)、小经济体,它们面临的问题、赶超路径和中国比完全不一样,从某种角度讲,它们比中国更容易赶超发达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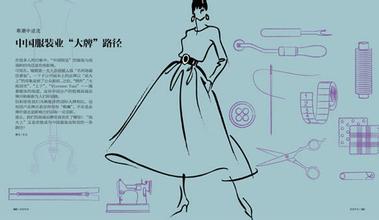
中国是在不断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来摸索经济发展的道路,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中国经济崛起的特殊性:
第一,中国政治上高度统一,但是经济上又高度分权,这样一种体制跟当年美国、日本、韩国等各个国家都不一样。日本、韩国这些相对较小的国家,经济上集权政治上分权,和我们是相反的;美国则是联邦制,中央跟地方的权力分配相当明确。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赖于以地方政府为核心和主要动力的、以“发展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各个地方政府纷纷以招商引资、解决就业问题、税收增长、GDP增长为最高追求目标、政绩所在。
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以发展经济获取政绩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市场经济处于萌芽阶段时期,能较快推动经济发展,几乎每个项目,一上马、一投资就会有收益,因为市场稀缺。但随着市场逐渐发育成熟,政府主导的投资的效率将越来越低下。
但是,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有明显改变的迹象。中央现在强调节约型经济、强调自主研发能力,这些政策可能对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改善环境、扶持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发展,但是总的来说,地方政府还是控制了太多的经济资源,最明显的就是土地。这和我下面要谈的农民问题关系很大。
在土地问题上,地方政府要给农民一定的谈判能力。现在城市规模盲目扩张,政府根据农民过去种粮食的价格乘以一个系数,补偿给农民,这个补偿太少了,因为你征地后实际是把农民的生计给扼杀了。补偿的权利不应该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应该交给市场来定,让农民和政府之间建立一个讨价还价的体制。推而广之,不单要向农民,政府要将更多的权力让渡给各个市场主体,但无疑这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第二,中国经济现在从意识形态上仍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被忽略的。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在经济生活中,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各家国有企业、政府经济部门,必须是由政府来任命,很难由一个无党派人士去任一把手。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在经济建设初期可以大量重用从西方留学回来人员做部长,甚至更高首脑。我记得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就是留美回国的。
第三,我们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改革开放之初人均GDP是300-400美元的水平——赶超国外的,而且我们还有十多亿人口。一个起点如此低、规模又如此大的经济体的崛起,对全世界的影响以至于中国承受到的反作用跟当年的美国、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而我们在很多方面无法简单照搬国外的经验。
举几个例子。
比如,资源和能源。如果经济体比较小,人们可以忽略本国经济增长和起飞对世界自然资源价格的影响,或者你可以通过节约、提高技术来消化价格上涨的影响,像日本在1971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后就做得很成功。但是中国仅靠提高原料使用效率无疑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真正的技术突破。
再比如大国的金融体系怎么建立?一个小国的货币体系可以全面美元化,但中国这么做绝对不行。中国现在采用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需要相当的外汇储备来支持,如果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我们接近一万亿的外汇储备恐怕都不够。所以中国作为大国,不能在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资本问题上搞简单一体化,需要探索新的国际资本管理模式。
从这些具体事例上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要有一批能在国际上为中国造舆论、维护中国利益的人。在这方面日本做得很差,日本虽然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但是它经常发不出自己的独立声音,这和它长期依附于美国体系及日本式教育体系有关。印度相反,虽然印度经济发展远远不及中国,但印度有一点比中国强,印度培养了一大批的精英人才进入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当高级领导人,他们势必会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制造舆论,所以印度现在在国际社会上的舆论声音不容忽略。
第四,中国现在有7.5亿农民,大部分农民现在不能正式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这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在。农民问题突出,这必将导致我们的赶超路径和别的国家地区不一样。“三农”的核心就是农民问题,怎么样给农民创造机会让他变成城里人、有序进入城市,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之根本,在农村范畴里解决农民问题是不会有结果的,这可能是我的想法跟主流观点、包括与政府观点不太一致的地方。
避免“日本病”的希望
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GDP中超过一半,去除掉约10%的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的这个数字还是有40%多,仍旧超过其他东亚国家的历史最高水平,韩国、日本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最高也就是40%多一点,一般在30%多。中国的投资比重之所以这么高,很多人认为是居民储蓄过多、消费不足,导致银行资金充足,资金成本很低;我认为另一个因素很多人没有谈到,即中国企业的储蓄过多。在一次分配中,国外企业的基本规律是四分之一为资本回报,四分之三为劳动所得,但中国企业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一般是40%为资本所得,60%为劳动所得。企业赚了钱按理说应该分红、返还给股东,但由于治理结构问题,中国企业经常不分红、自作主张将钱存起来或者进行投资。
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没有经历大的衰退,中国企业也没有经历过疾风暴雨式的挫折,故而在投资决策上比较乐观,这些都导致了中国企业整体投资率比较高。
日本“十年失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需不振,所以我曾说中国已出现了“日本病”征兆,但中国好在有内需潜力,如果能把7.5亿农民的消费启动起来,把他们中一部人转移到城里来,这个潜力不得了,这也是中国不致于真的得上“日本病”的希望所在。日本经济当年像得了成人病,而中国就像一个迅速成长的青少年,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成长,克服发育中出现的缺陷与毛病。
我认为如果能在以下两点上获取突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有所转变和提升。
第一,靠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来引导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依赖出口。
第二,改变市场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的无效性。现在自然资源、能源的价格太低,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政府再呼吁循环经济都是空话。
观点对照
实现以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要十年之时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所占比例极大。两者总计在GDP所占比例从2001年的60%上升到目前(2005年上半年)的89%还多。而同一时期,GDP中消费比例从60%下降到50%。中国经济对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依靠程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
中国增长模式中投资倾向如此强烈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刺激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发展贸易来创造金融资本;二是国有金融体系垄断了金融资本,政府部门也就控制了投资资本的来源。
这种发展模式有深度的政治和经济原因:首先,当外国资本主导的出口部门实现增长的时候,政府部门控制的投资确保为出口增长提供基础性服务设施。第二,国有控制的投资体系是促进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工具。第三,国有金融体系控制的投资渠道和资本还成为地方政府部门取得政绩的首要工具。中国的行政考核是以当地的经济发展成效来论英雄的。GDP成为了衡量一个省市经济发展的关键标准。为一个省市创造GDP最容易的途径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物质财富成为了衡量一个政府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因此,政府部门高度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中国要朝着平衡增长的模式转变,必须停止目前的模式发挥作用,实现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长远发展之道,完成这样的转变可能要花费10年的时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