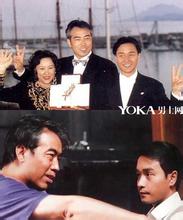廖沫沙、吴晗:三家村遗墨 ——廖沫沙、吴晗与汾酒文化 在汾酒博物馆收藏有这样一幅题字: 汾酒世所珍,芳香扑鼻闻。 水纯工艺巧,争说杏花村。 录吴晗同志诗,赠杏花村酒厂 廖沫沙1983年夏末 吴晗、廖沫沙,是中国当代史上人人皆知的人物。 历史把这两个人物紧紧地扯在一起,源于1961年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开办的《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吴南星的这些杂文紧密联系现实,敏锐地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 其中吴晗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09年生,1931年以数学0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才华出众,1937年,年仅28岁的吴晗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5年吴晗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主席著作。1949年北平解放,吴晗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北京市副市长等职。 廖沫沙则是现代著名作家、杂文家,代表作有《鹿马传》、《分阴集》、《廖沫沙文集》等。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晗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出的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吴晗、邓拓先后死于文革中。 吴晗生前,曾经访问杏花村,并留下了“汾酒世所珍”的诗句。1983年,廖沫沙也来到了杏花村,听酒厂的人介绍说吴晗曾经去过,并提过诗,但题字在文革中烧毁了。于是,廖沫沙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录写了吴晗的这首诗。 万兆元、祖岳嵘:松鹰的秘密 ——万兆元、祖岳嵘与汾酒文化 汾酒博物馆藏有一幅《松鹰图》,一看便知与画鹰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很有渊源。画的题款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军旅书法家李铎的手笔。画的作者有两位,一为万兆元,一为祖岳嵘。 这两位画家的名头,即便是在书画界,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多。仔细一查,原来很有些来头,值得一表。 万兆元(1932—1998),祖籍山东,北京中国画研究院画家,是我国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丈夫,国画大师郭风惠、李苦禅的弟子。万兆元最早的老师是郭风惠先生。郭老是1919年即任教于北京艺专的著名美术教育家,教过李苦禅、王雪涛等。郭老很喜欢万兆元,后来把他介绍给半师半友、情同手足的国画家李苦禅,于是他又成了李苦禅门下弟子。 万兆元的作品,深得郭风惠、李苦禅真传。他画的水仙、荷花、虾、松鹰,都有很高的品位。特别是松鹰,深得苦禅三昧。 《松鹰图》的另一位作者也是个人物。祖岳嵘,1919年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68军参谋长,八个样板戏之一的《奇袭白虎团》就取材于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亲自指挥的一场战役,祖岳嵘时任主攻部队的副师长。他同时也是一位儒将,诗、书、画、琴、京剧均有涉猎,自得其乐。 不知是什么渊源,万兆元跟祖岳嵘合作过不少画作,祖岳嵘与李铎也合作过书画作品。但是,这三位合璧的作品很少见。抚画思之,不由感叹山西汾酒的无穷魅力,汾酒文化蕴含的故事也太多了,永远说不完。

熊伯齐:诗书画印君子风 ——熊伯齐与汾酒文化 熊伯齐是当代少有的诗、书、画、印皆擅的艺术家,而且在书法领域又是楷书、行草、篆隶都很出色。他又名光汉,号容生,四川井研县人,1944年3月生于成都。有三个代表性的头衔: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联牡丹书画艺术委员会副会长。作品入展全国历届书法篆刻展及其他重大国内国际展,并多次任评委。 与张大千齐名的大画家于非闇对熊伯齐影响很大。1955年熊伯齐随父母迁家到北京。熊伯齐从小喜欢画画,很喜欢临摹中国的工笔画大家于非闇的画作。1959年于非闇去世后,熊伯齐去北海画舫斋参观了于非闇遗作展,感到非常震撼,决定一心一意学习中国画。因为中国画上题字、印章是不能少的,如果自己画的画还要找别人题字的话,有些说不过去,于是熊伯齐就干脆题字、篆刻全部自己干。于非闇是学宋徽宗的,写瘦金体,所以熊伯齐也认真学习瘦金体,后来成为当代“瘦金第一人”。刻印也是,他找来许多石头,一有时间就刻上几刀,渐渐地在篆刻方面也有了些名气。本来,熊伯齐搞书法、篆刻都是为画画服务的,但没承想自己反而在书法、篆刻方面成了名。 1971年,熊伯齐经朋友介绍,开始跟荣宝斋的徐之谦老先生学篆刻。1973年正式到了荣宝斋,篆刻成了他的专业。经过不断地钻研,熊伯齐的篆刻以雍容大雅、凝重朴茂之印风颇为海内外篆刻界所瞩目,成为当代印坛的表率。 除了楷书“瘦金体”,熊伯齐的书法还以篆书及行草见长。他的篆书既得纵横飞动之韵致,又具端严雄健之气象。其行草用笔洒脱散逸,少作连绵缠绕之态,驾轻就熟而极守法度,通篇洋溢着文质彬彬、潇洒自如的君子之风。 对于绘画、书法和篆刻之间的关系,熊伯齐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篆刻虽由刀石完成,但其文字书写仍需笔墨,故古人有‘印从书出’之说。中国画也如此。传统的绘画与书法所用的工具都是毛笔。古代的文化学习都是从写毛笔字开始的,日常书写亦基于用毛笔,所以古人有熟练的毛笔使用习惯。当用同样的工具来作画时,这种习惯也会下意识地带到绘画中去,故有‘书画同源’之说。” 熊伯齐留给杏花村汾酒厂的作品是两幅行书,其一内容是唐代诗人许浑的一首五律,其二是熊先生写给杏花村的一首无言诗:“促织鸣幽草,来尝竹叶青。杏花村月色,朗朗送深情。”书风洋洋洒洒,不激不厉,君子书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