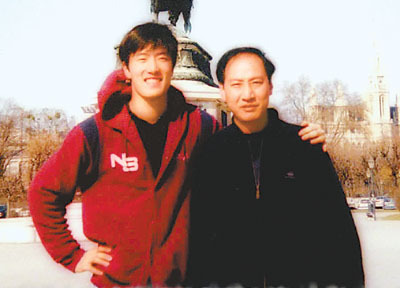小友云集时,问起一事:你们还看电视吗? 曰:否。 顿觉老脸无光。 这种调查方法虽然极不科学,可惜并非“孤证”。记得去年,本频道一帮电视理想远大的兄弟们,搞出了一套真人秀实验片《实习生》。收视率差强人意,而在制片人会上公布观众结构分析时,却搞得满座轰然。这套节目的定位毫无疑问地指向就业、创业中的年轻人,而观众居然以中老年居多。 满座轰然,继之以满座唏嘘。类似的反讽,据说在新闻频道的收视分析中,也屡屡一见。 其实也无需多做“调查研究”,仅从直观中,感受已很分明。十年来,但凡是吸引中老年的电视剧、栏目(如《今日说法》)往往一炮而红。而定位一但指向高素质年轻人,却总是草创艰难。 年轻观众的集体出走,带动了电视业的阵脚。一念及此,每每心惊。 一种霸权的崩毁,最可怕的就是面对核心资源逐渐流失而局中人浑然不觉的状况。 大清朝的覆灭,是一个不算远的例子。在中国王朝的败亡史中,清代演绎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末路故事。 记不得是哪位前辈史家(顾炎武?)说过,王朝倾覆不出乎两途:其一曰“土崩”。也就是大规模内外战争。如秦、宋、元、明。其二曰“瓦解”。也就是群雄割据。如汉、唐。 惟独清代,内患虽有,但经过咸丰、同治两朝,大乱次第戡平,居然隐隐然有“同治中兴”之象;外侮虽殷,但真到了太后回銮千疮百孔之时,列强已有共识,“大清天下取不得!”遂又转危为安;地方督抚权重一时,但招之来挥之去收发由心,终究还没有到尾大不掉,对中央形成实质性威胁的地步。 有清一代,从中央政权的执政能力上,可以说一扫中国古代王朝的诸多弊端。从宦官宵小到外戚权臣,从来不曾成过气候。就武力而言,除了洋鬼子,其他一律白给。平洪杨、平捻军、平回乱的武功,居然发生在内忧外患的王朝末季。仅此数端,就算是风雨飘摇,就算是百病缠身,又何尝不可以带病延年? 然而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只百足之虫,却经不起区区数万义军的登高一呼,旬月之内,死生反掌。如果说武昌首义是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话,这根稻草未免也太轻了。近三百年高寿的庞然大物死得如此不明不白,这个过程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比如一支军队,指挥部没有被打掉,战斗力没有分毫损失,却为何在一夕之间解体?如果你是指挥官,该有多少遗恨?多少迷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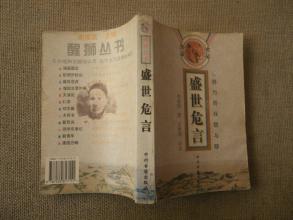
西方式的、以“系统结构”为着眼点的分析方法,是解释不了这种现象的。因为结构本身未变,维系结构的“办事体制”也未变。从管理技术的角度上说,经过1901年后的锐意革新和技术进步(铁路和电报),中枢的控制能力甚至是大大加强了。如果非要解释的话,一个东方式的词“气运已尽”,还算大体靠谱。 “气运”本身太神秘,不可说。表征出来的,是人才的繁茂或凋零。 回头看看“同治中兴”是如何造就的?庙堂之高,有恭王、文祥总持于内;江湖之远,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僧格林沁、多隆阿等一干能臣驰驱于外。一时间,可谓人才鼎盛。即使是光绪初年,李鸿章、张之洞、沈桂芬、张佩纶这样的人物,也颇上得了台面。而到了袁世凯一脚踹开寡妇门的时候,看到的,却只是载沣、岑春煊、盛宣怀这路货色。 人才哪里去了呢?应该在大帅帐下“赏穿黄马褂”的,正在革命军中踢正步;应该在都察院中“正色立朝”当御史的,正在上海租界里办报馆;应该在翰林院里研经传的,正在日本办同盟会。慈禧老太婆,任你精明强悍,不亡何待啊! 听听《桃花扇》的最后一曲:“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 从致死的病因上讲,这既不算“土崩”,也不算“瓦解”,权且称之为“淘空”。前两种病,史不绝书,惟独这“淘空”之症,清朝是唯一的倒霉蛋病例。 此症之所以难治,有两个原因: 其一,“土崩”和“瓦解”究竟是一个较长历史过程累积而成的结果,其间必有反复的较量,必有惜败的孤臣,必有垂成的反扑。而“淘空”之症,则是核心资源的缓缓流失,病来如抽丝,病死如山倒,望空搏影,想还手都找不着下家儿。 其二,“土崩”和“瓦解”都是因为当政者在原有逻辑下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失之于骄奢,或者失之于黯弱。而被“淘空”的过程,则不管你做得对还是做得错,只要你是在原有逻辑下做的,一概无效。 如果要开方子: 先入一粒“回魂丹”,多一些破局的勇气。再灌一碗“大补汤”,多一些珍惜的敏锐。 大势变迁,总是象从四周悄悄掩至的暮色,等你瞿然惊起的时候,已经入夜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