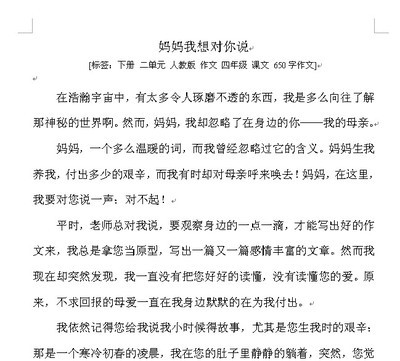杰佛里8226;萨克斯曾被誉为“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现在,他正致力于解决极端贫困、人口过剩和气候变化问题。这位顽固的乐观主义者向埃德8226;皮尔金顿表示,“消极论”是最大的障碍。

一年前,当杰弗里·萨克斯在伦敦皇家学会做首场里斯系列讲座的时候,在启蒙运动的怀抱中,在艾萨克·牛顿画像的注视下,他深信:他那关于我们能够战胜全球问题的信息将被听众接受。但是,当讲座结束时,他大为吃惊,听众冲他高呼“不,我们不能!”不,世界将永远不会合作!不,人类永远不会理智!不,我们无法弥合分歧!
“我吃了一惊,”萨克斯说,“我本想,在这种地方至少不会有异议。这里聚集了英国社会的精英。但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悲观主义,坦白地说,真是不可思议。”
上面的故事是对萨克斯生命中独特角色的鲜明写照。他几乎成了全球政治的滑稽大婶——英国传统儿童滑稽剧中的一个角色。在全世界响起“哦,不,我们不能!”的大合唱时,他以更大的声音还击:“哦,是的,我们能!”是的,我们能让非洲脱离贫困,并把人口稳定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是的,我们能继续享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寿命;是的,通过发现抗击气候变化的新技术,我们能够避免灾难。
假如这些主张来自其他任何人,则可能会被当成是屯溪寡妇的胡言乱语——屯溪寡妇是儿童剧中的一个搞笑角色。但是,萨克斯具有让人严肃对待的知识权威,他被誉为“大概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学家”。他曾在100多个国家工作过,并在拉美各国和前苏联担任顾问。最近,他把注意力转到席卷全球的重大危机上面,从非洲艾滋病到水战争。他在时任秘书长的安南手下担任联合国千年项目主任。爱尔兰摇滚音乐家及活动家博诺称萨克斯为“我的教授”,注意到“这个人行动起来,更像是哈莱姆传教士,而不是波士顿书呆子。”
不过,萨克斯本人两者都不像。相反地,他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精神焕发的大学毕业生,尽管已53岁了,却象二十多岁刚出校门的学生一样,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曼哈顿中央公园边上,我们坐在他的联排别墅内,屋内布置雅致,家具不多。在这里,他那当儿科医生的太太和三个孩子和他住在一起。交谈时,他激情四射,很有感染力。他的新书《共创富裕:拥挤星球的经济学》(企鹅出版社)同样充满激情,迸发着思想的火花,全书只能用顽固的乐观主义来形容。
那么,这种乐观主义又是从何而来呢?“来自观察和经验,”萨克斯用典型的启蒙运动风格回答道,“此外,也许生性如此。我看到成功的可能性。但是我很清楚,这是个选择问题,与看不见的市场运行和科学奇迹无关,关乎一个决定。”
萨克斯笃信把事物进行分解的方法,把难题拆解为更小和更容易处理的部件。他把同样的原理运用在自己身上,称其乐观主义有两个部件:相信“科学使人们在地球上生活富足、生息不止的能力,以及对人们跨越不同文化、宗教和语言进行合作的能力。”他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两种思想都遭到攻击。”
萨克斯能举出他所表达意思的实例。他最得意的是为非洲开出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处方。“我记得在十年前发现,用抗逆转录病毒来治疗身患艾滋病的最贫困者,在技术上是可能的。我问我的同事,能不能做,得到的回答是‘能做,为什么不?来吧,我来教你。’然后,我就带着这个知识,并派上用场。”
从问题,科学假设,到切实可行的方案。然后,与联合国和各类机构合作,落实。“直到2001年,还没有一个非洲人——没有一个人——在一个捐赠支持计划中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回顾过去,说到这些都令人吃惊。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当时]称,不行,非洲人不知道时间。但是,现在近两百万非洲人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
萨克斯走过的是一条非凡的人生道路。他在密西根州长大,一举考上哈佛大学,大学期间便当上了经济学教员,29岁被聘为正教授。在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他在哈佛呆了20多年,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
在那里,他所承担的任务与处理非洲艾滋病不可同日而语。他的著作对世界面临的三个巨大挑战发起了行动号召:人口过剩、极端贫困和全球变暖。最令人心惊的预测提出,到2050年,人口可能由今天的66亿增至117亿;贫困意味着非洲人的预期寿命比高收入国家要短33年;按照中国和印度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大气中二氧化碳(CO2)的浓度到2050年可能翻番,将导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面对如此灾变景象,你会觉得与皇家学会的听众产生了共鸣。“哦,不,我们不能!”萨克斯的回应是萨克斯式的,他把每一个问题进行分解、分析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他表示可以做到,而且全世界的花费异常少——只占总收入的2%-3%。“我们容易因正在发生的大事而手足无措,甚至吓倒,”他说,“这是个悖论,我们可能对自身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已经走上了这条路——然而找到另外一条道路的成本并不高。”
环保人士提出异议称,萨克斯想要鱼和熊掌兼得。他希望经济继续增长,但他同时还希望避免因经济活动导致的灾难性气候变化。
对此,他底气十足地回应道,他相信技术的力量和人类的聪明才智。就气候变化而言, 碳汇是减少二氧化碳水平的一种可能的途径,他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即使失败,太阳能可作为替代方法。无论如何,他不愿开历史倒车:“化石燃料对气候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两百年前就不应该用煤来发动蒸气机。这错了吗?我不这样认为。技术有预料不到的后果和副作用吗?当然。但是接下来你需要重新调整。”
不过,最尖锐的攻击来自纳奥米·克莱恩,她在其新书《振荡学说》中,对萨克斯进行口诛笔伐。她宣称,1970年代玻利维亚制服恶性通货膨胀——萨克斯藉此经济绝技而名声大噪——仅仅是通过政府压制实现的,她称之为“一种近似军政府”。她辩称,他后来在波兰倡导的自由市场休克疗法导致了全面的萧条。
“嗨,别这样,看问题要全面,”当我向萨克斯提到克莱恩的批评时,萨克斯的回答略有不快,“波兰经历了最为成功的复苏,有着强有力的民主制度,我再兴奋不过了。在玻利维亚的镇压?事实上恰恰错了,没有人丧命,如果她称之为近似皮诺切特的话——我是说,皮诺切特屠杀了数千人,并对成千上万人进行严刑拷打。在通货膨胀达到50000%的时候,玻利维亚依据宪法进入了30天的紧急状态。
但是萨克斯也同意克莱恩的看法,苏联垮台之后美国放弃责任。他说,他建议对俄国取消债务和紧急贷款,没有被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听进去,感觉像是在飓风中心呼喊。
萨克斯有他最大的抱怨。他在书中指出,乔治·W·布什政府在所有最为关键的领域里阻碍发展:从计划生育,到援助非洲,以及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相反地,布什政府追逐的是一条残酷的军国主义路线,美国现今花费的战争经费几乎是其他国家的总和。
翻开《共创富裕》这本书,萨克斯举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布什对全球行动说不的例证,该书点明美国总统最具破坏力的遗产将不是伊拉克战争,或退出《京都议定书》,或其他的任何单一决定,而是更为一般性的他所广为倡导的东西,萨克斯称之为“消极心态”。布什对“不,我们不能!”的大合唱给予了支持。这可能会使他们很多人听来感到痛心,但是皇家学会的听众在这方面是布什的追随者。
萨克斯承认,我们正走向悬崖,但仍保持一如既往的乐观,这并不奇怪。他欢呼:“美国宪法了不起,我们将在2009年1月20日午间产生新的总统,这将给予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
接着,他引用了一位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句:“否完之后即为是,未来世界之所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