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走出单位》
第三,纠正单位制的改造。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建立和完善了单位制。单位制对中国城市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这种改造如此彻底,以致我们总是下意识地重复单位方式,难以找到其他方式。但是,单位制的改造削弱了我们的行动力和领导力,让我们变得不敢判断自己的对错,而是习惯性地寻求他人的指导和肯定。 第四,领导自己。我们还只是在尝试获得公民权利和自治能力。未来公民社会的建设是我们培养领导力、履行领导义务的基础。但是,不断获得公民权利和培养公民自治能力与公民社会建设是同一个过程,这要求我们充分利用现实社会所提供的一切机会和可能性。 本书旨在讨论如何超越单位制对我们的思想力和行动力的约束,建设和提高领导力。在我们蹒跚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需要看看背包里有些什么样的遗产,这些遗产又是怎样消耗着我们的行动力。 从哪里开始呢?我选择在华跨国公司作为具体场景。跨国公司的典型性在于,它的外部是中国正开始弱化的单位环境,内部是以在单位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本地雇员为主体的雇员群体,而跨国公司体制夹在两者之间,其中的矛盾、冲撞、妥协和融合,代表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典型现象。本地雇员在跨国公司里建设领导力、实现职业发展、发挥领导作用,其间的挣扎与困惑、冲突与矛盾、成功与失败都具有总结价值和借鉴意义。 这本书主要是讨论本地雇员的缺点的。本地雇员的众多优点使他们有可能在跨国公司里生存下来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职业发展,但他们中的优秀者却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这种瓶颈是同质的,既不是性别歧视,也不是种族天花板,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我想告诉他们,那个瓶颈就是单位制的遗产,不卸载它就无法突破制约他们前行的阻碍。其他阻碍也是有的,比如跨国公司的身份类分制所导致的外籍雇员与本地雇员的不平等竞争,但这是可以克服的,因为人员本地化不仅是一种认知,更是一种现实。只是这种现实还有另一面—在领导者职位上,少有适合的本地雇员胜任。 我知道,我刚说的是可能犯众怒而且十二分不中听的话。忠言逆耳,我唯一的建议是吞下这颗坚果,细读后面的论述,看看能否以你的认同化解它。 这本书基本上没有对跨国公司的外籍雇员进行讨论和评论,只是在有助于对本地雇员的讨论时才涉及。这并不是说外籍雇员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也多得很,但他们不是我关切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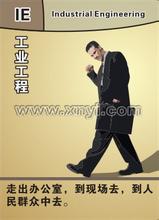
对典型环境的选择却并不意味着对典型人群的选择。这本书是写给转型过程中的单位人的,而不只是跨国公司的本地雇员。即使是从未在国有单位里工作过的人,其早期的社会化(包括家庭、幼儿园和学校的教育)也一定是在单位里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城市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单位人。单位人共有一种困惑,就是在与跨国公司体制共处或共事时,总感到有什么地方不接轨、别着劲儿,但想不出究竟是哪里。这种困惑预示着一种危险:想不出哪里不对,便认为没有什么不对,一切行为依旧,而行为依旧的结果是对组织的商业利益或国际化进程的损害。本书中“跨国公司”主要指在中国已有巨额投资、雇用众多本地雇员的大型跨国企业,“本地雇员”概指中国大陆公民,不包括香港、台湾或外籍的华人,而“外籍雇员”概指本地雇员以外的雇员。因为我也是本地雇员,所以书中也常以“我们”来代指本地雇员。 本书中对跨国公司雇员群体的分类是依照跨国公司的现行薪酬—福利结构划分的,符合跨国公司内部对员工的分类方法。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