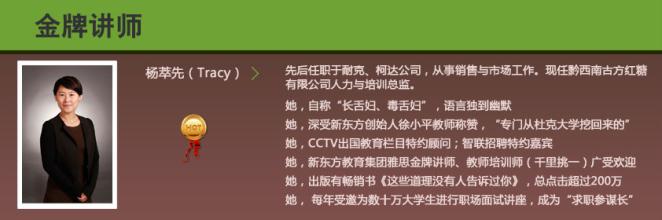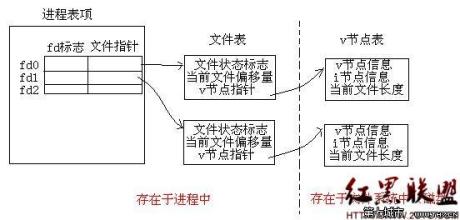系列专题:《活着和死亡:向记忆道歉》
"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说我很同情他,但是,这话说出来怎么听也会有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 老任的丈夫失踪了。 宁说:"这个人会不会想不开啊。" 我想到他在台上唱歌的样子:"应该不会啊。" "绝对不可能。他这个人很懦弱的。除了唱歌,别的事情从来没主意。我就是看上他这一点才嫁他。"老任开始为自己准备东西了,从孕妇服到婴儿包。省歌的人早就把这事传得全城的文艺工作者都知道了。"那个抽烟斗的老任,出事了。" 老任的丈夫回来了。他坐着红旗车,和老丈人一起回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我也是听说的: 老首长带着两个警卫员一个司机。四个人把老任堵在了家里。 "你跟我到军区总院去。" 老任没听明白。 "你不去也行,在这里把肚子里的杂种去了。"老首长对那三个小伙子说:"把她拉上车子。" 老任站在墙角,张牙舞爪:"你们谁敢碰我一下,试试看。" 三个军人都不敢,首长的女儿啊。 "孬种!"首长踢了司机屁股一脚,自己上去捉女儿。 老任一下子就钻到了床底下。 首长够不着了。屋子里转了一圈看到晾衣杆。他端着杆子像是拼刺刀,使劲往床下捅。 老任在里头撕心裂肺地喊,现场一片混乱。 躲不过去了,老任又从床下爬出来,拼命朝首长叩头:"爸,你就饶了我吧。"她的身上被晾衣杆捅得不像样子。头发像个拖把扫着地。 "把她给我抓起来!"首长朝三个军人吼道。 小伙子的力气哪里是老任可以抵抗的?老任象一堆破布被揪着扔到了红旗车了。车走了。开到了我们医院,老任进了我们科。 是主任亲自动的手。 老任被上了麻醉机,处于完全昏迷状态。 出手术室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腿上到处是擦破的伤口。衣服也撕了一个大口子。 引流瓶里是老任的骨血,大约二百多毫升的胚胎组织。 首长握着主任的手说:"我教女无方,给你们增加麻烦了。"

主任除了一脸惊恐,我看不出还有什么表情。 老任的丈夫给老任拎了一保温桶糖水鸡蛋。 老任醒了,她好像还没明白,一直用手护着自己的肚子。嘴里不住地嘀咕。没人听懂她说什么。老任的丈夫把头凑过去,老任抬起手就给了他两个耳光,然后就是不停地打下去。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进去阻止, "劈劈叭叭"的声音很刺耳。 后来,老任哭起来了。她的声音早就喊哑了,就听到嘶嘶的叹气声。 第二天查房,主任不敢进屋,我硬着头皮站到老任跟前。她把我的手抓着放在她的肚子上:"你摸摸,里面空了,扁扁的。" 老任的手很漂亮,指头修长。冰冷。我不敢把手缩回来,就觉得那股冷一直顺着我的手爬上去。 "安心养好身体。"我说,还温情脉脉地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只觉得自己的脸都麻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才发现,老任得了抑郁症。她整夜睡不着觉,老是听到婴儿的哭泣。她说:"我的小孩子吵得我睡不着。" 她必须服超量的安定才能睡上二个小时。 我们不敢让她出院。 晚上值班,我去看老任。她对我说:"你看到我的烟斗了吗?" 我说:"明天我给你去拿。" 烟斗在她家的卫生间的镜子前挂着。老任的丈夫灰溜溜地跟在我后面想见老任。我对他说:"你还是算了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