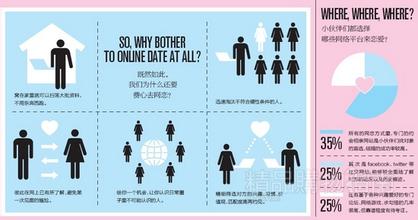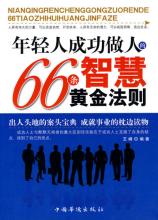系列专题:《活着和死亡:向记忆道歉》
第二部分:艰难的时世 现在想起来,1966年的夏天好像就没有过。我天天穿着长袖,怕挨打也怕看别人挨打。那个时候,我看到了太多的不能忘记的事情。每一次出门,妈妈都让我在手腕上扎一条手绢,怕被别人打破了头好包一下。还有就是穿胶鞋,这样跑起来快一点。 但是,人性真是残忍,我也一样,还是很想看。很多小孩子就是这么看着学会打人的,下手真狠。我只是不敢打。只干过一件事,把墨水倒到一个阿姨的脸上。到现在也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她已经没机会听我的忏悔了。最近的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格拉斯写了一部书,《剥洋葱》。生活就是这样,常常因为剥开了一颗洋葱,受不了,就会流泪。名人可以在各种场合炒自己,写名人的人也跟着出名。小人物呢? 我用这样的方式纪念我认识的小人物。有的人不高兴了,这也好。火葬是让一个人的肉体完全离开的方式。我用我的火葬场让那些可恶的年代远离我们,让我的小人物们像凤凰一样重生。 记忆中的格格奶奶 我们学校是大清光绪年就有的。是最早的学习西学的中学堂之一。上中学的时候,我是从五年级直接升上的,那年我不到十一周岁。 学校门口有两棵巨大的樟树。进校要爬坡,坡上还有两棵巨大的樟树,里面有洞,可以钻进去好几个人。学校的教学区和宿舍分在山坡的两边,都围着围墙。宿舍区的大门上弧形的图案,是西洋雕塑,清代留下的。 在这个画面下面有一个小摊子,坐在小摊子后面的是一个老奶奶。 老奶奶穿着蓝褂子,大襟的,领子很高,上面围着绣了一圈小花。老奶奶的头发梳得很亮,一丝不乱,拢在后头,有一根红线绕在中间,然后穿一把银钗子。银钗子很漂亮,上面有鸟还衔着链子。之所以知道是银的,是因为我有一天终于忍不住摸了一下。她笑起来说:"好看啊?" "好看。"我又摸了一下。 "银的。"她把我摸歪的银钗扶正。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银,过去都是听说。 学校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地主庄园:墙有几丈高,看得头晕。地主家里有一个晒金台,专门晒银子的。老百姓说当年的一个人不知怎么就进了这个地方,看到那么多的银子,一下子就疯了。见人就是一句话:"没服。"(当地话,意思是不服气。)这事成了阶级教育的生动事例。我们都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回到学校还要写心得体会,我写了:我坚决不会要地主的银子。 "地主有很多银子的。"我想起那个庄园。 奶奶不说话了,忙她的小摊。 小摊是卖零食的:一个小小的木柜,盖着一个玻璃罩,里面有很多格子,格子里放着洋桃片、咸橄榄、蜜杨梅、山楂片、糖球、还有一小包一小包的爆米花。运气好的话,米花里还有铁皮小剪刀可以玩。这些东西,一分钱到三分钱。我把妈妈给我买铅笔的钱省下来买这些好吃的。 只要有同学走过去,奶奶就会站起来,笑咪咪的。她站得急的时候,身子会晃一晃。因为奶奶是小脚。 奶奶的小脚只有我的铅笔盒一半大。白的袜子,鞋帮是尖的,总是蓝颜色。上面绣着花,荷花最多。有的花我不认识。熟了,我就会问奶奶。 "这是牡丹、这是桂花、这是凤仙,凤仙加了明矾可以染指甲。" 第二天,我去买桃片。奶奶拿出一个百雀羚的香油盒,打开,里面是一团红红的东西。她说:"这是凤仙花,我给你染。" 我的手指尖慢慢红起来了,漂亮得要死。回家路上都不敢碰衣服,就这么扎着手往家里走。 妈妈看到了,说:"你怎么回事。"

我伸出手:"奶奶给我染的。" 妈妈听了,叹口气:"你不知道她住在我们后面?" 写周记的时候,我用了"喜出望外"形容我的心情,老师在下面还打了红圈,这是好词好句的标记。 奶奶就住在我们机关外的一幢老房子里面,门朝南开,老是关着。墙边上有一块石碑写着:泰山石敢当、金界。我得绕一大圈才能进去。 第一次进去,觉得院子里很凉。一个大大的天井,四边是刻着图案的石条。正中的大堂里全是花格子,两边厢房也是花格子。现在想起来,至少是清康熙爷时代的文物,还不得让文物贩子二十四小时惦记着? 天井里有两口大水缸,我要踮着脚才能看到里面的东西,金鱼。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