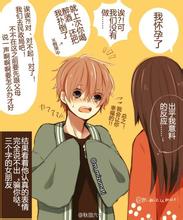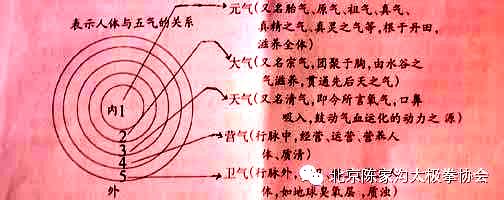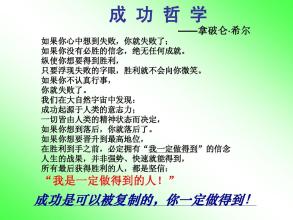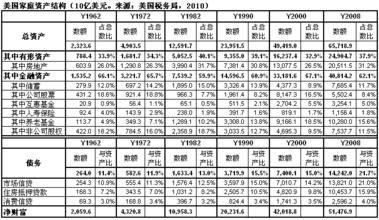系列专题:《名记基础:特稿采写宝典》
第一节 特稿之谜何其多 捕捉特稿线索,前提是要认识特稿"特"在何处,以便于我们按图索骥,对号入座。 坦率地说,特稿就像"美"之于美学、"诗"之于文艺学、"人"之于伦理学一样,不但不好定义,而且,至今也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在特稿的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一、 特稿的历史是一个谜 大家知道,报纸作为现代传播媒介最早出现在西方。特稿是西方新闻写作的一种重要方式。说其重要,是因为在西方国家,只称"新闻"或"报道",并无"通讯"这一体裁,按照他们的划分,除了消息、社论之外的所有文章,都可以归为特稿,美国新闻学教授詹姆斯·阿伦森在《特稿写作与报刊》中写道:"特稿,通常指报刊上篇幅较长的某类稿件,这类稿件没有正规的新闻导语,写的是有关某人、某机构的一桩新闻事件,或某一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 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乃至于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新闻奖。她创立于1917年,奖项由最初的为公众服务奖、社论奖和报道奖,发展到现在的14项。其中,1979年设立了特稿奖(Pulitzer Prize Feature Stories)。《巴尔的摩太阳晚报》的记者乔恩·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篇读起来像短篇小说的医学报道《凯利太太的妖怪》,意外地得到普利策奖评委会的赏识,获得首届特稿奖,这标志着一种新型的新闻文体由此得到了权威机构的承认。 而在中国,特稿历史到底起于何时,至今尚无人加以考证。我偶然从曾敏之写的《抗日战争中难忘的往事》一文中见到了这样的回忆:

1942年,我担任桂林《大公报》的记者,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后期,失地千里,流民载道……衡阳是湘桂铁路交通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保卫衡阳的是国民党第10军,军长是方先觉,他苦守衡阳40天之久,以弹尽援绝而失守,他也不知所终,传他已被俘。我在湘北奔波了一段时间,以前线全部军事逆转而奉命撤回桂林。 1944年10月,我撤退到重庆后,在《大公报》担任采访军政新闻……一度苦守衡阳与敌鏖战40天而城陷传已被俘的军长方先觉,突然脱险到渝,他的行踪是极端秘密的,受命在来向蒋介石汇报军情之前,不得泄露行踪。而我却从一位国民党高官口中得知这一信息,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十分重大而轰动的新闻与事件,于是就费尽心力,辗转从国防部总参谋长陈诚的公馆取得了方先觉藏于陈诚公馆的确证,为了能冲破警卫森严的陈公馆,我借到了一部豪华轿车,伪装成"大人物"直驶陈公馆,警卫人员见到我的派头,不敢阻拦,于是混了进去…… 回到报馆,即以电话向总编辑兼主笔的王芸生汇报访问方先觉的情况,王先生十分兴奋,要我赶写特稿,他写社评配合刊登…… 当特稿刊登时,王芸生以《向方先觉军长欢呼》的社评配合,借方先觉守土抗战的行动,对国民党不战而退失地千里、独山受威胁、后方受震动的局面,提出尖锐的谴责,令蒋介石感到难堪…… 这则回忆表明,早在20世纪40年代特稿在中国就已经出现了。 时至今日,新华社设有国内部特稿室;1996年5月,《华西都市报》筹建特稿部;1999年,《沈阳日报》成立了特稿部。由此看来,特稿也确实是有历史生命力的。 二、特稿的称呼也是一个谜 一个新生事物产生后,正像一个婴儿诞生之后,往往会起一串名字,爷爷奶奶起一个,外公外婆起一个,父亲起一个,母亲起一个……后来,只有他比较定性比较成熟了,才会有一个确切的大名(即学名)。 新闻如此。中国新闻报纸刚刚诞生的时候,记者不叫记者,而是叫"访员"或"报事人",后来,才统称为记者。 杂文如此。杂文是评论与文学的杂交。现代杂文是随着报刊的发展特别是副刊地位的确立而逐渐兴盛起来的一种新文体。刚诞生的时候,称呼多种多样,上海的《同文沪报》称为"丛谈",《申报》称为"杂感",《新闻报》称为"谈话",广州的《觉悟日报》称为"谈屑",《浙江潮》称为"杂文"等。后来,才形成比较统一的名称"杂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