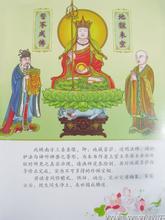系列专题:《世界名校开学毕业典礼演讲精选》
大学课程不容许学生有时间作个人修身的"独思",它同时不允许学生有独处的空间。四年或七年大学生涯,大半在喧哗而流动的群聚中度过,自己对自己的检讨、探索、深思,难有空间。对此,梅贻琦感叹极深: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砺,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复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 "慎独",其实就是在孤独、沉淀的内在宇宙里审视自己在环境中的处境,剖析人我之间的关系,判别是非对错的细微分野,"慎独"是修炼,使人在群体的沉溺和喧闹中保持清醒。这,大学教了你吗?"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砺",在不在大学的课程里? "只知从众而不知从己"的人,不知"人我之间精神与实践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的人,请告诉我,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纽约市长布伦伯格是纽约市立大学今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人,他送给毕业生的"金玉良言"是:"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比别人能打拼。如果你比办公室里所有同事都早到,都晚退,而且一年365天没请过一天病假--你就一定会成功!" 他举自己的父亲作为典范:"我父亲就是这样,他从早干到晚,一周7天,一辈子从不休息,干到最后一刻,然后跑到医院挂号,就地死亡。" 我看了报纸对这段"金玉良言"的报道,不太敢置信,心想:会不会这位老兄意在反讽,却被居心不良的媒体拿来做文章?于是我找出他演讲的现场录像,从头看到尾,发现:老天,他真是这么说的,而且极其严肃。 我想,如果你是以纽约市长这种哲学来培养自己的,我会很恐惧有一天落在你的手里。医生被称为医"生"而不被称为医"死",是因为,他必须对"生"要有所理解。 第二、制度性教育教了你如何认识"实",但没教你如何认识"空"。 我不知道在你们医学的制式教育里,有多少文学的培养?你们全都在摇头,表示没有。我认为,文学应该是医学院的大一必修课程。文学,应该是所有以"人"为第一对象的学科的必修基础学之一,因为文学的核心作用,就是教你认识"人"。

读过卡谬的小说《瘟疫》的,请举手一下……70人中只有4个,比例很低。我因为2003年的非典爆发而重读这本小说,小说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描写一个城市由于爆发瘟疫而封城的整个过程。瘟疫传出时,锁不锁城,有太多的重大决定要做。是什么样的训练,使一个卫生官员做出正确的决定?医学技术绝不是唯一的因素。是什么样的人格,使一个医生可以走却决定留下,不惜牺牲?是什么样的素养,使一个医生知道如何面对巨大的痛苦,认识人性的虚伪,却又能够维持自己对人的热诚和信仰,同时保持专业的冷静? 卡谬透过文学所能够告诉你的,不可能写在公共卫生学的教科书里。医学的教科书可以教你如何辨别鼠疫和淋巴感染,可是卡谬的文学教你辨别背叛和牺牲的意义、存在和救赎的本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