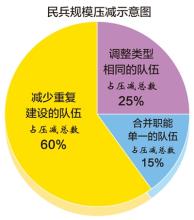文/Corinne Neale
在来自新巴塞尔协定银行业实施小组和对初始模型确认评审的监管人员双重反馈的激励下,第二波开发内部评级基准计算模型(Inner Rating Basis)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亚洲。
在来自新巴塞尔协定银行业实施小组和对初始模型确认评审的监管人员双重反馈的激励下,第二波开发内部评级基准计算模型(Inner Rating Basis)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亚洲。 考虑到接触信用风险模型开发银行权益人的数量以及他们可能冲突的目标,模型的再建和完善很可能会成为风险管理业的一个永久性特征。这种发展趋势,体现了巴塞尔协议对促进模型开发和风险管理实践不断进步的精神。 作为发展里程碑的标识和对以往经验的总结,我们对许多亚洲银行及其监管机构在实施IRB所面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涉及三个方面。此外,作为最佳实践性银行,花旗集团在IRB实施方面,其全球业务平台使其面临与亚洲银行相同的挑战。我们对花旗集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这些实际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终端用户(比如,贷款员,投资组合经理,信用分析员)应该如何参与信用模型开发和测试? ●IRB的风险预测如何做到既有前瞻性又植根于历史? ●在实际工作中,银行怎样满足使用测试(UseTest)的要求? 终端用户对IRB模型开发的参与 第一个问题,在亚洲,终端用户对模型开发和测试的参与"合适"程度,尤为相关。亚洲银行没有单独的内部风险建模和分析团队,因此更倾向直接或者间接通过顾问,求助于终端用户,来设计和确定评级模型。如果不同业务对模型开发施加的影响不均衡就会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 在花旗集团,独立的模型开发团队积极寻求内部风险经理和业务终端用户的参与,在此基础上来决定模型的输入变量。模型变量的选择过程本身取决于变量的统计显著性,而终端用户根据自身经验进一步分辨那些对特定行业或市场来说不可靠的变量,以及传统上用于分析客户信用风险的变量。在一些终端用户的量化背景更为显著的国家,比如韩国,终端用户会被邀请到纽约来参与模型变量的选择过程。这些特意安排,使感兴趣的终端用户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变量的选择过程,从而有效利用内部专业能力来提高用户对产品的接受度。 为了促进整个过程的一致性,统计技术和方法的技术层面全部由花旗集团的模型开发团队确定。所有的主要决定都由整个团队共同通过,并且由经验丰富的具有量化背景的终端用户参与建模技术的基本讨论。 IRB模型方法的确定直接根植于花旗集团的商业实践。这一点为终端用户接受产品提供了双重保证。例如,模型中的一年违约概率投影水平线(OneYearProbabilityofDefaultProjectionHorizon)是根据花旗集团批发型风险评级原理定义的,这就为建模团队确立了目标。主要的模型方法全部由风险经理,业务经理和模型开发团队共同合作确定。 在整个模型开发过程中避免使用技术术语,以此来提高透明度以及内部各级终端用户的专业能力。例如,考虑到类似"当前型(Point-In-Time)"或者"贯穿周期型(Through-The-Cycle)"的专业术语从未在业务领域里使用,花旗并不使用这些术语来定义评级系统。在符合IRB标准和要求的基础上,模型对特定的时间范围(一年)进行预测,但是其开发和测试依据更长时间范围的数据,包括在许多情况下的多重循环。模型对终端用户提供的输出结果表现为与一系列违约概率相关联的内部风险评级。 因此,花旗集团终端用户在理解一年违约概率的含义,或者在协调一年违约概率与自身评级理念方面没有任何困难。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花旗集团就以违约概率和预期损失范围定义内部评级系统,从而建立符合花旗集团商业原则和规范的模型。风险等级图示定位提供了与风险关联的简单途径。 风险预测既具前瞻性又根植历史经验 第二个问题是风险预测如何既具前瞻性又根植于历史经验。这个问题特别是对许多亚洲银行的挑战。首先,现在广泛使用的记分卡(Scorecard)在风险预测时更着重于序列相对系统(Rank-ordering Ordinal System)而非直接预测违约概率的基本系统(Cardinal System).此外,要获得既反映长期历史均值又具有前瞻性的预测结果,其目的在于将主观性因素加入风险量化的过程。考虑到1998到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历史数据是否可以作为未来预测依据对亚洲银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既根植历史又具有前瞻性的IRB模型的运用中存在的挑战导致了花旗集团大量的模型再建,从而使商业实践与新巴塞尔协定的预期保持更紧密的一致。 许多在九十年代初建立的初始评级模型都是统计回归模型(Logistic-type Model).在这些模型效用的启发下,由于复制内部以及外部风险评级模型带来的数据问题,花旗集团开始转换思路。在这个时期,花旗集团开始实施建立全球违约及财务数据库的研究项目,使得银行可以建造具有前瞻性的,适用于任何资产组合(获评级的或者无评级的),用以预测一年度违约概率的模型。考虑到较大的资产组合涵盖中小企业,这些一年违约概率模型对其信用风险的预测显得至关重要。由于中小企业缺乏外部评级,违约预测模型就必不可少。 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银行现有的信用风险模型与新巴塞尔协议预期保持一致的结果。新巴塞尔协议预期要求模型作为IRB实施的一部分,在长期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开发,并且对违约风险进行前瞻性预测。 因此,与IRB标准相符,花旗集团内部模型设计为在预测违约概率时表现出前瞻性。此外,作为概率模型设计的结果,模型可以用于情景分析(ScenarioAnalysis),使用者通过改变主要输入数据比如利率,或者减少收益,来反映经济发展低谷。在这些情况下,模型可以生成"草拟"评级结果或者多次"草拟"评级结果,使用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分派最终评级。 应新巴塞尔协议要求,花旗集团模型在开发过程中的校准和测试都基于至少一个(如果没有更多)的商业周期。大部分花旗集团用于校准的历史数据库可以回溯到1994年,跨越一个十年的周期。在韩国,花旗银行通过收购建立平台,历史数据可以回溯到1998年。由于时间范围较短,作为模型开发的额外注意事项,韩国模型以内部客户数据为基础校准并且以非客户数据为基础测试。 当然,对模型的历史数据基础必须进行认真分析,数据的完整性对于确定模型是否符合"以历史为根据"的要求至关重要。比如,在韩国,考虑到相对较短的数据历史,花旗模型开发团队在数据清理和模型开发阶段通过与业务终端用户紧密合作来对用于校准的数据进行核查。这种共同努力在必要程度上保证了用于校准的数据库能够代表最终适用于模型的资产组合。对于其他基于内部数据和供应商数据的模型,花旗集团花费了大量时间清理,复审和人工检查输入数据。业务部门接下来参与对违约和非违约实体的数据复审过程,以保证数据库具有与模型所适用的资产组合相似的特性。 因此,开发的模型数量是银行投资组合的构成,业务重点和数据可获得程度的函数。 满足"使用测试"(UseTest)的要求 第三个问题是识别出满足新巴塞尔协议下"使用测试"(UseTest)要求的实践活动。现阶段,有些亚洲银行还未使用信用模型对信贷利差(LoanMargin)的违约风险进行定价,尚未建立积极型投资组合管理(ActivePortfolioManagement)的团队,并且还没有以个体债务人信用风险或者以投资组合损失的统计度量为基础进行限定管理。这一问题带来的挑战,对具有这些现状的亚洲银行的影响尤为显著。 2006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对IRB使用测试的指导。在这一前提下,花旗集团开发并且实施了与指导要求一致的风险模型。在花旗集团全球业务和操作范围内,模型的开发和实施提高了用于信用风险估测实施的信用风险方法,风险定义,和历史数据基础的一致性。 在花旗集团,模型使用的一致性构架通过"基准债务人风险评级系统"(Baseline Obligor Risk Rating)建立。风险经理和业务经理可以对基准进行一些有限调整使得基准可以包括对债务人或者行业的特定风险,比如,那些在模型的输入数据中没有反映的风险。模型广泛的涵盖了所有的普通公司(General Corporate)(又称为工商业,包括非金融服务公司)以及花旗开展业务的所有国家的商业银行。在数据允许并且建模工作持续进行的情况下,会继续添加更细分的模型。 在此意义上,花旗集团模型确立于业务活动并且用于支持日常交易和操作。除模型评级以外,风险经理还研究其他的度量来指导最终风险评级的分摊和信贷审批决定。他们可能依据来自全球风险评级机构的评级,以及一些市场基础模型的输出结果,比如花旗集团自身的混合型违约概率计算模型(Hybrid Probability of DefaultModels). 为了使模型更有效地被接受和使用,终端用户通常被培训,而他们的回馈用于未来模型的改善。其中一种回馈表现为终端用户被认可的对现有结果的异议。有关花旗集团信用系统的更改会被及时实施以防止异议进一步扩大。像终端用户通常在培训中被提醒的一样,任何统计模型都有极限,因此用户对公司,市场,政治氛围,管理和其他因素的专业知识对于进行最精确的风险测量至关重要。 对于像花旗集团这样规模和复杂程度的银行来说,成功地运用内部信用风险计算模型极具挑战性,并且要求对内部资源,深入的信用建模和市场的专业知识,以及不同市场环境和文化的沟通合作的广泛投入。对花旗集团而言,随着令人满意的效用成果的增加和终端用户信心的提高,这些努力达成了一种透明的,一致的,分析上严格的信用风险测量和管理方法。 (作者Jennifer Courant供职于Citigroup,Risk Architecture.作者Corinne Neale供职于Algorithmics Capital Managementgroup.)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