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思维是我们第一次经济升级的发动机,但是现在已经成了第三次升级的拦路虎。
文/周仲庚
新加坡华点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实力得到第一次升级,国民所得GDP由不足400美元突破1000美元。现在中国实力迈入第二次升级,奔向GDP3000~4000美元。按照目标,第三次升级约将发生在2020年左右。 我们可以用会计的理念来比喻中国的三次升级:第二次升级的重点思想之一就是“资产性的收入”。在长达20年的升级过程中注重的是“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而这一次升级将“资产负债表”也列为发展要素。损益表追求的是经济总量及最终留在荷包中的利润,现金流量表追求的是握有足够的现金供周转及支撑成长,而资产负债表展现的是可持续成长的资源,从企业来讲就是有形的库存、设备,无形的知识产权,从国家来讲就是原料存量(矿、林、地等)、工艺技术及无形的环境条件。 以上的轨迹很清楚。第一次升级中确实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损益表及现金流量表。第二次升级所追求的资产负债表,在中央的决心下其成绩相信也指日可待。 那么,第三次升级呢? 现在就开始担心公元2020年的事,是不是早了些?一点都不早,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到第三次升级的要件,应该说这个担心已经晚了。 在千年历史的包袱压力及不足百年的现代化经验下,第三次升级将遇上多只拦路虎。本文仅谈其中的一只“母虎”。为什么称它为“母虎?因为很多其他方面的拦路小虎,不论是社会面还是企业面还是政治面,都含有它的基因。 很吊诡的是,这只拦路虎正是第一次升级能够取得如此良好成绩的发动机制,也就是大家所感激的承包机制以及其背后的承包思维模式。 中国人的承包思维 回望历史,可以理清中国人承包思维的脉络。 最原始的承包就是封建制度,一种绝对的物理资源隔断,定额进贡,其他的归你。这里面绝对没有价值链或价值流的概念;如果黄河上中下游分为三段承包,那么上游那一段一定竭泽而鱼,或尽情排放污水。 稍微进步一点的承包,开始引进法律规范。资源虽然归你运用,但你不得如此如此。例如,几寸以下的鱼不能捕,污水排放质量不得超标。但即便如此,承包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对物理资源的运用决定权。如果连资源的运用方式都要规范细节,那就不叫承包了,而是集权或计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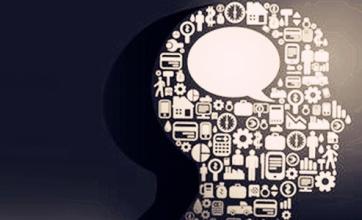
中国民族的资源运用史,大局上可称作是一部集权与承包交替出现的起伏史。这个潜规律主宰了人们思维千年,一直到今天。在过去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下,中央控制力强大时就集权,弱势时就承包,国库充实时就集权,空虚时就承包。从军队到生产,从税赋到官位无一不如此。少数始终未承包的活动,朝廷则视如神圣珍宝,如科举选才。 新中国打破了这历史循环,成就了几件历代难以建功的大事。首先,军队杜绝了承包,再来,银票(货币)也杜绝了承包。 完全不可否认的,承包制及其各种形式的变种对近二十年的中国经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承包制,改革开放做不出今日的成绩。由中国自身内部来看,承包思维的功效可圈可点,今天需要追问的是,从国际竞争的层面看,承包思维堪负重任吗?例如: ?包税思维,足以应付中国未来20年的财政需要吗? 村地、农地、工业地的土地承包政策,足以应付中国下一代人的环境生态需求吗? 交警、路警的罚单承包,足以改善交通吗? 博导与大学之间的博士生承包关系,能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吗? 最近兴起的“官员决策失误要担责”之风,基本上是一种不问过程只问结果的“决策承包”思维,这样足以提升官员决策质量吗? 家长、学童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承包思维(你考95分以上就给你买变形金刚),对中国下一代人格教育有利吗? “承包”的局限 今天多数人都已意识到,本土企业的“来料加工”,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头在外”,已经难以继续提升中国的经济附加价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自愿地、主动地划定了自己在全球化生产价值链中的承包角色。虽然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承包的角色不足以成大事,但是古老的承包思维下的短期利益格局,具有难以被变革的凝固力。 转过身来看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内需市场是中国的主场,道理上主队应该比客队拥有实施价值链整合的绝对优势。然而,国际价值链运营商经由在中国近二十年的操作,已经意识到了,最容易让中国人理解、接受的就是承包思维,只要顺着承包思维讲道理,提供足够的“承包好处”,大多数中国人就会对号入座。于是,价值秩序的整合者与被整合者的坐席就被区分出来了。 “承包”与“政策”是两个相抵触的概念,就像“正方形”与“菱形”是两个抵触概念一样,当人们说“承包政策”时,就像在说“正方的菱形”一样的矛盾。 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商业模式上,“连锁”是有政策的;选址要依循总部的政策,价格要遵循总部的政策,质量、流程都有总部的规范。而“加盟”的本质仅是“挂牌承包”或“借经验承包”。尽管你有政策,在“利润归我”的承包思维下,我就有我的“对策”。在包干的结构下,政策与规范是没有执行力的。当政策不力时,资源整合自然难以进行,系统也就成为不可能,资源割裂下所带来的浪费也就惊人。 再进一步举两个眼前的例子。中央推动绿色GDP,国务院进行“规划环评”立法,但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部门地区利益冲突导致立法推迟”,其中两大阻力来自“重审批轻规划”的部门利益,以及“短平快出业绩”的地方利益。 再看,国家推动第二套房贷款收紧政策,但由于国有银行已经是“包干”单位,对策百出,有的以“个人”为单位,有的以“户”为单位,交通银行(爱股,行情,资讯)最妙,内部监管细则规定,第二套房贷的界定由各分行因地制宜自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承包体制的自然产物,尤其在政绩指标承包的情况下。例子举不胜举,翻开每天的报纸从经济新闻到社会新闻各种例子扑面而来。以上所举两例就来自同一天报纸的相邻版面。 “承包”的根源 承包是一种基本的经济分工,或利益切割方式,或权力切割方式。凡是人类的活动,都见得到承包的影子,大至皇朝的封建制度,小至家庭中的儿女零用钱发放方式(你负责洗碗,每个星期给你五十块零用钱)。 但是在中国,为什么承包会如此深入人们的思维,乃至到“承包挂帅”的地步?资源运用与承包挂钩,政绩考核与承包挂钩,企事业经营与承包挂钩,科研与承包挂钩,出租车与承包挂钩,医疗与承包挂钩,办学与承包挂钩。哪一种重要的人类活动,在今天的中国不与承包挂钩? 这是个困难的课题,需要各路专家的剖析,此处的观点,仅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观察。作为早期的经济活动,承包可以实现释放潜在价值的作用,随后,若资源是丰富的,原始的承包思维将会转化为某种“协作”或“价值链”的思维,因为谁也不愿意吊死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反之,若资源出现匮乏,原始的承包思维就会固化为一种零和思维(他多吃一碗,我必然少吃一碗),而经济上的零和反应,必然导致权力上的零和反应。否则,地主制度是怎么来的? 中国历史上的主干思维是零和的,因为承认零和,所以只得“认命”、“顺天”。一直到了近代,看到了西方的经验,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意识到原来在“零和”的概念外还另有一个“成长”的概念,才认识到生产工艺、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原来可以突破资源的匮乏。不幸的是,在追求“成长”时,心理嫁接的还是原始的承包思维。为了迎接第三次升级的挑战,为了突破平均GDP5000美元的门槛,中国是不是该来一场“思维转换工程”了? 今天,翻开报纸。从社会新闻到教育新闻到政法新闻,无处不看到承包思维的底子。二十年前的“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描述的是追求原始积累的现象。时至今日,原始积累格局已成,但若未来20年走向“十亿人民九亿包,还有一亿在推敲”,那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了,而是社会文化学或历史学的问题了。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