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关键在于界定政府职能,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否则,即便大部了,仍会回到小部的营生
王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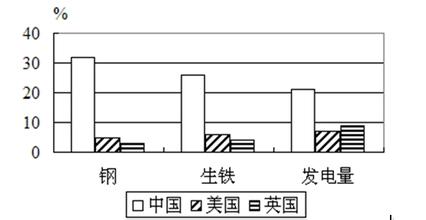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大部制之所以在2008年热火冲天,是因为公众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大部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启动。 政治体制改革范围广大,既有国家层面的政治,还有社会机构层面的政治,也有公众日常生活层面的政治。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认为,在这3个层面上,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是权大法小,官重民轻。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制度缺失,也有观念缺失。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来走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有很大进步,但也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首要和最关键的是没能建立规范的制度,造成部门立法和管理相结合,并且行政、司法与收费罚款等部门利益相结合,严重抑制了社会的创业活力和投资热情。其次,权力集中、官僚主义、机构臃肿和家长制等依然严重存在。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权力腐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大,牵一发动全身,改什么?怎么改?先改什么?后改什么?如何衔接?怎么继续?每一任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是在前任的基础上推进,既要接受前任的“遗产”,也就承担着前任的困惑。因此,谨慎,犹豫,甚至拖延政治体制改革而“击鼓传花”——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或许也是时代的次佳选择。 一个大部制,如何承担政治体制改革重担? 但大部制确实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大部制表面上是职能和人事的变动,实质是权力、资源和相关部门利益的调整和重构,政府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的重新确立,而不是部门间的简单合并。 只谈政府行政改革。这里有一些基本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宗旨是什么?政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关乎意识形态,牵扯到政治体制改革,也期待技术操作。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进行了5轮。从最初的精简政府机构,一步步转变政府职能——由全能的管治型政府,转向权责相称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最终建立有效有限可问责的政府。这是一场伟大的变革,是对过去数千年中国政治传统的“反叛”。 然而,公众对政府改革依然颇多不满。中国行政管理部门规模庞大,不仅是因为部门利益作崇,还因为政府承揽了太多的直接管理职能。政府控制着大量资源和企业,对经济活动进行微观管理,有些部门号称是监管机构,但与主管部门无异,以保证下属行业繁荣,维护下属国企盈利为己任。 因此,大部制改革关键在于界定政府职能,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否则,即便大部了,仍会回到小部的营生。 发改委怎么办 发改委是大部制的学习榜样还是负面模板?发改委怎么办? 在3月11日人大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特别为发改委说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要进一步转变职能,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进一步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 此言完全在理,条理分明。但现实是绿色的,又怎能长出千奇百怪的花朵。 有论者认为:发改委“集权力之大成”的实质与大部制根本抵触,也使大部制改革无法推行。此次大部制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要解决职能交叉问题,但发改委的职能涉及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几乎所有方面都与其他部门重叠或冲突。 虽然发改委是宏观管理部门,是指导性的,似乎很吻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但许多规划做完了就束之高阁,真正着力是那些项目审批权、资金调配权,以调控之名,行审批之实,以市场之名,行计划之实。如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于某些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但原本由地方政府批的项目,到国家发改委备案后就成了变相审批和收权。 发改委的前身是国家计委,权倾朝野,有“小国务院”之称,宏观微观全管,但也没能解决职能交叉、决策失误等问题,2003年并入原国务院体改办和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实际上是“下岗了”。 深圳“行政三分”被锁进抽屉 如何防止大部制下的政府机构权力过大? 据参与此次内部方案设计的人士透露,与此前5次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制方案中加入了“决策、执行、监督”分立的意图。即对“三权”进行厘清、分立归属,形成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运行机制。 此论5年前在深圳已有故事。 2003年初,深圳市“行政三分”改革试点,当时引起海内外巨大关注。深圳特区也期望凭借这次改革重拾“改革先锋”的光环。还有境外媒体将“行政三分”曲解为西方式的“三权分立”,这让深圳感到压力。 2002年开始,深圳市政府派员考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管制体系,最终吸取了源自英国“新公共管理”的理念,主要借鉴的是香港经验。 当时改革方案主要是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按照大行业、大系统的原则设立若干决策局,负责制定政府的法规、政策、办法;再根据每个决策部门的关联业务,设置若干执行局;另设置一个监察局。决策局将在每年年初与执行局签订行政绩效合同,由监察局进行考察和监督。 决策局只有决策权,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属市长管辖。 当时最激进的方案是设立3个决策部门,即以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社会发展三大体系为基础,设立三大决策局,然后下设不同的执行局。 改革很快遇上风浪:“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政府机构要给砍掉。”据说,一个星期天,市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突然被通知开会,会上下发了部门调整方案,大多数拟被撤销的部门都未表态同意。某局负责人知道自己的机构将被裁撤,当场拿出一份自备的方案,提出制定改革方案的机构也应该被撤并。 在各部门讨价还价之后,改革方案中确立的决策机构从3个变为12个,再到15个,最终的方案是21个。 改革在争议中沉寂下去。当时媒体的描述是“锁进抽屉,不了了之”。 这“行政三分”天生就不合逻辑。在同一个行政部门里实行“行政三分”,不仅要增加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如何三分得开?大家同吃一碗饭,接受同一个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怎就互相制衡得了? 周天勇从更大范围设想了制衡机制,他说,我们不要谈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人民能把政府收钱和花钱管住,就是最大和最实际的人民民主政治。要真正建立起人大政协—政府—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架构。人大体制要改革完善,包括人大代表制度、会议制度、程序都要改革,让人大体制真正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发挥监督作用,例如,一定要管住政府乱收费、乱罚款,这是最基础的。 国企无权与民争利 国企是政府公共财政以企业形式的延伸。国企怎么做事,实际上就是政府怎么做事。政府是不应该参与经营的,不能与民争利的,那么国企,特别是央企怎么办? 3月6日,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表示央企的任务是赚钱:央企的贡献主要是多纳税,通过财政分配到社会,而不是直接让利,否则会影响(央企)经营积极性。企业的主要任务还是获取利润,在兼顾国家、股东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赚得越多越好。央企的经营利润并不完全是价格造成的,有很多因素,如经营成果,并非完全是政策或垄断造成的。 王瑞祥副主任给央企提出了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如何兼顾国家、股东和社会利益? 几年前,中石油、中石化挤掉民营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这两家国企通过国务院出台法规,限制一定距离内的加油站数量,最后逼着大批民营加油站以象征性价格卖给中石油、中石化。中石油、中石化兼顾了国家和股东(包括海外股东)的利益,但如何兼顾社会和民企的利益?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说:“国有企业的存在会从根本上破坏行业的游戏规则,法治就难以成为现实,因为法治的第一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民企跟国企不可能平等。” 国企是企业,企业该不该由政府负责? 学者王占阳认为: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指导国企改革的基本理论,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误区和危害日益显现。国企绝不应该实行政企分开,如是,那就是剥夺了国家所有权,也就是剥夺了人民所有权。如果国企实行自负盈亏,就是剥夺了人民对国企的收益权,也就是剥夺了人民对国企的所有权。国企无权与民争利,无权在人民面前奢谈“国企利益”。如果按照私有产权的逻辑明晰国企产权,就只能把国企变成事实上的“集体私有制”企业。 国企是政治。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