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媒介高度商业化运作伴生的新闻、广告、娱乐三者的冲突与可能的危害,以及“社会公器”为本位的新闻运作(编辑)机制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媒介市场化、产业化、集团化的进程中如何防止媒介偏离和疏远公众利益提供了借鉴。 与中国媒体尚停留在同业监督(非大范围,仅局限于个别媒体)层面不同,西方媒体的自律机制已上升到了行业评议制度与媒介自律的高度。当然,中国媒体也有自己的行业协会,但如众所周知,其监管重点并不在此。往往要等到新闻敲诈等恶性事件曝光后,它才象征性地发出声音。 英国人在1953年首创了全国性的报业评议会(后易名为“报业投诉委员会)制度,根据为保护编辑和公民双方的权利而精心制定的规则听取针对报界新闻报道准确性和公正性的诉怨,这个成功的范例导致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美国新闻业在20世纪下半叶发展了一系列以媒介批评为基础的专业自律机制,如新闻评议会、专业协会及其章程、内部督察员和专业批评期刊等,其共同特点是“软监督”而非“硬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闻业对自由与独立的要求。目前,美国多数新闻机构采取的是媒介自律。 2003年,《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一、二号人物,因下属两名记者造假和侵犯合作者著作权而双双宣布辞职。在此之前,《纽约时报》刊出长达四个整版的“认错报道”。 《纽约时报》的自我纠错机制,绝非偶尔为之,亦非哗众取宠。其自我纠错的编辑制度体现在“更正”栏与“编者的话”的设立。两个栏目在一张报纸上被固定存留,实际构成了组织制度和编辑制度的一部分,形成新闻组织的“纠错”机制。正是这种自我纠错机制常规性地发挥作用,才使得在时报曝出丑闻后,依然能够赢得读者的信任。 西方的媒介自律,主要是规范媒介的传播伦理范式,即选择何种道德推理模式,在诸如读者利益与被报道者隐私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而中国不是,财新的这几篇调查报道说明中国的媒体生态已越过伦理失范的藩篱,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监管不到位、法律的模糊与空白、泛商业主义等因素助长了这些媒体弃“社会公器”、“媒介的良知”于不顾。如何推进和建构中国媒介的专业自律机制,恐怕是财新同业监督报道的意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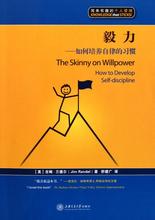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


